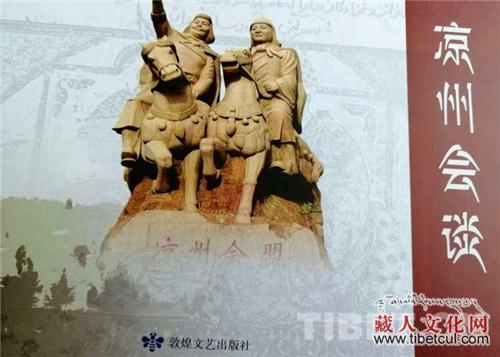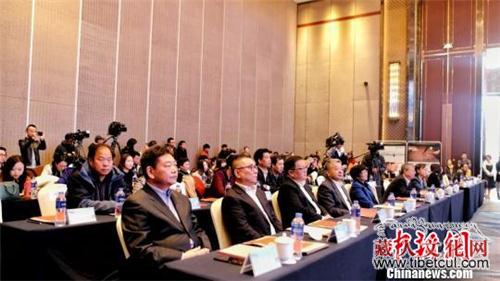中国的藏学研究队伍
在旧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研究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振兴藏学,着手把瓢 零星散的各族藏学专家吸收、聘任、选调到藏学研究机构中来,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中国政府于1951年6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央民族学院。学院没置的第一个专门就是藏语文专业。当时,从全国各 大学抽调了一批有力的青年人入校培训,新中国藏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工作就此迈开了第一步。这些青年学生 在老一代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大多成为藏学研究、教学、编译、出版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古藏文研究班,延聘藏族名师授课,进行藏学的语 文、历史、宗教、哲学、医学、天文等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从这个研究班毕业的学生很多成为高级藏学人 才。与此同时,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高等学府在培养藏学人才方 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1978年以后,全国有近百名藏学研究生学成毕业,其中半数以上是藏族。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本科生、专 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源源不断地回入到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这些中青年学者不囿旧说,发表了高水平的 学术论著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中国藏学研究进入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
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科学工作者才开始对西藏进行有计划的文物考察。
1959年西藏开始创设文物管理机构。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60年代初期,西藏文物工作者分赴各地,调查、征集到数万件失散文物,其中有举世罕见的贝叶经有西藏绘 画艺术的瑰宝珍珠唐卡,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宗教器具。关于贝叶经的普查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贝叶经是一种用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书,源自印度,因不易保存,现存世品极少。由于西藏特殊的 自然条件,至今仍保存有不少贝叶经,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贝叶经的搜集、整理、研究,对研究佛教和古代 南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查发现的文物中还有元明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 、印鉴、金册、匾额,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拉萨等地修建的石碑,以及乾隆皇帝颁赐的、确定达赖转世灵 童身份的抽签用的金本巴瓶等,还有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和地方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这些文 物不可辩驳地说明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中央政府从很久以来一直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
从60年代初开始,文物管理部门还对西藏全区的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古石碑、摩崖石刻等进行调查,基 本摸清了全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目前,西藏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昭寺、布达拉宫、甘丹寺、 萨迦寺、扎什伦布寺、昌珠寺、藏王墓、古格王国遗址、哲蚌寺、色拉寺、贸布林卡、夏鲁寺、江孜宗山抗 英遗址共13处,还有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1处。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大批存款和稀有、珍贵材料,用于这些文 物保护单位的维护和修缮。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全面维修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由国务委员李铁映任维 修工程小组组长,计划拨款350O万元(约合402.3美元),至1992年又追加到530O万元(约合609.2万美元)。这 项举世瞩目的维修工程耗资之大,在中国古建筑维修工程史上是创纪录的。1994年8月,布达拉宫维修工程胜 利竣工。
截至80年代末,西藏考古工作者在全区共发现旧石器地点5处,细石器地点30余处,新石器地点和遗址20余处 。此外,在山南、那曲、拉萨等地发现吐蕃时期古墓葬群20余处,墓葬约2000座。 1978年至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卡若遗址 ,实物遗存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 代意义,预示着西藏高原考古挖掘的广阔前景。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拉萨北部曲贡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 时代遗址。发掘证明,这是继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又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
藏族历史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50年代,藏汉族文化艺术工作者就开始这 方面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结集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等。
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藏族有古老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 多彩,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学继承、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根 据这一指示精神,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泛流传在民间的音 乐、舞蹈、藏戏、民歌、民谣、格言、寓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截止到1992年底,全自治区共整理出上亿字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本,已经和将要出版 的有《西藏民间故事集成》、《西藏歌谣集成》、《西藏谚语集成》、《西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民间 器乐曲集成》、《西藏戏曲志》、《西藏曲艺志》等大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丛书,全面有效地抢救保护了民 族文化遗产。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说唱体 英雄史诗,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讲的是以格萨尔王为首的一群英雄同人民一道, 英勇机智地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战争、生产、生活、民族、宗教、道德、爰情 、家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古代藏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哲 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长期以来,《格萨尔王传》主要以芝人口头说唱的方式流传,有失传湮没的危险。因此,从50年代起,国家 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组织力量进行这部史诗的抢救工作。1978年以后,《格萨尔王传》被列为“六 五”和“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这部史诗流传的省区均建立了专 门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相互配合,共同开展《格萨尔王传》的挖掘、收集、录音、整理、研究、出版工 作,并举办学术研讨会、民间艺人演唱会等活动。仅西藏自治区一地,以1978年起的10年里,就通过普查收 集到不同目录的说唱版本180多个,收集到木刻本、手抄本、油印本55种共83部;整理出的目录,有首部7部 、18大宗、149小宗,共174部;录制艺人口共头说唱录音70部,磁带3000多盘;并发现民间传说的格萨尔遗 址多处,“格萨尔实物”11件,格萨尔民间传说30多条。预计能整理出80部书,共约100万诗行,1500万字。 目前已经出版了20余部书。此外,集中反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格萨尔研究成果的《格萨尔集成》最近已出版 问世。
藏学古籍文献出版事业
中国各民族文字的藏学古籍文献浩如烟海,难以计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有些学者曾设想系统地整 理藏学古籍文献,并为此进行了努力,终因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央和地方各有关研究机构、出版部门花了很大气力进行藏学古籍文献 的抢救、整理、出版工作。据统汁,截至80年代末,全国各地公开出版的藏文古籍200余种,累计达上百万册 。其中既有《青史》、《红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朗氏宗谱》、《萨迦世系史》等一批 历史名著,也有宗教、文学、诗歌、文艺理论、语法等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四部医典》、《历算派典》等 科技文献也整理出版。
除了藏文原著,还选编出版了一批藏文史料集,如《西藏历代公文档案选》、《西藏历代法规选编》、《中 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分别收录了仅见存于藏文史籍的历代重要历史文献。 《中华大藏经》包括《甘珠尔》(藏语部)和《丹珠尔》(论释部)两部分,是传统藏学的百科全书。1987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将多种版本的《大藏经(丹珠尔)》进行比较校勘,以出版整 部16开精装本158册的权威性《大藏坚》对勘本,与已出版汉文《中华大藏经》珠朕璧合。目前,这项宏大的 工程正在进行中,首卷将于年内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整理、出版藏文古籍的同时,汉文藏学文献 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出版的汉文古籍文献上起隋唐,下迄民国,有一两百种,印教上 百万册,包括实录、档案、奏牍、方略、方志、游记、笔记、日记等,其中不少是十分罕见,甚至濒于失传 的孤本、善本、手稿。《全唐文全唐待吐蕃史料》、《通鉴吐蕃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 族史料》、《西藏奏疏》、《清末川滇边务档案资料》、《民元藏事电稿》、《十三世达赖纸圆寂致祭和十 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黄慕松、昊忠信、赵守钰、 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等均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
经过藏、汉等各民族学者的亲密合作与共同努力,藏、汉文藏学古籍的互译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 各类藏、汉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意义重大。它不但为今人研究藏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为揭穿“ 西藏独立”的阴谋,维护祖国统一,拿出了确凿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保护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关人士 为此专门撰文评说道,在旧西藏,许多珍贵著作仅有一两部手写本,即使印制木刻版,其流传范围也十分狭 小。近代西藏地方政府,则将历史文献封存于秘密暗房,普通人难以自由浏览翻阅。数百年来被禁锢、埋没 、鲜为人知的藏文典籍,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第一次有了各神装帧精美的铅印本,得以广泛出版发行, 重新回到藏族人民手中。
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前面曾经说过,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藏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但是,现代的、科学意义 的藏学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确立的。新中国藏学与传统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首先,新中国的藏学工作 者是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方法分析、研究藏族及其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把藏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新中国的藏学研究突破了传统藏学大五明(即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和小五明(即诗 词、词藻、韵律、戏曲和历算)的范畴,发展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民 族、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法律、制度、教育、考古、民俗、医药、历算、工艺技 木等等。其中主要是社合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某些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体系。
据粗略统汁,近40多年来,中国藏学界人士撰写的论文、文章约有五六干篇。其中有些发表在《中国藏学》 、《西藏研究》、《中国西藏》、《国外藏学动态》、《西藏社会发展研究》、《雪域文化》、《西藏艺术 研究》、《西藏教育》、《西藏佛教》等藏学刊物上;国内许多相关的学术刊物、报纸也为藏学论文提供发 表的园地;另外还有一些藏学论文专门结集出版。
中国藏学界的专家学者撰写并出版的各类学术专著数以百汁,蔚为大现。《西藏通史》、《藏族简史》、《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蒙藏关系史略》、《清政府与喇嘛教》、《达赖喇嘛传》、《西藏地方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西藏革命史》、《西藏封建农奴制形态 》、《西藏宗教史》、《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族文学史》、《藏语简志》、《汉藏语言概论》、《当 代中国的西藏》、《西藏:非典型二元化结构下的发展改革》等著作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藏学研 究有关领域的问题。此外,还有几十种词典、书目等工具书问世。其中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已故张怡逊教授 主编,有近六十位藏学专家参加编写的《藏汉大辞典》。这部辞典藏汉语双解,收词目5.3万余条,300多万 字,是国内外收词目最多、部头最大、有很高学术份值和使用价值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藏汉大辞典》 出版后,受到国内外藏学界一致好评,被誉为“藏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国内外学术交流
为了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各藏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每年都要举 行几次规模不等的藏学学术会议,经常举办各种专题的讲座、研讨班、进修班,互派访问学者,并就若干重 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
1980年以来,中国藏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凡是国外举行的国际性藏学会议,几乎都有中国藏学家 参加;中国藏学家还经常应邀到国外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合作研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藏 学家来到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功。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就接待了几百人次的外国学者和港台学 者。还有不少国外进修生、留学生来华学习深造。近年来,中国藏学界在北京、拉萨等地召开多次国际性学 术会议,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蒙古、捷克、前苏联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藏学家应邀 到会。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中国的一些藏学研究机构还与国外学术机构签 订了合作和交流的协议,使国际学术交流正规化、经常化。通过上述活动,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与国外同行的学 术交流将会在更为宽广的领域持续、顺利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