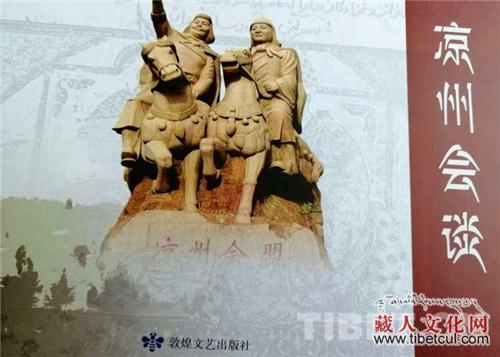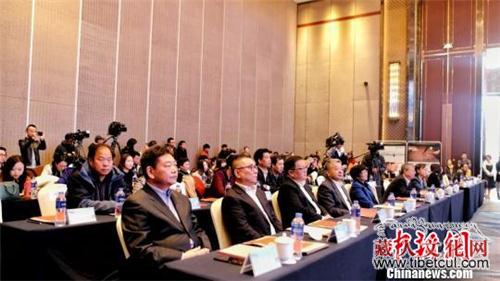苏俄:藏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苏俄藏学的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沙俄时代
早期开始对于西藏的研究即已初具规模;(2)沙俄境域控制范围内的布理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图瓦人所信
仰的喇嘛教乃从西藏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3)在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上苏俄学者的贡
献较其它国家为大;(4)苏联的藏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外首屈一指;(5)十月革命后,苏联藏学家在藏学研究中
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在国外藏学研究史上,苏俄学者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
下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苏俄西藏学研究的兴起、形成和发展作一简要的叙述。
一、沙俄初期藏学研究的发轫沙俄初期,俄罗斯中亚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于1774—1782年经喀什、喀喇昆仑来
到当时的西藏文化区拉达克,他的《漫游和奇遇》一书于1786年出版,其中有“西藏”一节,生动地叙述了
拉达克一带藏人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这是苏联历史上对于西藏的最早的直接报导。尽管他同匈牙
利学者、国际西藏学的创始人乔玛一样并未进入过西藏本土,但作为早期的第一手记载,以后的苏联学者一
直对其活动大书特书,如丘涅尔(1877—1955)教授的《西藏志》(符拉迪沃斯托克、1907,1卷上册)、尤瑟夫
的《西藏自然地理述要》(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茹拉夫列夫的《俄国人在西藏高原旅行的历史》(1963年版)
都将其活动摆在首要位置。
二、德裔俄国藏学家俄国早期藏学家多为德裔人,较有成就的当推施密特(1779—1847)。他是俄国科学院的 院士,其藏语知识是从布里亚特喇嘛中学来的。他用藏文著名史籍《王统世系明鉴》的卡尔梅克文译本来研 究蒙古史。其成就主要在藏语方面,他的《藏文的首音》(1832年版)较早地分析了藏文基字与前加、上加字 的关系。他还编制了《甘珠尔》索引(1845年版)。他的《藏语语法》(圣彼得堡、1839)及《藏-俄字典》(圣 彼得堡、1843年版)是俄国藏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藏语语法和字典的出现为俄国藏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三、不懂藏文的藏学家比丘林俄国的藏学研究要发展,不能只靠外国血统的人,但当时不仅很难在俄国人中 找到一位通晓藏学的人,甚至要找一位精通藏文的人也殊非易事。然而俄国东正教会的驻京使团的一些汉学 家中却不乏研究藏学的有志之士,比丘林(1777-1853)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1807年被任命为该团团 长,在北京居住达十四年之久,期间在我国搜集了许多文献,包括典籍。他通汉、满、蒙诸文,但不通藏文 ,在藏人钦喇嘛的帮助下,从汉文编译了《西藏现状志》(圣彼得堡、1928年版),这是俄国学者同藏族学者 的首次合作,该书并附有成都至拉萨的路线图。他还从《廿三史》及《通鉴纲目》中编译了《西藏和青海史 》(圣彼得堡、1833年版),且附有各时期的地图多幅。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书在俄国藏学史上曾经产生 过,而且至今仍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些不通汉文的藏学家多藉此书来攫取汉文中的有关西藏记载。人们 至今仍可发现,俄国藏学家的立论观点多与中国传统史书观点相同,追根寻源,就可发现材料出自比氏的编 译。人们还发现:比氏的藏学研究要较乔玛早好几年。只是由于乔玛精通藏文,并用英文著述,故影响胜于 比氏。如果说乔玛首开用藏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气的话,那么比氏也可说首开用汉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 气,二者各有千秋。
四、俄国藏学研究的兴起早在1790年,加克曼就发表了《西藏史地及其自然状况的报导》,尽管这还谈不上 是什么研究,但在对西藏所知甚少的俄国,这种概要性的介绍无疑是必要的。1800年后,也就是说从十九世 纪开始,俄国的藏学研究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德裔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通过 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藏文,其所撰之《藏语研究》(1851年版)至今仍为学者所征引。他的《梵-藏-蒙佛学辞 典》(圣彼得堡、1859年版)中使用了俄国所藏藏文木简。他还翻译了藏文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及 《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伦敦、1882)。《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人从象雄语中转译过来的本教要籍 ,席氏的《本教经典<十万龙经>》(1881年版)是国外最早研究本教经典的论文。瓦西里耶夫(1818—1900)也 许是俄国第一位精通藏语的藏学家,他还通汉、满、梵、日、朝诸语及几种突厥语,他的藏学研究成就有赖 于他的语言天才,除翻译了藏族僧人多罗那达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外,还翻译了敏珠尔呼图克图的 《西藏地理》(圣彼得堡、1895);并依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编译了《西藏佛教史》,这部著作为手 稿,苏联学者多所引用。与此同时,俄国境域内的一些蒙古学者也在研究藏学,如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喇 嘛迪尔基洛夫将《如意宝树史》译成了蒙文。卡尔梅克人巴扎-巴克希曾去西藏朝圣,他的《西藏旅行记》 最早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897年出俄文对照本。
五、到西藏去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这是当时俄国所谓“探险家”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 国的扩张野心是产生这种欲望的土壤。俄国藏学史进入了探险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 l888),1879年他首次入藏,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进藏。他很快到了离拉萨仅160英里的地方,因遭当地人民 反对,只好败兴而归。他的许多游记曾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普氏最后死于赴藏途中。其后彼夫佐夫(1843— 1962)肩负起了所谓西藏“探险队”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1896年出版的三卷本 《西藏探险集》(圣彼得堡)记载了“探险队”1889—1890年的考察成果。罗博罗夫斯基(1856-1910)曾以动 植物学家的身份随普氏和彼氏多次入藏。俄国的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 国参谋本部的重视。科兹洛夫(1863-935)是俄国西藏“考察队”的殿军,他曾多次入藏,其《蒙古与康》 (1907年版)、《蒙古与安多》(1923年版)、《蒙古与西藏》(1913年版)、《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年版)等 著作反映了作者试图将西藏的两个文化区“安多”与“康”,以及蒙古、达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