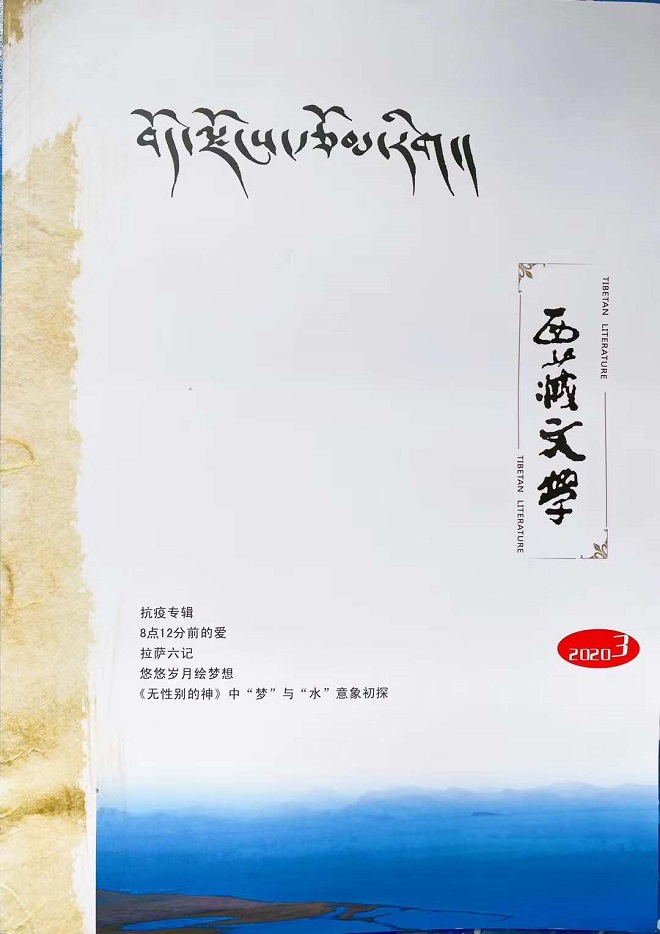
六只铜铃
八月间,带上雍贝去拉萨转经,那是我的意愿,他只当是一场出行。
凌晨五点的登机时间,我们四点便起身赶路。飞机离地起飞时,我牵住了身旁安坐的雍贝的手,我们在各自的内心里踩着最轻的脚步,去推开一重又一重厚重的门……舷窗外,浮云如潮漫向天际,一道红光猛然跃出,天穹瞬息渐变为嫣红、橙黄、黛青色,愈来愈浓厚,愈来愈深广,于是,我们看到了金色的日出,如天地之眼。
抵达贡嘎机场,巨幅的玻璃墙外,超然明艳的日光照亮了我们细碎又急切脚步,还有我们几乎就要生发翅翼飞出的心灵。坐上驶向拉萨市的小汽车,雍贝侧目看着窗外景致,一路无话。沿路,稀稀落落的白杨树林立在一片沼泽湖里,湖面映着寂静的天空,荒凉贫瘠的山体,还有无边的光影。汽车转入拉萨市区,经过巍然屹立的伟大宫殿和那红白色彩时,雍贝才发出惊喜声来,一双眸子闪着晶莹。
我们预订的“暮野客栈”,在小昭寺对面的深巷里,由一栋半新的藏式民居装修而成。紧挨着几户民居,门紧闭,门楣上钉着水波样别致的布幡,养着几盆雏菊的窗台上卧着一只黢黑的野猫,祖母绿的眼睛警惕地看着我们走进大门。进门是一方院子,院中设有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一大壶为客人准备的藏红花茶,我们落座喝茶,等待十二点钟,早先入住的客人退房。墙根下有一湾清水,雍贝蹲身去拨弄水里游动的几尾深红锦鲤,水面上浮着几株印度蓝睡莲,出水的地方有白色的雾气不断地升起、逸散,睡莲若隐若现。有穿长裙、戴墨镜的女子同提着行李箱的男子走下木楼梯来退房,门口吹送的微风轻扬起女子的裙边,她戴银镯的手护住裙子只微微绽开,有进门来的客人忽然遇见她的样子,眼神活像是闪烁在五月间的花蝴蝶。又有几个女子下楼来退房,她们窸窸窣窣地说话,林芝、泽当、芒康,这样的字眼洁净明亮,使她们的嘴角泛起了明亮的笑。
我和雍贝的房间在二楼,是一张茶桌间隔的两处榻榻米。床头有两根柱子,盘绕着龙凤和大朵的牡丹芍药,两扇窗户照进来的光线令它们栩栩如生。
临近晚上的拉萨,日照依旧炽烈,我和雍贝在脸上围了防晒的面纱去大昭寺转经。大昭寺门紧闭,门外,人们在起起伏伏地磕长头,有修行的老人坐在边角,用一只八宝碗舀起面前布袋里的五彩青稞,倒入,又舀起,像要使这古老植物焕发出耀眼光芒。我领着雍贝在众人身后磕头,对着门内的觉卧佛通白:我和雍贝来朝圣了!
有人在身后拽我的衣边,转身,见一位纤小的姑娘,胸前挂着皮围裙,她竖起一双拇指对我说:祝长寿!皮围裙下随之冒出几只黄毛狗儿来,两只嗅着热突突的地面焦躁地叫唤,四只仰头与那姑娘一道用清澈的眼睛望我,分别套在它们颈脖上的毛绳一端全部系在姑娘的腰间。我递钱给她,愿她用我们的名字行乞,身体温暖,心灵满足!姑娘眼露微笑,把钱揣入怀中便转身朝着转经的人潮一步一拜,五体投地的前行了。狗儿们随着她走走停停,像六只无声的铜铃。
心中的花朵
一梦醒来,天光柔和地镀在窗玻璃上,像梦本然的模样。
我和雍贝去大昭寺,寺门外排满了从八方赶来朝圣的人。一直走到几尊白塔处,我们才接上队伍末尾,随不断进入寺庙的人缓慢前行。那些与我们逆行的脚步正匆促地环绕大昭寺转经,他们口中默诵的经文,手指捻动的串珠像遗落在这个清晨的雨点样透明又快乐。有蒙着花头巾的妇人提着暖水瓶(熬好的酥油用作点灯)和哈达紧随着我们叫卖,我们默不作声,她们耐性极好,一直随在我们边上走。就快接近寺门时,队伍滞留了一阵,只见前方立着一位身穿灰白藏袍的男孩,怀抱一大把金色的哈达,人们纷纷朝他递钱,他动作僵硬迟缓地取出一根哈达递去,才接过钱费力地揣入怀中,接着又取出一根哈达给另一个向他递钱来的人。他接过我的钱时,队伍迅速快进了几步,我转身朝他摆手示意:并不重要,请不必追逐。他把头扭向一边,嘴里发出了“哼”一声,像一头倔强的小牛拒绝喂食第一把藏盐那样。他从中选出一根较长的哈达,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哈达柔顺地向后飘逸着。到我近前,他踮着脚将哈达顺利地搭在了我的肩上,那高昂的头随之晃动了两下。我对他微笑,像回敬这圣地对我的一场优厚礼节。
进入寺院,我和雍贝双手合十,按左进右出的转经仪轨朝拜,去记住一尊尊庄严法相,让内心获得从容与安宁。朝拜的人挨挨挤挤,偶有后来者贸然越过我们前去,身后就有举着佛珠的老人伸手来护住雍贝的臂膀,恐怕撞了孩子。雍贝并不回头,是早已在心里点亮了一盏灯来庇护自己。有的佛陀单独供奉在一间窄小的房内,佛龛上的酥油灯照亮了佛陀的面容,他那样生动,像是一直就在那里精修,只是偶然间轻轻目睹了我们恭敬膜拜的身影。人们用头去顶礼门口的护栏,表达诚恳的意愿,又从栏杆处投进几张角票才匆匆走过。继续左绕,需要登上几步台阶,有僧人立在门口主持秩序,双手船桨样赶着起伏如潮的人们,我们就这样来到了供奉觉卧佛的大殿。提早嘱咐过雍贝,觐见觉卧佛,要在心里许下愿望,从佛陀的面容获知因果。佛陀端庄慈美,默默注视着我们。我将那条金色的哈达搭在了佛陀的脚边,心想:世尊!我只要你脚上的灰尘一点。人们不断举起暖水瓶递向立在佛陀脚边的僧人,僧人不断接过暖水瓶倒入铜灯盏里,又迅速将铜灯盏里的酥油倒出在一个木桶内,灯盏里的棉花灯芯一直孤寂地亮着,那是它的使命。
走出主殿,遇见了文成公主进藏、显密二宗佛像等色彩丰盛的壁画。不晓得是哪一程的微风,吹动了公主和侍女们的衣袂,她们像在自如地飘飞。我的指间也有一丝柔风穿梭而过,原来是雍贝快步从我身边走到了一壁《欢庆图》前,他入神地仰望着以浅绿为主,金色为点缀的色彩,它们好似茂盛植物与纷繁果实的属性。几对摔跤的男子,用粗壮的手臂盘绕对方的腰部使劲,仿佛谁先跌倒,滋养在谁心中的花朵就会枯萎。跳面具舞者,用动态体势表达着丰盛的情感,演绎了天地万物的喜怒。看久了,自己也被注释在壁画中了,那方白脸面具忽然朝我揭下,我就见到了前世里我的一生......再往前,人们就分散了,有的上了二楼,有的继续朝三楼攀爬,我们则沿千佛廊绕“觉康”佛殿转一圈“囊廓”为圆满。
走出口,路两边坐着化缘的人,手中握着一把枯叶样的角票,一边吟唱,一边微笑。
深巷里
在深巷里穿梭,脚下的路近似叶片上的脉络静静舒展,通向大昭寺,通向冲赛康,通向一两栋响着清脆铃铛的转经房。不担心迷失,路总能把我们送回去。
经过冲赛康的入口,人频繁移动,声音嘈杂,有飞扬的音乐伴着民歌唱响:拉萨的冲赛康,你想要什么这里都能买到......融进人群,脚两边向着市场深处延伸了两排席地售卖杂货的人,其间自然形成一条弯弯绕绕的通途。他们面前铺展了一方油纸,上面齐整地摆放着新鲜塔黄叶包裹的奶制品、青草捆扎的大黄杆、浸润了鸡油黄的小蘑菇......经过之处,有浓重的草木香气袭人。他们身后围了大大小小的商铺,经营藏毯、铜器、竹器、佛器等。我蹲身在一束蓝莹莹的绿绒蒿面前,用指腹去轻触花茎上的细密绒毛,扎绿头绳的妇人不动声色地看着我,面容像映照我的湖水。我拿起一束递向她,她嘴角上扬,露出了皓白的牙齿。她从怀中牵出一个小布袋,取出一张面值二十元的纸币,展示给我看。我奉上同样面值的钱,捧走了花。继续走,我们停在了一个编织氆氇的妇人身后,她身体微微向后倾斜,腰背缠绕的皮条拉直了延伸至店铺深处丝丝缕缕的牛绒线,一把光滑的木梭在氆氇与绒线间穿梭。顺着氆氇进门,妇人抬头对着我们身后说了一句温和的藏语。店内码放着编织好的各色氆氇毯子,还有氆氇缝制的衣服和长靴。我站在齐整的绒线面前,它像一把古琴,我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仿佛我天生就具备弹奏它的本领,那旋律能让城外的石头像牦牛一样奔跑,让天空的白云回心转意。我为自己忽然而至的想象无声地笑了。出门时,那妇人又抬头说了一句藏语。我知道,她说的是:再见。在拉萨,再见是个美好的祝福词。
一个铜器店,在门口就能照耀我满眼的金灿灿。走进,被顶上方垂吊的铜灯盏、铜香炉连续碰了头,我指着香炉看向老板。老板用一根镶着铁叉的竹棍取下香炉来给我。在家,我一直用铁炉烧糌粑、酥油,火供我隔世的奶奶。一个个都说铁炉火供,会烫伤召唤的魂。铜炉子才是它们的专属器皿。可是,火供的那些日子,奶奶来了我梦里,她的面容分明是喜悦的,倒是我的心一直在灼痛。我细细地看铜炉,山形盖,圆盘底座,圆柱与炉体相接镂空的花,这更容易让炭火受风,能使火供的粮食滋滋地燃烧,如此,遂了愿望。雍贝提着铜炉在前面走,圆润的日光在上面晃荡。
周边忽然就安静了,我们又走入了另一深巷。一个甜茶馆门口放着一张藤编椅,上面熟睡着一位戴毡帽的老人,一只不灰不白的猫在他脚边假寐。我们像梦一样轻轻走进了老人和猫的影子里。
甜茶馆
早起,雍贝说,先去寻早茶喝。
路上的行人,脚步带着一阵风经过我们。路面的青石板,记忆着他们围大昭寺转经的步数。临街的店铺在陆续开门了,有相馆,门口张挂着融进了民族元素的人像摄影。唐卡店内,卷头发的年轻画匠已绷好了一面新的画布……转完经的人,走向了店铺后方一间间光线灰暗的茶馆喝茶,热气丰饶着他们的面容。
我和雍贝随他们的脚步迈进了一间客人稀疏的甜茶馆,几张藏桌上放着几个矮小的暖水瓶。待我们坐定,里屋悄然走出了一个女子来,她手捧着两只茶杯,摆放在我们面前,雍贝自行提起水瓶往杯里盛茶。女子低头站在我们边上等待点餐,我对她说,需要两碗藏面。她点头便进屋忙碌去了。我和雍贝喝茶,一口甜茶入喉,滇红的内敛,牛奶的淳厚,砂糖的甜腻,如接于松林中的春雨之境,令我的五脏六腑逐清醒而身心喜悦起来。雍贝咂舌,用闪着晨光的嘴唇说,甜美。
女子很快端出了两只大木碗放在我们面前的藏桌上。根根圆润的面条浸在半碗清汤里,面上漂着几点葱花和牛肉末,我和雍贝端碗大口地享用这圣城才有的至味。面条松软绵糯,咀嚼能体味到做面者雅致矜持的为人。门口又走进来五六位老人,他们肩背花氆氇口袋,是从远方来拉萨转经的人。女子又捧出几只茶杯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从各自的氆氇口袋里取出糌粑皮袋、木碗和酥油盒子,有的在木碗里放入糌粑酥油揉捏,拌匀,压紧,倒入半碗甜茶大口喝尽,便用舌头舔舐那层打湿的糌粑吃下,又添入甜茶慢慢喝起来;有的在木碗里放入拇指大的酥油,倒入甜茶,酥油融化后放入糌粑用手指来搅拌成团,握在手中,再在碗中倒入半碗甜茶,一口甜茶,一口糌粑的吃起来。他们悠然自得的样子,像是在自家的火塘边上一样。雍贝喝尽最后一口面汤,擦拭了嘴巴去望老人们吃糌粑。边上一位扎着蓝头绳的老人对着雍贝温和地笑,雍贝腼腆地回敬微笑,他眼角就盛开了雏菊花样的皱褶。老人从油浸浸的糌粑团上取下一小块双手递给雍贝,请他一起享用早餐。雍贝连连摆手说着谢谢的话。旁边的几位老人见状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他们笑的时候都朝着一边倾斜,像风吹醉了一片沉甸甸的麦穗。
我起身准备付钱离开,雍贝对着我的耳边说了句热乎乎的话。我点头,雍贝“嗖”一声进了里屋,再出来时,他身后跟来了那女子。我们出门,女子对着几位老人轻轻地说出了两句歌唱般的拉萨藏语,几位老人便一齐对着我和雍贝的身后回应了几句高高低低地答谢,像雍贝用单手按响的黑白琴键样优美。
初升的太阳端端地镀在大昭寺的金顶上,护法神鹿正朝着远方的山影慢慢起身。我和雍贝今天要去色拉寺转经。
小六
阳光强烈,路人用各式各样的面巾遮蔽了脸,只露出一致通透明亮的眼睛。
我和雍贝转经回来,步子懒散,在街边寻找歇脚喝茶的店子。一拐弯,就走进了一个巷口。有个店铺,名字叫小六。门面用老树皮做成,从钉下的钉眼处仍旧能感受到钉子还具有很强的节奏感。门口晒着几盆海棠,开着深深浅浅的红花。门内偶尔传出几声吉他伴奏的安静没有起伏的歌声,我们随声进入店内,弹吉他的男子坐在店正中一把较高的旋转椅上,他轻轻摇摆,兀自弹唱,像没有旁人一样。一方柜台里站着一位皮肤白皙的清瘦男子,他用修长的手指勾兑一杯红黄绿色的果汁,眼神不时去探对面木桌围坐的几个穿花裙子的女子。她们在轻轻地说话,接过男子递去的果汁喝下,她们笑出了更多颜色的声音,像这古城里的寄养的精灵。
我和雍贝选了靠内的桌子对坐,柜台里的男子很快为我和雍贝端上了两杯柠檬热茶,雍贝一直看着边上一面画着花草的绿色板壁,接着他推开了壁上的一道门,进去了。许久后,他回来告知我,那里面是一个天井,底楼到楼顶都陈设有书橱,每一层的书都分了类别。你想要什么书,那里好似都能找到。我推开那道门,进了天井,仰头就看到了用钢化玻璃打造的透明屋顶,它远比天空更具想象。几个看书的人,立在书橱前,以舒适的方式阅读,偶尔翻动书页,像微风轻轻卷起了树叶。我沿着楼梯上了二楼,接着又上了三楼。越接近屋顶,书橱里的书越像这天井的裂痕,在无声绽开。我用手划着书橱行走,走过了《阵雨中的车站》《古都》《花的圆舞曲》,走过了《神曲》《时生》《东方之旅》……它们通向了四个楼道口。
转入第一个楼道,见一日式推拉门内放置了一张长木条桌,桌上摆放着土陶茶具,土陶花瓶里插着一枝粉红的樱花,桌边一周放着大红缎面的榻榻米靠垫。继续走,见到半截书橱,上面开着一扇白漆窗户,窗内设有低矮的大木床,洁白柔软的被褥边角绣着蓝色的玉兰花,一对枕头上绣着蓝色的叶子。床脚有木桌,桌下放着住店人的行李箱和两双人字拖鞋。是怎样的人啊,觅得了这么精致的住处,他们的梦定然也绣着蓝色花边吧。沿着半截书橱,我走到了另一个楼道口子,它直通向了一间屋子,有柔和的阳光照耀,一个穿白衣裙的女子在低头阅读,她垂下的眼帘像歇着一双黑蝴蝶,蝴蝶轻轻扑扇翅翼,她就去翻动一页书籍。一个五官清秀干净的男子坐在她身后,他在为她编发辫,他动作轻柔、婉转。我从那极致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感到,他们是从川端康成笔下托生在这方相守的男女。我不能惊扰了他们,便踩着最轻的脚步转身离去。
沿着楼梯回到一楼,那清脆的吉他声伴着安静没有起伏的歌声唱着:刻下你的名字,在粗大的树干上,眼看它枝干参天,你的名字会渐渐变大……
我双手捧起杯子,柠檬茶还是温热的。
度母的微笑
一早去堆米寺转经,在入山路口烧香,卖香的老者取了一枝新绿的松柏枝叶沾了清水朝燃烧的桑烟洒去,口中念着秘语。阿克吉麦说,他这是在向山神打招呼:我们来了。
上回到拉萨,阿克吉麦专程从昌都丁青寺赶来引我转经。他不懂汉语,但能够领会我的心意,并回应恰如其分的微笑。阿克吉麦精通象雄占卜术,在闭关静修的时候他占卜了自己的寿数,果真就在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就圆寂了。那天早上,我在佛堂里敬茶水,一只杯子里的茶水忽然就洒了。我从来不会做没有轻重的事情,那早令我没有一点安宁。中午,我就接到阿克吉麦圆寂的消息,才知道那洒了的净水是阿克吉麦的道别。阿克吉麦引我在拉萨转经的日子就越发清晰起来了,仿佛他一路伴在身旁……
一路向上的石梯用白浆泼染过,日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路旁的僧房门紧闭,铜锁紧扣。路边有卖青苹果的妇人,头上系着绿头巾,边上她的孩子在独自玩耍,看见我戴在手腕上的蜜蜡,她跑来抚摸,又靠近来嗅闻,以为是色彩鲜亮的野果子。雍贝想要用厉害的声音呵止她离远点,去找自己的母亲。女孩识别出不是野果子的时候,她仰头望着我的眼睛害羞地笑了。雍贝只好从衣兜里取出一枚薄荷糖递给了她,她剥开后迅速放入了嘴巴里。接着她和雍贝都嘻嘻地笑了起来,他们都知道了糖里的秘密。
登上最高处,俯瞰来路,疏散的红色僧房和庙宇,像一片被日光照耀的鼓声般宁静。矗立在山上的大殿肃穆威严,我们从左侧的小门进入,内里供奉的佛陀高大伫立,怒目相视,手势遮天盖地。两旁粗大的圆柱上有雕刻精美的莲花,正静静绽放。我们按格鲁教仪轨朝瑾佛陀,有穿长衫的尼泊尔男子在一盏灯前添点酥油,灯光映着他黝黑的肤色和精致的五官,忽然从亮处进门来的人看见他眼含的笑,会以为他也是殿前的一尊佛像。临出门,见所有转经的人都走到门边一位老僧人面前,躬身接受他用一截木棍轻触他们的前额,只几秒钟的时间,接受的人要瞬间记起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佛陀自会成全他们祥瑞。几秒钟太过紧迫,我的脑海里挤满了张张面孔,他们仿佛都可归置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事后却又都模糊不清了,许是前世旧影吧。
走出大殿,一路下坡多是沙石路。路边有修行者在光滑的石板上凿刻经文和八宝图案,已刻好的上了鲜明的颜色,晾晒在太阳底下,几只蜜蜂在上面嗡嗡地鸣唱,以为是石头开出的花朵又结出了果子。再往下,听到了一阵水声,我们便经过了一条浅浅的小溪,有些孩童和年轻妇人用铜铸的“擦擦”在水里打印,一次一毛钱,他们脚边的塑料桶里有路人随手丢进的五毛、一元。如此也算是一种营生或修行吧。
走到山脚,有一处简洁素朴的庙宇,门外能闻到香火旺盛的气息。我轻轻掀开张挂在寺们上的氆氇帘子,见无数盏酥油灯照亮了一尊微笑的度母佛像。
门外,十几位年迈的老者在阳光下歇息,自若地捻动佛珠。有的面前放置了一根塑料口袋,里面装有米饭或馒头,他们在享用午餐。有苍蝇停落面前贪馋,他们就取出几粒米扬手撒出去,苍蝇便随之飞落,老者又清闲地抓起一团米饭在手中捏成团放入口中嚼食。他们每天都会在此等候寺内的酥油灯盏燃尽,然后把灯盏擦拭锃亮,装上灯芯等待供朝拜者添点酥油,一如生命生生不息。
“度母的微笑那么美,难怪有那么多老人来这里守护。”我以为是远处的溪水声呢,原来是雍贝清亮的声音在解读。
原刊于《西藏文学》2020年3期

南泽仁,女,藏族,四川九龙人。中国作协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散文》《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著有散文集《遥远的麦子》《戴花的鹿》等,纪实文学《远山牧场》。曾获孙犁散文奖、西凤杯全国青年散文大赛金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