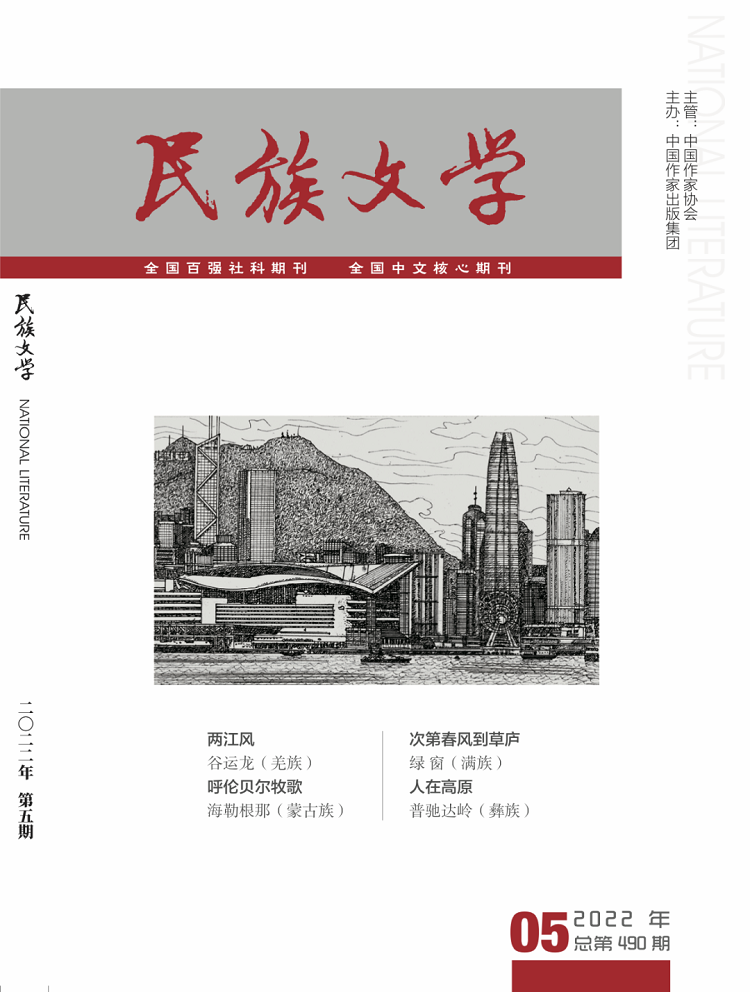
1
藏族有句谚语:有福的牧羊人即使睡着,羊群也能回到自己身边。然而那天,牧羊人的这一心愿没能实现。
次松次仁醒来时看到太阳已从天空正中央稍稍偏移到了西边。南边一片乌云像个阴沉着脸的人正凝视着大地。他不慌不忙地侧身躺下,地上散落着之前吃油馍时掉下的残渣,好多蚂蚁围在上面。那些蚂蚁拥挤着为食物奋不顾身的样子,让他心中不由生出一丝对有情众生的悲悯。牧羊人次松次仁嘴里有时会冒出一句“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每当这样说起,麻囊下庄的人们就会嘲讽地说,拇指般大小的人儿说着石头般硕大的话。但他并不想理会。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对他来说,生活中最多余的好像就是说话了。次松次仁对这些蚂蚁虽有一丝怜悯,但他还是非常顽皮地吹了一口气,那些蚂蚁一下子跟食物一道飘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观望四周,山沟中的草木已变金黄,大地如同披着一层金色的外衣。整座山谷已然没了绿意,满目萧然。
次松次仁没看见自己的羊群,羊群没像往常一样环绕在牧羊人周围。他突然起身又一次观望四周,但羊群如同一朵被风吹走的白云没有了踪影,大地的空旷和寂静使他心中生出一种被人遗忘的孤独悲凉之感。他快速拿起干粮、投石绳、望远镜等一些牧羊人的“装备”,没来得及抖去沾在衣服上的草屑就忙着从温巴日山正面爬去。
在他睡觉的时候,羊群不见了,这绝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次松次仁坚信,在山上他侧着睡、仰着睡、趴着睡,无论怎么睡,羊群都不会走远,会围绕在身边。他也一直认为自己就是那句谚语中所指的牧羊人,自己的羊群就是谚语中的那个羊群。他满身是汗,从山的正面爬上温巴日山顶,视野开阔了许多,但除了狭小的山沟、凹陷的山坳、干涸的河床和黯黑的断崖,目光所到之处都没有发现自己的羊群。次松次仁急了。他气喘吁吁地在山体正面的蓝色巨石上休息片刻,心想:“啊!可恶!大白天的羊群会去哪里?是被狼吃了还是被人偷了?”他陷入了疑惑。不管怎样,羊群如同被风吹走的一朵白云不见了踪影,仿佛是眼前的大地故意跟他开玩笑把羊群藏了起来。
一眼望去,目光被赛青冈挡住。高高的岩山虽直插云霄,但在山顶却像一个豁口般形成一处山坳,山坳右侧焦黑的拉则①宛如一位端坐着眺望远方的老太婆。山冈的另一侧是亚囊上庄,一般羊群不会去那边。次松次仁眯着眼看了一会儿那山坳。一条山路修在深沟,非常狭窄,远远看去像个落有阴影的黑洞。那样看着,他嘴里不由说:“啊!不好!”过了一阵,几只羊沿山路走了回来,像是被黝黑的山路吞进去又吐出来一般。羊慢慢变多,白悠悠地铺满赛青冈的山坡,羊的咩叫声随风飘到他的耳畔。
“咯——”次松次仁看见羊群大喊一声,从温巴日山正面朝赛青冈跑去。
2
“鲁亚——”次松次仁跑到赛青冈脚下,朝在山头吃草的羊群大喊。
“鲁亚——”然而,那只叫鲁亚的放生羊并没像往常一样从羊群中出来,走向他。往常只要喊一声鲁亚,它就会像听懂了人话一样,无论距离远近都会朝他跑来。鲁亚是次松次仁的知心朋友,它虽不能像朋友一样说话,但他们已经在心底认定了彼此,语言就多余了。鲁亚是次松次仁用自己的干粮喂大的,现在它已经长成了一只羊角锐利、羊毛洁白的公羊。平日里他们没有太多交流,但这羊从一开始就知道,鲁亚是次松次仁给它起的名字。只要叫一声,它就会来到牧羊人身边。
没有看到鲁亚,次松次仁四只四只地把眼前的羊快速数了一遍。少了十只。他又气喘吁吁地爬上赛青冈山顶,走到赛青拉则旁,朝山头另一边望去。跟以往不同,亚囊上庄的山谷空空荡荡,没有人畜身影。从前,他也听说过,亚囊上庄和麻囊下庄一样,如今已经没人放羊了,男女老少都走出了山谷,他们夏天去挖冬虫夏草,其他季节外出打工。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座山头像是被人掏空了,已变得空空荡荡。不过,现在他没有时间想这些,他要想的是包括鲁亚在内的十只羊去了哪里。
那天,一切都有些反常。羊群无缘无故从山谷走向赛青冈,而且朝着赛青冈另一边走去,又从山坳里走了回来。在这空荡的山头,除了次松次仁再无他人,但好像又有个看不见的人赶着他的羊群朝赛青冈那边走去,然后又赶了回来。这样一想,次松次仁心中忽然燃起一股火,他直勾勾地盯着被风吹拂的赛青拉则,嘴里喊出:“老天爷、护法神!是谁赶走了我的羊群?”但赛青拉则宛如一位端坐着眺望远方的老阿妈,一言不发。
“鲁亚——”次松次仁朝赛青冈另一侧的亚囊上庄山谷大声叫喊。从远处红色岩山发出的回声立刻回旋到他耳旁。山顶刮起的寒风使次松次仁脸上流下的汗水完全变干,卷起并散落在脸颊两侧的长发也随风飘动着。他干裂的嘴唇已经脱皮,看上去迷茫而焦急。他急切地用目光在上庄的土地上搜寻,没有发现自己的羊。他跑向山坳中那条黑洞般的小路,朝上庄山谷走去。
太阳即将落下,天边的乌云变得越发厚重,现在半边天已经变成黑沉沉的一片了。据说是因为赛青冈亲切地将麻囊下庄抱在怀中,背对亚囊上庄,所以,阴面的赛青冈水草丰盛,但朝向上庄的山头却恰恰相反,阳面的赛青冈没有草皮,像一张怒气冲冲的人脸,越发通红。这却使次松次仁发现了线索,通红的土地上留下了羊群的蹄印。他一路追踪,蹄印渐稀渐少,十几只蹄印落在延伸至山脚的那条小路上。次松次仁从那些印在红土地上的蹄印中间还发现了一串人的鞋印,就落在那串蹄印后面。观察着这些足迹,他发现羊群被赶走已经有段时间,印迹其实已经被风侵蚀了一点儿。自己的羊已经被小偷赶走多时了,他想。
3
次松次仁给父亲饶丹打电话说了羊被偷的事。通常,他们父子间没有太多谈话。父亲是个急性子,他经常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儿跟不上。
“那么多羊怎么就从你眼前消失了?”电话里父亲抱怨说。
“我稍微睡了一会儿,羊群就被赶走了。”次松次仁紧盯着坐落在山谷中的亚囊上庄慢条斯理地说。
“谚语说,男子贪睡易失势;女子贪睡易败家。真是不假。”父亲总是喜欢说谚语。
“阿爸,现在不是说谚语的时候了,应该跟着小偷的脚印走,蹄印和脚印伸向了亚囊上庄。”他说。
“可恶!小偷肯定是到处流浪的‘六只手’。”父亲的话中带着怒气,“一定要留下他的脚印。哎!现在快要下雨了。”父亲又说了些语无伦次的话,次松次仁一时没能理清头绪。最后他说,“我们很快就到。”话音未落,一阵雷声传来了。
乌云从高处往下黑沉沉地压来,即将落下的太阳已被乌云完全遮住,刹那间周围被一团阴影包裹起来。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大风,掀起的尘土,弄得次松次仁一时无法睁开眼睛。可恶!次松次仁冲着大风、乌云、雷声骂道。电话中父亲的嘱咐前言不搭后语,绕来绕去,他只记住“留下脚印”这句。俗话说,小偷虽已进深山,脚印却已清晰留下。倘若自己能留住小偷清晰的脚印,那么如父亲所说小偷有可能是亚囊上庄的“六只手”,不就有了证据吗?然而,强风正在抹去红土地上的印迹,之后还可能会下一场大雨。情急之下,次松次仁突然有了个主意。他在路边一处较为清晰的脚印周围堆了一些石头,上面盖上自己的衣服,又用石头压住衣服的四个角,以防被风吹走。做完这些,他继续沿着蹄印和脚印向山谷走去。
山谷里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就在河边,蹄印和脚印消失了。小偷多么聪明啊!他把羊群赶进河里。次松次仁耐着性子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些羊粪散落在石头缝里。又继续走了一会儿,就在河岸左侧的小路上再次发现了蹄印和脚印,一路向山谷深处的亚囊上庄延伸。
儿时,次松次仁在乡村小学读书,他从课本上读到过一句话:“山谷深处有一座村子,村里只有上进之人,没有堕落之人。”后来麻囊下庄的一些顽皮的孩子就把它改成了“山谷深处有座村子,村里只有堕落之人,没有上进之人。”事实也是如此,半农半牧的亚囊上庄里有几个出了名的小偷,所以整个村子也由此变得更加出名。那些出了名的小偷白天赶走别人家放在山头的牛羊,晚上拿走别人门口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市场上羊皮的价格很高,那些小偷就在山上宰杀人家的羊,拿羊皮去卖。
有时,名声就像一阵雷,它可能是绵绵细雨的预兆,也可能是暴雨冰雹的前奏。因为那些小偷,这里的人遭受过不小的损失。但小偷们逃到山里住上一两个月,搞得乡里的警察也无处抓捕。后来,村里的老人请来了麻囊下庄的活佛,让村里人在活佛面前起誓,那儿的小偷确实变少了。这些年,其实小偷已经没有了可偷的牛羊。这里的人们逐渐卖掉牲畜,去其他地方打工。次松次仁可能是最后的牧羊人了。
在亚囊上庄的路口,随一阵雷声降下了倾盆大雨,是头顶那朵乌云再也忍不住了。在这里秋雨是极为珍贵的,有秋雨如牛奶、如酥油的说法。然而,它现在正在给次松次仁制造麻烦。雨像是存心庇护小偷般地下着,它压住飞扬的尘土,也制造了泥泞,路上的一切都将被冲刷干净。秋雨啊!
4
身上流着雨水来到次松次仁跟前,他才知道父亲饶丹电话里说的“我们”指的是他和邻居家的几个男人。同时他看到父亲手里拿着自己为保留脚印而盖在路上的上衣。
“这秋雨来得真不是时候啊!”父亲一脸愁容,继而转向次松次仁,“有福的牧羊人即使睡着,羊群也会回到自己身边。现在羊群在哪里?啊?牧羊人。”
“那个小偷难道有神灵在庇佑?”雨衣发出吱吱声的那个邻家男人说,“老天爷也在帮他。”
“鲁亚也被偷走了,谁会偷一只放生羊啊?”次松次仁说,“脚印和蹄印已经被雨水冲走了。现在该怎么办?”
“大白天从牧羊人眼前赶走羊群的人一定是‘六只手’,不是说他有神灵保护吗?”另一个人说。
雨势似乎没有变小的迹象。相反,天空像是被谁捅破了一样,雨水如注般倾泻下来。他们站在一片迷蒙的雨水中说话,次松次仁感觉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神灵就在这片迷蒙的天地之后。
“不是有人说六只手是霍尔六只手指的转世吗!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偷都能有这样的荣耀,真是奇怪!”父亲说完,另一个邻居鼓起勇气说:“现在即便是老虎身上的毛也要拔。我们现在就冲进他家里,那么多羊他肯定没地儿藏。”
“如果六只手是个像疯狗一样无头无脑的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偷东西不可能不留下一丝证据。”这会儿父亲饶丹不再焦躁,反而变得十分理性,“他今天能这样把羊偷走,肯定是早有准备。不过,他又不是有先见之明的上师,怎么知道会下雨呢。他家里肯定有一处谁都无法找到的藏羊之处。上庄和下庄本来就有矛盾,我们如果直接冲进他家,无疑是在旧伤疤还没恢复的情况下再制造新伤疤,到时就不是几只羊的问题了。”
“那我们就这么算了吗?”邻居家的男人问。
“那些羊肯定被赶进了村里,六只手有很大嫌疑。”父亲饶丹挥手让大家先回去。他说,“现在只能埋伏观察了。”
听到“埋伏”一词,次松次仁感觉有位旧时代的老人正在慢慢靠近。他从父亲口中听到这样一个陌生词语,感觉自己也要多说一些话。然而,自己只在山头对着鲁亚说过一些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谚语,大部分时间他都沉默不语,而且他已习惯了不言不语,慢慢变得说话都有些不自然了。
关键时刻父亲饶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智慧,尤其是有一种将全局揽入囊中的气魄。次松次仁心底生出一股对父亲的敬爱之情。但他没说什么,只是问了一句:“怎么埋伏?”
“要自己扒下十只羊的皮、取出十只羊的内脏是不可能的。按这数量,小偷肯定要卖给屠夫。所以,不会一直把羊圈在家里。我们要选一个高处埋伏起来。”父亲接着说,“尤其需要观察六只手家的情况。”
“那我来埋伏。”次松次仁说。
“对一个人进行埋伏,就要像去寻找那个人的影子一样,人多了没用,反而会让对方发现,说不定小偷也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先要佯装回去。”父亲这样安排后那些人就按原路回去了。秋雨像是专门来保护小偷的,它洗过大地,而后渐渐变弱,最后就像假装哭泣的人脸上留下的几滴泪水。
他们沿着亚囊上庄的岩山小路朝赛青冈山崖走去,这时周围的阴影变得越来越浓,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黑夜的掩护下,父亲饶丹对前来的邻居道谢,然后安排他们返回。他和次松次仁商量选定亚囊上庄一个高处埋伏。
5
牧羊人次松次仁父子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他们躲在亚囊上庄前方岩山的一个土坳中,在雨后寂静的夜晚里,眼前的上庄沉陷在黑暗之中,几户人家窗户里发出的微弱灯光投向夜幕。父亲指了指离他们较近的一侧村庄外围的灯光,说:“那就是六只手的家,要格外留意。”
次松次仁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村边那个窗口的灯光。地面已经湿透,雨水沉积,他和父亲像两只青蛙一样趴在泥泞中。秋风瑟瑟,又是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寒冷使他们不停地哆嗦。空中的乌云一点点变薄,眼前却依旧被黑暗笼罩,看不见星辰。这黑暗好像故意要包容所有罪恶。
“阿爸!如果六只手趁天黑赶走羊群,我们也看不见啊!”次松次仁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忧。
“赶走差不多十只羊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儿动静,它们会发出咩叫声。”次松次仁发现冷风改变了父亲的声音。
“再说六只手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偷,他知道我们暗中埋伏,今晚可能不会把羊赶出来。”父亲一边拧着次松次仁上衣的雨水一边说。
“阿爸!有点儿冷。上衣您穿上吧!”说完次松次仁就感觉有点儿不自在了。他们父子几乎没说过一句带温度的话。他和父亲的对话一直都是男人对男人的,近似于两个外交官之间的“谈判”,理性而克制。他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就成了这样。一直以来,父亲也从不把他看成一个孩子,家中所有大事小情都会平等地和他商量。所以,他从小就开始说“大人话”了,长大成人的过程可能就是语言的变化了。
“我不冷。要特别注意雨后的这股寒风,它叫‘雨风’,以前有人就在这种雨风中冻死过。你穿上。”饶丹把上衣披在了次松次仁身上。穿上湿漉漉的上衣,次松次仁就听到从山谷中传来风的呼啸,他感觉上庄山谷的所有空间都被一股强风所占据,如同一股江水在山谷激涌而下。
“这风声好大啊!羊叫了也听不见啊。”次松次仁再次说出自己的担忧。
“这风实在可恶。不过它会吹走乌云,如果头顶的乌云被吹走,就会看见星星和月亮。那时,六只手就没有夜色的掩护了。”父亲说了一句非常睿智的话。
“阿爸,鲁亚也被偷走了。谁会偷走一只放生羊?”想起鲁亚,次松次仁忧心地说。这位牧羊人,没能保持住把话装在心里的内敛。
“人没有羞耻是狗,狗没有尾巴是鬼。亚囊上庄的那些小偷怎么会听道理,尤其是六只手,他本就是个无恶不作的人。如果会看是不是放生羊,他就不会这样偷东西了。”听了这话,次松次仁心情更加沉重了,似乎有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压了上去。
“只有两只手的人被叫作六只手,他可是个不一般的小偷。”父亲说完沉默了。次松次仁也不说话了。
沉默中,次松次仁想起自己丢失的那些羊,尤其想念鲁亚,想起鲁亚的通人性,想起在山顶靠着它睡觉时的温暖,想起他给它喂食时鲁亚用湿润的嘴唇触碰他手指的情形,每当呼唤它,它便咩叫着从远处朝他跑来。一想到心爱的鲁亚可能被困在一处黑暗里承受苦难,就像他现在一样,而他对能否找到它毫无把握,他心中就生出一丝悲凉。
过了一阵儿,如父亲所料,头顶的乌云被吹到了东边,蓝黑的天空闪起星星点点。不久,一轮满月终于从东边的乌云中挣脱出来,高悬在村庄上方。从村里人家窗户透出来的灯光陆续变暗了,村边六只手家的灯光也熄灭了。
“不听老人言,必有恓惶泪。倘若你以前听我的话把羊卖了,现在就不用吃这样的亏。”父亲朝次松次仁埋怨道。
次松次仁没搭腔。关于卖羊的事他们父子有过几次争论,每一次都是次松次仁败下阵来。“你看看别人。”父亲讲周围村子里有人卖了羊群,买了汽车,还有的到外地打工,讲的都是身边熟悉的真人真事,也就特别有说服力。有的人刚在外面待了一两个月,他发财了的消息就传回到村里。有的没有牛羊的家庭,现在也过得富足了,还变成了有汽车的富人。所以父亲经常说:“你看看别人。别整天跟在羊屁股后放羊了,你应该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去外面见见世面。”听父亲的语气,那些人好像不是外出打工,好像他们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就有钱自动落入口袋。
次松次仁不想把自己的羊群卖掉,他从七八岁开始就跟在这群羊后面,高中没有毕业就自愿留在家里当起了牧羊娃。那时父亲也没要求他继续上学,他就一直过着放牧的生活,一年四季,日复一日。长年一个人放牧,次松次仁的话渐渐变少了,性子也变得慢了。村里的羊一天天减少,人们后来就不叫他真名,改称他“牧羊人”了。家里人看不过去,也觉得他应该像“别人”一样,卖掉羊群去外面闯闯。然而,次松次仁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他心想,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不可能轻轻松松做到衣食无忧。再说,“外面”对他来说太遥远,他想象不出一点儿能吸引他的细节,更别说好处了,脑海里浮现的,只有出去就不得不面对的艰辛。起初,他对劝说他的人解释,要赶着自己的羊,唱着自己的歌过日子。慢慢地,也就不愿意再多费口舌了,人们觉得他当牧羊人当得太久了,现在变成了一个傻子。
“阿爸。你饿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饿也要忍着,干粮不能吃完。我们要在这里盯很长时间。”父亲说,“至少明天一整天不会有人送食物来。”
“我还剩很多干粮呢。”次松次仁打开随身的干粮口袋,从里面拿出一块馍馍说。
“你母亲说你饭量很大,是不是老拿干粮喂鲁亚?”父亲语气中夹杂着责备,“用馍馍喂它,让它变胖,屠夫就会第一个宰了它。”
“……”
次松次仁还是没有搭腔,父亲的话刺痛了他。他想立刻起身冲进六只手家,眼前的村庄仍旧一片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6
第二天,黎明的曙光在东方天地间划出一道明暗界线。没过多久,一束耀眼而温柔的阳光照在次松次仁脸上。饶丹黎明前就已越过赛青冈回家了,他计划今晚给次松次仁送被褥和干粮来。
“小偷不会在白天赶羊出门,所以今晚非常关键。”父亲接着说,“你守在这里不要动,小偷可能也在观察这边。”
饶丹走后不久,次松次仁拿起望远镜从晨光中将山下六只手家里里外外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一缕轻柔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他感受到一股湿气正慢慢从骨肉皮肤间抽离,而且亲眼看到从自己的上衣冒出了一股热气。过了一阵儿,他又看到亚囊上庄的房屋顶上挂着的经幡和泛黄的树叶上裹上一层金黄的光晕,几个烟囱已经冒出了如柱的青烟。这个时候,好几户人家的妇女已经开始烧火做饭了。
又过了一阵儿,六只手家的烟囱还是没有冒烟。次松次仁有点儿着急,他在等着六只手起床,等着他从家里走出来。如果那家伙出了门,就说明昨晚他没有趁着黑夜把羊赶出去,那样次松次仁就能安心一些。
亚囊上庄的房屋在这个深秋的清晨里,舒缓而安静。次松次仁看见有的人家门口的看门狗在摇尾巴,时不时地还能听到狗吠声。前后两座山都是岩石山,亚囊上庄就坐落在这个狭小的山谷中。这个清晨,次松次仁像一名哨兵隐蔽在山腰的土坳里,用望远镜将亚囊上庄的动静尽收眼底。
六只手终于出现了。
他身披藏袍,伸着懒腰走出了房门。这个远近闻名的六只手不高不胖,外表普普通通,没有任何突出特征。次松次仁曾在新年赛马会上见过他,当时他骑着一匹黑马经过,身边的同村人告诉他,“这就是六只手。”当时他心想,小偷都能这般威武吗?他提出自己的疑问,同村人说:“身体是鬼,衣着是神。今天这人穿了一件好衣服,再骑上黑马,小偷也能威风八面啊!”另一个人接过话茬儿:“没什么可羡慕的。从头到脚都是偷来的。”看来正如人们说的,“衣着是神”,现在他穿着普通的藏袍,平平无奇。
六只手在门口撒了一泡尿,之后抬头朝前面的岩山眺望片刻。虽然有些距离,但从望远镜中能清楚地看见那家伙的脸,次松次仁赶紧低下了头,不过马上又想到,六只手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视力。这座被视为亚囊上庄神山的红色岩山高耸巍峨,相比之下,他只相当于一只蚂蚁的大小。神山能够而且已经将次松次仁掩藏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又拿起了望远镜。六只手依旧站在原地望着这边,他似乎真的察觉到了什么,次松次仁又一次把头低下了。当他再抬头用望远镜看时,只看到六只手的背影消失在他家房门背后。
“小偷!”次松次仁不由得嘟哝了一句。他仰身躺下,天空犹如连夜被擦拭干净的镜子,蔚蓝清澈。在山上放牧时,次松次仁喜欢这样躺着盯着天空看,看得久了,感觉这镜面上会突然映出自己的身影。现在他更希望天空真的是一面镜子,那样即使他现在这样躺着,也能看到六只手家的动静。
如果运气好一点儿,兴许还能看见被圈在门口牛圈中的鲁亚和另外的那些羊。
太阳一点一点升起来,次松次仁听见从自己肚子里发出的声响,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儿母亲做的油馍吃了起来。塑料瓶中的水早已喝完,他的嘴唇已经开始干裂脱皮了,每咽一口干硬的馍都要费一番力气。这块儿馍馍本来是留给鲁亚的。他想起鲁亚嘟着羊嘴吃他喂的馍时,唇齿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吃完了还用嘴拱着他的手,继续索要。要是不理,它会用羊角触碰装着干粮的口袋,蹄子焦急地跺着地面。“如果不抑制自己的食欲,黑暗的肚子是无法满足的。”每当这时,次松次仁就会摊开自己的双手,说一句从父亲那儿学来的谚语。鲁亚也会像听懂了一样,安静下来,卧在地上反刍。当他轻轻抚摸鲁亚洁白的羊毛,它就像一个被宠溺的小孩子,眼中泛起幸福和安逸。想到鲁亚和丢失的羊现在可能没有吃食,没有水喝,次松次仁就没有了食欲。鲁亚,饿了你就大声叫吧,只要你叫,我就一定能将你找到!
7
到了中午,次松次仁真的听到了一声咩叫,他赶忙翻身拿起望远镜向亚囊上庄环视了一番,但没有任何发现。最后他锁定六只手家,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没有人出门,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他只好又仰身躺下了,心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咩——”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一声咩叫。
这回他感觉不是幻听,立马又爬起身拿起望远镜观望。秋末的村路空空荡荡,小孩儿们去县城上学了,大人们出去打工了,牲畜基本上都卖掉了,村子里不再有嘈杂声,安安静静。屋顶的经幡懒懒地飘着,一两个烟囱冒出断断续续的青烟,看门狗在打盹。他企图找出叫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是自己丢失的羊群在六只手家里发出的哀鸣吗?他差点儿朝向村庄大声喊出了鲁亚的名字。
“咩——”叫声再一次响起。这次次松次仁发觉声音不是从村子里传来的,而是来自村后的岩山,而且不是绵羊的叫声,是山羊的声音。
次松次仁对面亚囊上庄的后山与前山不同,陡峭的岩山直入云霄,像是大地燃起的一股火焰,一直烧到天际。陡峭的红色岩山上有许多山梯和沟壑。次松次仁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突然,在一块石阶上发现了一只黑色山羊,正朝这边咩叫。石阶在陡峭的山崖上,石头周围的青草已被山羊吃完,一点儿不剩。根据他的经验,那只山羊应该是追着青草不知不觉走到那里的,然而现在它前面没有路,脚下的平地也窄得无法转身了。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山羊被困岩山,就如同一个利欲熏心的人走上歧途,最后让自己深陷困境。山羊似乎已经在石阶上困了好几天了,断了水草,看起来很虚弱。
这山羊看起来是没救了。它自己走上了绝路无法逃脱,朝眼前的亚囊上庄发出求救的哀鸣也无济于事,没人会不顾自己的性命爬上岩山去救它的。它只能在那块儿巴掌大的岩石上等待死亡。可能是昨晚的雨水温润了它干渴的喉咙,现在又能发出求救的叫声了。几声咩叫似乎耗尽了山羊最后的气力,现在它只是伏贴在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村子的方向。
次松次仁用望远镜朝对面的岩石看了很久,心想有情众生实在可怜,为一时饱腹竟导致断送性命的后果。如果是在村里,他说出“有情众生”这样的话,村里人就会嘲笑他,拇指般大小的人儿讲出天大的道理来了。他不想理会那些说他的人,心想是他们不懂得他的心。他虽然年纪还小,但觉得在山上度过的放牧日子让自己真正地成熟了。他觉得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心怀变开阔,目光变长远,而不是像村里人那样,年纪越大,心却越狭窄,目光也只能看到眼前了。人们把时刻计较得失,为眼前的一碗饭打拼叫成熟,令他心生怜悯。这就是他对“有情众生”的怜悯。山上广阔的空间拉长了他的目光,无边的大地抹平了他内心的波澜,让他的心容得下天地间的一切躁动,回归宁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渐渐变得少言寡语了。
次松次仁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被困在岩山上的羊将要饿死,一边惦记着自己丢失的羊群,尤其是鲁亚,它们现在也可能正在忍受着饥饿之苦。鲁亚一直都是他用干粮喂大的,怎么忍受得了没有食物的痛苦呢。想着,他又去看六只手家,他不知何时出的门,正站在禾场上仰头望着后山。看来他也发现了被困的山羊。次松次仁心想他是不是正在等待山羊断气掉下悬崖。
……
注释:
①拉则,藏族地区山口、山坡、主峰、边界等处用石、土石所堆砌的石堆,其上插有长竹竿、长箭、长木棍、长矛,还拴有经幡。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徐海玉)

拉先加,藏族,生于70年代末,博士,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大学开始藏语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五十余篇(首),出版文学作品7部。2019年,短篇小说集《睡觉水》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先后五次获得“章恰尔文学奖”,是此奖项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作家。作品多被收录于藏族当代文学的各种文集,并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其中长篇小说《成长谣》由日本星泉女士译为日文出版,成为第一部被译为日文的藏文长篇小说,该小说2021年还被译为法文在法国出版。

增宝当周,藏族,青海黄南人,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汉藏文学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