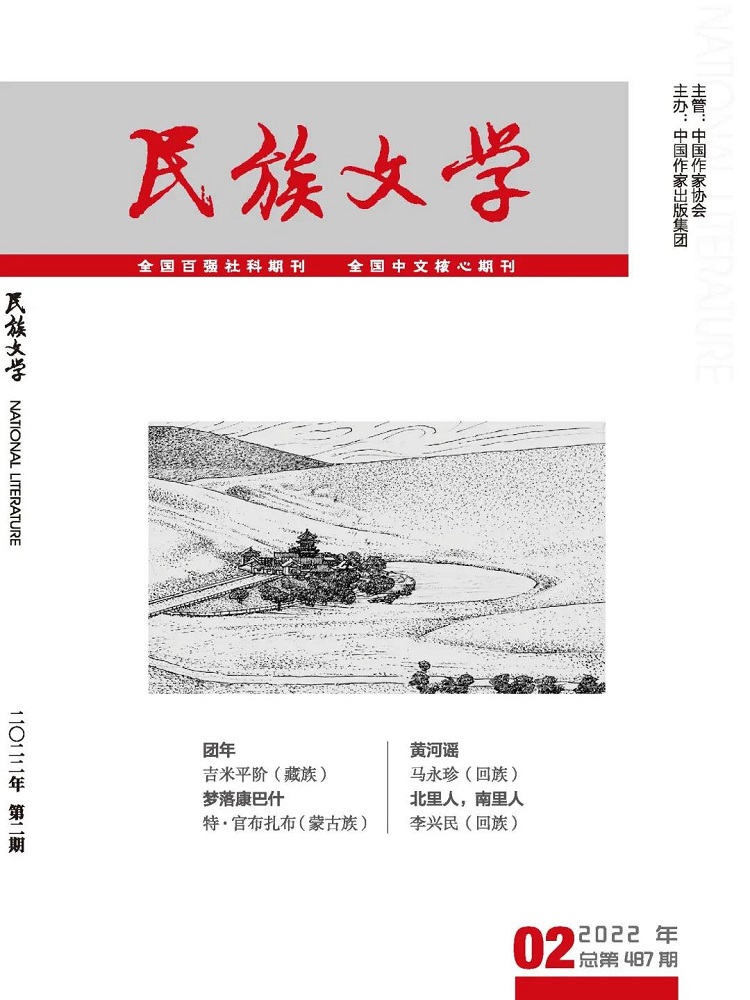
一
快到年关,下村的年味儿也渐渐浓厚起来。
好像越是快到年关,没干完的活儿越多。这不,阿妈刚刚在院子里指挥着家里老二和来帮忙的邻居拥西,把拆洗的一大堆被褥和藏毯晒到院子里的铁丝上,一进厨房,就看见对面墙上的木台上,那几排大小不一的汉阳锅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汉阳锅是一种铝制的平底锅,大概最早是在湖北汉阳生产的吧。那些汉阳锅,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个个黑得快要流油了。如果不把汉阳锅刷洗得锃亮,那叫什么过年呢。阿妈从厨房的窗户里伸出头,叫正在院子里跟拥西说笑的老二赶紧去把汉阳锅刷洗出来。
老二从晾晒的被单后头答道:“您两个儿子不是就要回来了嘛,等他们来刷!”
“天晓得他们啥时候才到,电话里又不说清楚,你不要啰唆了。等会儿拥西要帮我擀面翻花茹,你又做不好。”阿妈说。
老二放下手里的活儿,嘟嘟囔囔去厨房,搬出大大小小十来个汉阳锅,在院子里的水池子里泡上,转眼,人不知哪里去了。
拥西进门来,见阿妈已经在厨房里摆开架势,准备要炸花茹。
花茹是一种油炸馃子,下村过年必备。炸花茹既是过年的准备,又是过年的开始。以往,过年炸花茹,是很隆重的事情,一家人无论大小,围坐在一起翻花茹,家里主事的拿着长长的竹筷,在翻腾的油锅里查看花茹的成色,很有架势。
上好的花茹,要在面粉里加鸡蛋、酥油、红糖,擀成黄豆薄厚的面皮,涂上玫瑰花瓣泡出来的食品红,撒上豆粉防粘连。翻花的时候,对折成两三指宽的两层,切开,再在折缝处切出连接的细条,六七八条不等,做成花瓣花茹。做花瓣花茹一定要在接口的地方涂点儿糖水对接粘牢,再翻出五瓣六瓣七瓣等各色花样,下油锅炸透,捞起来放在竹筲箕里。还有一种蝴蝶花茹,做法就简单多了,把涂抹食品红的面皮卷成圆筒,切出半厘米薄厚的圆片,放平两手一捏,就成了蝴蝶形状,精细点儿的再在下方捏出两个小尾巴来,就更神似。
花茹焦黄香酥,作为过年的上等贡品,神龛前必不可少,供奉,祭祖拜佛。家里来客人,摆上一盘,格外增色。花茹既可当糕点,还可以解饿,早餐时抓出一盘花茹泡酥油茶,也是很好的,特别是蝴蝶花茹,酥油茶泡出来,又酥又软,香甜可口。过年,下村再不济的人家,也要炸几斤面粉的花茹。
今年阿妈的花茹炸得多,光面就发了满满两大面盆,还专门去县城买了一米来宽的擀面板,客厅里的藏桌已经擦得干干净净,预备着放翻好的花茹。
阿妈家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了。
自从老大结婚以后,回家过年就稀松,老三高中毕业出去打工,已经有三四年了吧,全家没有在一起团过年。今年,阿妈早早就给在外面的老大老三说了:天大的事情放一边去,一定要回家过个团圆年!还有一层意思她没有说,初二是他们阿爸70岁生日。
想到老头子,阿妈停下来听听动静,知道他肯定又去村委会扯闲篇去了。从乡小学退休下来,老头子完全不适应闲适生活,不像其他老人,去村头的甜茶馆喝喝茶、打打牌、转转经,不然出门旅游也行,他不,整天跑到村委会找那些驻村干部东拉西扯,好在他对村里的情况了解得多,驻村工作队经常有求于他,倒也自在。
阿妈想叫老二去把老头子叫回来帮忙翻花茹。别的事情他干不了,一辈子拿粉笔,地里家里的活儿,都是她和家里的几个孩子干了,不过像翻花茹这样的细巧活儿,老头子还是得心应手。
阿妈看院子里的水池边,只有水管汩汩流着,不见老二人影,她对翻花茹的拥西说:“你看,这么大的人了,屁股还是坐不稳。”
拥西说:“她老公小廖不回来过年吗?好长时间没看见他了。”
“不晓得。这些年总加班,难得回来住几天。”阿妈说。
“他们这样子,啥时候才要得上小孩。”拥西说。老二结婚也快十年了,翻过年就是本命年,往四十奔的人了。
“就是啊,我看她倒是不操心,整天嘻嘻哈哈。”阿妈说。
“要说人家小廖也不容易,当个副乡长,整天忙得跟跑山神一样,啥事情都跑不脱。”拥西是本乡卫生院的医生,老二的丈夫廖志远在金沙江边的白玉乡当副乡长。今年,江边泥石流形成堰塞湖,全乡干部在山上当了两个月的山大王,等到泄洪结束老百姓都回到家他们才“解放”,这两年又是安居房改造,又是脱贫攻坚摘帽,真是忙得够呛。
“我们小廖就是哪个都能支使,窝囊!”阿妈这样说,语气里却透着自豪。
“人家好歹是乡领导呢。”拥西说。
正说着,阿爸溜达着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捆碧绿的油菜,说是村委会温室里种的。
“你咋个不在村委会吃过午饭才回来呢?”阿妈调侃道,又问,“看见老二没?”
阿爸说:“我这里有家有室,好意思在人家那里吃午饭?人家的饭钱也是有数的。”又连忙说,“拥西留下来吃饭啊。”
“还用你说?正好来翻花茹,我还说叫老二去找你。”阿妈说。
“我看见老二往乡政府那边去了。”老头子说。
“你看这半截子活儿,汉阳锅还在那里堆着呢。”阿妈抱怨道。阿爸连忙说:“我去洗我去洗。”说完放下手里的油菜忙着刷汉阳锅去了。阿妈看着老头子的背影对拥西说:“这女儿都是被他惯坏了。”
还别说,老二从小到大,阿爸就没有动过她一根毫毛,村里的人都说,这个在全乡(过去叫公社)都出了名的坏脾气,有了老二就变了。
二
下村四十多户人家,这些天,家家都有在外工作或者打工的人回来。
虽说现在的生活天天像过年,但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村边小河沟总是热闹非凡,家里的小媳妇、未嫁女都在那里叽叽喳喳,洗各种东西。其实现在每家都通了自来水,聚在河边的性质,更多是交换些家长里短。而水泥铺就的小道,通到了家家户户,每家人都把家门口冲洗干净,在大门上换上新香布,就是那种藏式的门楣帘。
这个靠近金沙江边,错落在山坡上的小村子,冬小麦已经油绿绿长出来了,不时有小孩子放几个二踢脚,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硝烟味儿。
阿妈今天主要的事情,就是准备古突夜(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晚上)的东西。
古突就是一种面疙瘩汤。做古突时,会在面疙瘩里包上各种不同的小东西,都有不同的含义,谁吃到什么,或者象征他的性格,或者预示来年的运气,是一种轻松欢乐的饮食文化。
阿妈把准备包在面疙瘩里的干辣椒、木炭块、羊毛一类的小玩意儿都找出来,放在一个瓷碗里。切玛盒、养着青稞苗的罐头盒子、彩绘羊头这些东西都早已备下,花茹炸了整整三大筲箕,还不包括送给拥西家的。
天气很好。偏西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有点儿发暗的厨房里,分散成许多细小的光柱,一些平常看不见的尘埃在光柱里飞舞,好像快乐的小精灵。这个时候,连村子里的狗都不叫,院子里的藏狗孔老五也懒懒地趴在门槛后面眯着眼打盹,俩眼眉上的黄点,在阳光的照射下,倒像是睁着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
老二一大早就去白玉乡看老公去了。
老二的老公廖志远是阿坝汶川人,“5·12”大地震时在汶川一个学校教书,忙着抢救学生,家里双亲都遇难也没顾得上,重建开始,小廖再也无法在那里待下去,报考了这里的公务员,分配到白玉乡工作。因为肯吃苦心眼儿实,现在已经是副乡长了。
阿妈经常为有这个女婿感到安慰。家里老二也不知像谁,在县里读完初中死活也不愿意继续上学,那些年跟着几个姐妹在成都的宾馆当服务员,跟小廖谈上恋爱。这桩婚事老两口还是相当满意的,小廖对老两口很尊重,老两口也把他当亲生儿子。结婚后,老二就回来在乡小学打小工,离家也就几公里,经常回来住,这样老两口身边也算有个照应。
说起来,这个家在下村,甚至在全乡,也都是让人羡慕的。老大上学时,阿爸还在乡小学教书,那时候精力旺盛,把儿子的功课抓得紧,老大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州里的单位,娶妻生子,现在是什么副处长了。女婿是乡干部。老三现在在拉萨打工,听说也混得不错。阿爸在村委会进进出出,不时会有人对他恭维几句,这也是他愿意往村委会跑的动力之一吧。
肯定,他现在又在村委会的院子里。
阿妈到客厅看看挂钟,摇头叹气。老大今天一早就来电话说出发了,还说大门和厨房的吉祥图都等着他来画,现在还没有音信。老三前几天电话里说是跟几个朋友开车从川藏线出来,按说也该到了。
听着挂钟嘀嗒嘀嗒的声音,阿妈心里七上八下。这时,大门口响起了汽车刹车声,阿妈赶紧迈过孔老五的狗头,往院子里迎去。院门打开,白玉乡的朋友送女儿和女婿小廖回来,老二手里提着几个点心盒子,小廖扛着一箱啤酒。
“小廖,不是说今年过年值班吗?”阿妈问。
小廖说:“是值班,我们书记说今天是古突夜,让我回来陪老人,明天大年三十他回去过年,我去替他。”
“那就好那就好。”阿妈搓着手说。
放下东西,小廖挽起衣袖进到厨房准备帮忙,看见厨房里堆着的东西,吃惊地叫了起来:“妈呀,您准备这么多东西,这得吃到什么时候?”
他还没看见厨房旁的食品仓房,这里光是肉食就有猪牛羊鸡鸭鱼,还有香肠腊肉各种罐头,和血肠风干牛肉,更别说其他的蔬菜干鲜果品,林林总总堆满一屋。阿妈说:“今年好不容易大家都回来,我还嫌不够哪。”
小廖摇头道:“您这得花多少钱呀。”
阿妈说:“你阿爸的退休工资,每年都涨一点儿,我今年还卖了两头猪。”说完推小廖进客厅,“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你就歇歇吧,等老大老三到家就开始做饭。老二,给你阿爸打电话,叫他回来和小廖他们先喝着。”
三
老大和老三差不多前后脚进的门。
老大开着两年前买的国产越野车,还没到家门口就开始摁喇叭,孔老五听见动静,一跃身爬起来往大门口跑,阿爸也放下酒杯急匆匆往门口赶去。
此刻那辆白色的越野车已经停在大门外,首先下来的是孙子,因为两年没见,长高一头的孙子有点儿腼腆地跟爷爷问好,然后跟藏狗孔老五搂在一起。
“跟你说做人不要张扬,两里地以外就听见你来了。”阿爸有些抱怨地说。
“不是想通知你们一声嘛。”老大不以为然地说。这时老大媳妇从车上下来,手上脖子上耳根上金光闪闪,大概车里很热,鲜艳的上衣敞开着,露出丰满的身材。跟阿爸打完招呼,老大媳妇就忙着指挥从车上往下搬东西。
“又买这么多东西,哪里吃得完?”阿爸看着院子门口包装得花花绿绿的一堆,摇着头说。
此刻阿妈、老二和小廖都从屋里出来,阿妈说:“不着急搬东西,先进屋喝口热茶。”
老大媳妇说:“还是先收拾停当,不然车没地方放。”
因为下村地形不平整,能停车的地方很少,这些年,开车回来过年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时候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阿爸之前跟村委会打过招呼,在村委会里预留了一个车位。
搬完东西,阿爸带着老大停车回来,阿妈已经张罗了一桌子酒菜,老大媳妇也换了一身衣服从楼上的卧室下来,大家围着藏桌坐下,阿妈问:“咋个顶着年关才回来?”
老大媳妇说:“还不是您儿子,今天早上还到单位去了一趟,不是我催着,现在还到不了呢。”
“有那么忙?”老二问她哥。
小廖说:“大哥是单位领导,忙是肯定的。”
老二撇了撇嘴:“都像你,攒笨的料。”
小廖住了嘴,阿妈招呼大家吃喝,突然想起来说:“阿牡丹今年该高考了。”
“就是啊,最要紧的时候,你们非叫回来。”老大说。
正跟爷爷说话的孙子阿牡丹此时插嘴道:“也不在过年这几天。”
老大横过去一眼:“这个时候分秒必争,你看你这个不上进样,不要像你叔叔,考成高考次数状元。”老三高中毕业后复考了几年没考上,老大着实有点儿看不起他。
“哪个兴在背后说人坏话。”话音刚落,老三推门进来。
“你个短命的……”老二看见老三进来,站起来就叫,说到这儿,意识到现在是过年,赶紧把话音咽下,迎上去说,“还是鬼鬼祟祟的。”老二和老三从小一起长大,说话没遮拦,看得出他们感情很好。
门口的老三双手一摊:“院子门就没关。”说完往后面招手。
随着老三的招呼,从门外怯生生挪出来两个人,一个年轻女子,手上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儿。已经起身的老两口身子僵在那里,向老三投去询问的目光。
“这个是德吉,还有她女儿云珍。”老三介绍说。
“哎呀呀,这个孔老五越来越不懂事了,来了客人也不吭一声。”老大媳妇怪罪着藏狗,随后又热情地对怯生生的母女说,“快进来快进来,一路肯定辛苦了。”
一家人如释重负般纷纷起来让座,阿妈说:“还是请客人先洗漱一下吧。”说完用眼神儿示意老二带着母女俩去洗漱,老二本来有一肚子话要问老三,此刻万分不情愿地领着德吉母女去了卫生间。
待她们看不见身影了,阿爸问:“这是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呀,女朋友。”老三轻松地说。
阿妈忍不住问道:“你的女儿?”
“说什么呢?这小孩儿多大了?”老三说。
“啊?找个二婚的,还‘买一送一’。”老大说。老三很不高兴地看老大一眼,转过头去。
“这个……德吉,你是认真的?”阿妈小心翼翼地问。
“不认真我带回来?”老三说。
“她是哪里人?家里情况你了解吗?爸妈是干什么的?”阿爸插进来问。
老三说:“家是拉萨的,她爸妈我都见过了,挺好。”
“那在电话里不提前说一声。”阿妈说。
“电话里又说不清楚。”老三说。
“按你说的,不是几天前就跟几个朋友开车过来吗?”阿爸问。
“加上她们两个车坐不下。她们也是临时决定过来的,只能赶长途车,所以耽误了。”老三说。
“那小孩儿怎么回事?”老大媳妇好奇地问。
“没怎么回事,就是德吉的女儿,一直跟着她。”老三说。
“那她的父亲呢?”老大问。
“不知道,没问。”老三说。
“这个人……”老大环顾四周,见没人理会,自言自语道,“太不负责任了。”
老三想要搭言,阿妈见不是个事儿,圆场道:“老三你不提前说一声,这多失礼呀。”
“反正要成一家人了,不用那么客气。”老三故作轻松地说。
四
古突之夜的气氛,由于德吉母女的到来,有点儿沉闷。
本来,下村人对过年吃古突,可有可无,这个风俗也是生活富裕以后兴起来的。有的家庭早在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张罗晚饭,到天黑时都喝差不多了,加上当地习俗,大年三十早上,家家户户都要上山扫墓祭祖,所以许多家庭吃完晚饭,看会儿电视也就睡觉了。
阿妈家不一样。阿妈年轻时从江那边嫁过来,之前过年一直要过古突之夜,到了这里二十九不吃古突,很久不习惯,所以,下村开始过藏历新年,她就积极推行吃古突。今年的春节和藏历新年正好在一起,加上儿女们都回来,就更搞得隆重些。
还在晚饭时分,为了调节气氛,阿妈让老大带着儿媳妇和孙子,在厨房和家门口,用糌粑和石灰画吉祥图案和符号,她带着德吉和老二准备做古突的面汤,客厅里只剩下阿爸、小廖和老三喝酒扯闲。
“老三你应该经常给家里来个电话,爸妈平时常念叨你。”小廖酒量有限,几杯啤酒下肚,就开始跟小舅子掏心窝。
“来电话就听他们唠叨。再说平时也没时间。”老三说。
“没时间?你现在在忙啥?”阿爸问。这个小儿子从小不听话,因为是家里最小的,舍不得严管,结果高中毕业考了三年,连个技校也没考上,前几年去拉萨打工,平常也没有几句真话给家里。
“反正有我的事情。”老三不满地说。
“你把人家母女两个带回来,拿什么对人家负责?”阿爸也有些不高兴了,他觉得这个小儿子吊儿郎当,管自己都困难。
“这个不用担心,我又不会问你们要钱。”老三说。
“老三,阿爸也是为你好,少说两句。”小廖说。
几爷子在这里拌嘴,那边老二早把老三在拉萨干什么、混得怎么样,从德吉嘴里套得清清楚楚,原来老三先跟几个人合伙开旅游车,这几年拉萨搞供暖工程,又跟着几个人在做供暖,干得好像还不错。德吉嘴甜,没少说老三的好话,加上有一个小女儿云珍在身边晃着,几个女眷周围的气氛慢慢轻松起来。
大号的红双喜高压锅里,骨头汤里加了牛肉碎、萝卜丝的古突开始冒气,牛肉萝卜混合的面汤香味儿弥漫出来,连刚刚喝得有点儿上头的阿爸,都从楼上的卧室里踱步下来。数着人头,阿妈把10个金边瓷碗摆好,把藏狗孔老五的饭碗也准备好,开始给高压锅浇水冷却,老大媳妇和老二在旁边打下手,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盯着她们操作。
今天晚饭的座位是这样的:藏桌在客厅正中靠着北墙,由三张雕花小方柜组成,两边是两张藏床,阿爸和老大分别坐在藏桌北边的两头,孙子阿牡丹坐在爷爷旁边,老三和德吉母女紧靠着坐下,老大旁边给老大媳妇留着,然后是老二小廖,藏桌的南头是一个四方火盆,高压锅从厨房煤气灶上端出来就煨在火盆上,阿妈在南头忙碌,座位也在那里。
这会儿,热气腾腾的突巴(面汤)已经上桌,桌子中间还摆着晚饭时剩下的一些凉菜,卤牛肉、香肠腊肉之类,最显眼的有两盘红彤彤胖乎乎的辣椒,是这里有名的醋海椒,最配面食。
也许刚才只吃菜喝酒了,一家人也不多话,各自端着碗拿着小勺呼噜噜吃起突巴来。阿妈给孔老五端了突巴回来,坐下说道:“你们吃慢点儿,里面还包着东西呢。”
一句话提醒了大伙儿,都在碗里边吃边找。
五
做古突德吉在行。在拉萨日喀则一带,家家妇女都懂得做古突,当然,每家在面团里包的东西不尽相同,所以说辞也都不一样。刚才,德吉不仅包了阿妈准备的那些东西,还用面块捏了太阳月亮、小狗小人混在里面。
大家正认真吃着,老大媳妇夸张地惊叫起来:“看我吃到啥了?”
大伙儿都抬起头,老大媳妇用勺子高高挑起一撮羊毛,左顾右盼。
吃到羊毛代表心肠好,大家纷纷夸她,阿妈看了看,说:“你们不要‘只顾人家碗里的菜,不管自己碗里的肉’。”
大家又都认真在自己碗里挑起来。
一会儿,叫声此起彼伏,所有的人都有发现,阿牡丹把手举得老高,说吃到了一粒玉米。大家都看着阿妈,因为过去没有包过玉米。原来,在刚才做古突的时候,德吉告诉阿妈,说现在他们那里都不包羊毛,嫌吃到嘴里不舒服,用玉米替代了。
这时候阿妈愣了愣,德吉说:“真是好兆头,玉米代表强大的心脏,说明这个人宽容善良,还有,玉米节节高,说明今年高考考得好。”
老三说:“你还懂得挺多。”
阿妈意味深长地看了德吉一眼,德吉旁边坐着的云珍也跳起来说:“我吃到一块糖。”
德吉说:“云珍啦就是嘴甜。”
老二听德吉用敬语叫自己的女儿,说:“你们那里的人奇怪得很,跟自己的女儿都说敬语。”
老二刚才吃到了一块瓷片,瓷片象征游手好闲,大家为此取笑了她半天,这会儿她有点儿不高兴。
德吉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阿爸插话了,阿爸说:“给孩子说敬语好,教育他们从小就懂得互相尊重。”
大家都把各自吃到的东西吐出来,放在自己跟前的纸巾上,什么辣椒呀、木炭呀、人参果呀、青稞粒呀,人参果、青稞粒代表有口福,木炭说人狠心黑,辣椒表示此人说话尖酸刻薄。每吐出一样,就会迎来一家人的品头论足、哄堂大笑,气氛越来越热烈。说也奇怪,这些打趣的象征物,好像总是和吃到的那个人性格有几分吻合。
“啊呸呸。”阿爸小心翼翼从嘴里掏出一包东西,放在面前,阿妈一看乐了:“哎呀老头子,你吃到了最吉祥的东西,代表我们全家今年都丰盛,取不尽,用不尽。”
“那是什么?”小廖问。
“一包盐!”阿妈开心地说,然后一边伸长脖子四处看,一边自言自语,“包的黑豆子没有出来。”原来,黑豆子象征小气、吝啬,被老三吃到,悄悄咽了。
六
德吉看出了老三的小心眼儿,又不便说明,就说:“我吃到了小面人,该我出节目,我给大家唱个歌吧。”
阿妈说:“也是,说不定我舀给孔老五了。孔老五就是个小气鬼。”又说,“今天大家肯定吃到了好多代表吉祥的太阳月亮,都是德吉捏的呢,现在请德吉给我们唱歌吧。”
德吉唱了拉萨流行的酒歌,接着大儿媳妇、小廖都唱了各自家乡的歌,反倒是阿妈一家子,没有人出节目,阿妈说:“老头子,这下该你表演了。”
阿爸抹抹嘴,起身上楼拿了一把胡琴下来,抹松香、调音,认真捣鼓了半天,拉起了下村著名的弦子。
悠扬的琴声响起,一下子就让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生动起来。阿爸陶醉地随着琴声晃着脑袋,不知什么时候,桌上的人,除了德吉母女和老三,都在客厅的另一头拉起圆圈跳了起来。
年幼的云珍好奇地张大嘴巴:“阿妈啦,他们都会跳耶。”
“他们还都会拉琴呢!”德吉说。
果然,几首曲子过后,趁阿爸为了防止琴弦划伤手指关节,往左手食指中指上缠胶布的时候,老大拿过胡琴拉起来。他拉的风格跟阿爸不太一样,欢快中带着一丝急躁。女婿小廖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把胡琴,在圆圈里边拉边唱:
长在石头上的神树,已过千年万年,
我们慈祥的父母,希望也这样长寿……
一边是丰盛的餐桌,一边是欢快的弦子,火盆里炭火熊熊,在这个温暖的冬夜,这样的场景,让人感觉好幸福呀!
云珍兴奋地在弦子队伍里,一会儿跟这个模仿几步,一会儿又蹿出来找吃的,阿牡丹从舞蹈的圆圈里出来,这会儿已经完全投入到和同学的手机联机游戏里,周围的音乐歌舞对他毫无影响。
老三凑近德吉的耳朵:“我没说错吧。”老三曾经跟德吉夸耀,说他们那里的人,只要是男人都会拉胡琴,只要是女人都会跳弦子。
德吉推老三起来:“你也去跳呀,一家人这样,多好。”
老三轻蔑地撇嘴:“我才不跳这些老土。”
德吉没办法,站起来往厨房走,老三追上去问她干什么。
“我去做驱魔用的糌粑。”德吉说。
老三拦住她说:“我们这里不兴这个。”
德吉说:“刚才我已经问过你阿妈了,阿妈说可以。”
歌舞尽兴了,吃古突前的酒也消散得差不多了,阿妈说:“德吉今天带来了拉萨的风俗,我们也都祛祛一年身上不干净的东西,图个吉利。”说完拿起德吉准备好的糌粑团,在身上四处滚擦一遍,啐三口唾沫,扔进大家吃古突后倒残汤剩水的砂罐里,大家学着阿妈的样子,纷纷拿起糌粑团,老二一边滚擦一边叨叨:“净整这些没用的。”
小廖说:“这就是图个吉利,给过年增加点儿仪式感。”
都扔完了,足有半砂罐,阿妈叫孙子:“阿牡丹,跟你叔叔去把它丢村口垃圾桶去,记住丢了不要回头啊。”
德吉挺好奇地问:“大哥儿子怎么叫阿牡丹呀?不是本名吧?”
老大媳妇说:“他叫洛桑次仁,小的时候我们忙,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那时候也没什么娱乐,天天听广播里蒋大为唱‘啊牡丹’,就学会了,到哪里都唱,结果叫名字没人认识,叫阿牡丹,都知道是他。”
阿牡丹正忙着打联机游戏呢,很不情愿地说:“叔叔去丢就行了嘛。”
“你是家里的长孙,再说今年要高考,讨个吉利。”平常一贯不信这些的阿爸这会儿说。
老三抚弄一下阿牡丹的头发说:“走吧,我想一个人丢还没资格呢。”
七
阿妈家的房子是这一带常见的藏东风格小楼。阿妈家人口多,前些年盖安居房时,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就只留了一个小院落。
盖房子时老三还在上高中,老大老二都反对盖这么大,说将来只怕老三也不会回来住,但阿爸阿妈坚决要盖大房子,说这辈子就这一回了,赶上安居工程的好政策,你们不出钱,也要给你们留出房间,哪怕一年住几天。所以就盖成了这样一楼一底的楼房,楼下正门是客厅,西边是厨房和食品仓房,东边是卫生间和堆放杂物的储藏室,楼上东面是两个老人的卧房,往西缩进去一溜,是四间不大的卧室,一个卫生间在楼梯旁边,三层是一个晒台,北面起了一个咤口楼,夏天可以乘凉晒东西。
这样一栋楼,可以说耗尽了阿爸阿妈的心血,也是他们为之骄傲的家业。他们给每个子女分配了卧室,每间卧室配备了双人沙发床,准备了被褥,只有西头那一间大一点儿的屋子,放了一套藏柜一套藏床,阿妈在里面安了佛龛,阿爸的很多书刊报纸,也都摆放在书架上。
八
听着楼上没动静了,德吉脱掉鞋,把两腿平放在藏床上,靠着床沿轻轻叹了口气。
“累了吧?”老三小声问,“要不你们早点睡?”
云珍放低声音说:“我们不累,我们不想睡。”
德吉挺有感触地说:“你们家真好,你爸妈真好!”
老三不置可否,向德吉做了一个拉易拉罐的动作说:“想不想再喝点儿?”
德吉点点头。老三从食品仓房抱出几罐啤酒,小心翼翼放好,拉开一罐,“刺——”,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很刺耳。阿妈听见了楼下的动静,走到楼梯口说:“在火盆上烤点儿干肉,或者拿点儿零食出来,空肚子喝酒不好。”
“您就别管了。”老三说,德吉和云珍对视着吐了吐舌头,又听见阿妈说:“德吉,我把你们的电热毯开到高档上了,等会儿别忘了调小,楼上卫生间牙刷和毛巾是现成的。”
“好的嫫啦,我们跟着就睡。”德吉向着楼梯点头说。
老三去把火盆拨开,拨出火种,挑几根新炭架在上面,一会儿,火势就起来了。小云珍新奇地看着这炭火,老三把火钳给她,看她小心翼翼在火盆里夹木炭。藏狗孔老五听见客厅有响动,扒开大门钻进来。
德吉看着老三烤干牛肉,说:“你们家好奇怪,狗叫老五,那老四是哪个?”
老三被这个问题问住了,想了一会儿才说:“没有老四。这个老五跟我们几个没关系,它是孔老五!”
藏狗听老三叫它,顺势跑过来趴在火盆边上,要是不来客人,它可没这个待遇。
“这样啊。”德吉说着也去挠挠孔老五的大脑袋,说,“也是你家的一分子了。我看你哥哥嫂嫂好像不满意你。”
“我哥和我从小就不对付,他觉得他学习好,本事大,当了个什么副处长,哪个都看不起。”老三说。
德吉把手指竖在嘴上说:“小声点儿。我看你跟阿牡丹挺好。”
“那当然,小时候净是我带他玩儿了。”老三骄傲地说。
两个人说话间,云珍在藏床的一角睡着了。看着云珍熟睡的样子,德吉心里百感交集。本来,这次她并没有打算跟老三来,她还没有想好他们之间的关系。直到跟老三进到这小楼之前,她还没有想好要不要把她们母女的终身托付给他。她觉得老三处事有些优柔寡断。但自从进了这栋小楼,她立即被一种温暖厚重的气息包围起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云珍的生身父亲,也是一个康区男人,那时候跟着他舅舅在拉萨做生意,租住在德吉家里。德吉跟他结婚时,刚刚从卫校毕业。那个人开朗帅气,表面豪爽大方,可是好赌好酒,没有自制力,输了做生意的本钱,他们结婚时置办的一点儿家当也输得精光,最后打起了她父母财产的主意。德吉毅然告诉那人的舅舅,把他告上法庭判决离婚。
在跟那人共同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从没给她提起过他的父母和家人,让德吉觉得很古怪,难道康区男人都是不顾家的?刚跟老三认识,觉得老三干事认真踏实,没什么坏习惯,知道老三也是康区人以后,她很犹豫要不要继续跟他来往,但云珍很喜欢老三,老三也经常跟她们讲起老家和父母,所以,德吉才下决心跟他来一趟,主要就是要看看这个家庭。
老三拿一床毛毯轻轻给云珍盖上,然后在火盆架子上烤牛舌和风干肉,看着薄薄的牛舌片冒出的油脂,沁润到干牛肉上,散发出奇特的香味,德吉食欲来了,她拿过一罐啤酒,用毛巾包裹着打开,坐到火盆边问老三:“你们这里大年三十上坟,是哪里的风俗?”
这又把老三问住了,他想了半天说:“不知道,反正别的地方好像没有。”
“其实挺好的啊,在过年之前先祭祖,不忘祖先。”德吉说。
“就是,西藏好多地方没祖坟,我也觉得怪怪的。”老三说。
“风俗不一样吧。”德吉说。
其实,西藏最早是流行土葬的,吐蕃时期留下的藏王墓就是证明。大概是由于西藏地处高海拔,木材稀缺,挖掘墓穴也不容易,土葬的成本实在太高,于是就有了天葬、水葬这样的替代形式。佛教传到西藏,赋予了这些丧葬形式一定的特殊意义,使它们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些东西,德吉是不明白的。
“明天我们要一起去吗?”德吉问。
“我去就行,你们不用去。”老三说。说到明天早上上坟,老三有点儿兴奋,“你不知道,有的家庭四五点钟就上山了,明早你看吧,天还没亮,漫山遍野都是手电光。”
德吉看看手机,过了子夜了,老三帮助抱着云珍上楼,安置娘儿俩睡下,也下来收拾睡了。
九
早上五点刚过,阿妈就起床下楼,看见火盆呀桌子呀收拾得干干净净,老三蜷在藏床上睡得正香,孔老五也伸长了身子,舒舒服服趴在火盆边。阿妈在厨房烧上水,放上砖茶,在电动酥油茶壶里放上酥油、盐、碎核桃仁,还没有等茶烧好,看见德吉从楼上下来,手里还捧着两样东西。
阿妈轻声说:“还不多睡会儿,昨晚睡那么晚。”
德吉惺忪着眼睛说:“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这里给您有一个帮典(围裙),是山南杰德秀的。还有几斤酥油,礼太轻了,昨天不好意思拿出来。”
“德吉太客气了。”阿妈接过礼物说,“帮典正好新年系上!坐长途车还带酥油,难为你了。酥油真新鲜,今早上就用它打茶。”
德吉拉开客厅门到院子里四处看,果然看见一面山上手电光闪动,隐隐有人声传来,感慨道:“真有早的呢。”
阿妈出来与德吉并肩站着说:“有些家户人少,要赶着回来预备年饭,有的是扫完墓去泡温泉,所以起得早。”
“这里每家都有祖坟吗?”德吉问。
“只要过上两三代的,都有,过去是土葬,现在是骨灰了。还不知到了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阿妈感慨道。
“嫫啦您说什么呢,您和啵啦(爷爷)的身体都好着哪!”
这时候厨房里烧茶的壶哨响起来,两人反身回屋打茶。阿妈把刚才放好的酥油挑出来,换上德吉带来的新鲜酥油。打茶的声音成了起床号角,这会儿,一大家子纷纷起来,在楼上楼下洗漱。
廖志远在院子里先洗漱好,钻进储藏室准备上坟用的香蜡纸钱,阿妈在厨房装好了苹果、桔子、桃干、杏子干、花茹,都放在一个背篼里。
几个女眷帮着阿妈把花茹、饼子还有几个冷盘摆上桌子,阿爸见阿牡丹还没起床,自己上楼去叫,老二给老大媳妇使眼色,意思是“看把你儿宠的”,老大媳妇也用眼神儿回敬,很得意的样子。
除了还在楼上睡觉的小云珍,一家人又聚集在了餐桌上。因为起得太早,都没什么食欲,端着碗响声很大地喝酥油茶。阿爸没话找话说:“今天的茶很香啊。”
小廖应和道:“就是,加了核桃米就是香。”
阿妈说:“用的是德吉带来的新鲜酥油。”
老二说:“我们拿来的那一包在哪呢?不用的话我带回去呀。”
小廖说:“德吉她们那里的酥油,跟我们这边的味道好像是有点儿不一样。”
老大抓起几个花茹泡在酥油茶里,说:“其实都差不多,远香近臭。”
见老三要说什么,德吉急忙说:“上山扫墓,我跟云云可以去吗?”
老大媳妇说:“你去做什么?要不是阿牡丹今年高考,我都不去。”
德吉有点儿尴尬地埋头喝茶,这时候阿牡丹说:“上山扫墓又不是去贿赂祖先,如果这样想,我就不去了。”
老大厉声道:“你是长房长孙,你怎么可以不去?”
老二讥讽道:“就是啊,我们家坟头冒青烟还靠你呢。”
阿妈见不是个事儿,说:“一大清早吵吵吵,你们都快去,我和德吉在家里给你们准备冒面。”
阿牡丹欢呼道:“太好了,好久没吃奶奶的冒面了!”
十
上山扫墓的队伍出发以后,屋子里安静下来,德吉不安地说:“都怪我不好。”
阿爸说:“别往心里去,跟你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他们是属刺猬的,近不得,离不得。”
阿妈被老头子的话逗笑了,说:“还满嘴新词呢。这会儿还早,你们去睡个回笼觉,我去清洗佛龛。”
德吉说:“反正也睡不着了,我帮您吧。”
阿爸说:“你别,这件事她谁都不放心。”
阿妈说:“德吉从拉萨过来的,我就要她帮忙呢。”
阿爸说:“那你们忙,天也快亮了,我正好散步去。”
德吉跟着阿妈来到二楼西屋,边收拾屋子边聊天,德吉知道了阿妈是江对面的人,由亲戚介绍嫁到这里,因为两个地方只隔一条金沙江,风俗习惯都差不多,很快就适应了。这些年大家都忙,亲戚走动少了,阿妈把心都放在了这个家里。
“嫫啦,冒面就是臊子面吗?”德吉在拉萨吃过四川臊子面、岐山臊子面,但她不知道拉萨还有盐井加加面,跟冒面类似。
“冒面你都不知道?”阿妈有点儿吃惊,在她看来,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冒面吧,“好多内地人专门过来吃冒面呢。”
德吉为自己的无知感到不好意思,阿妈说:“今天我专门手工给你和云云擀一刀面。”
待阿爸散步回来,阿妈便指挥他从咤口楼上搬下几抱烧柴,现在做饭烧茶都用液化气罐,用土灶的时候很少,为了做出地道的冒面,阿妈让老头子专门点燃柴火灶,摆出隆重的阵仗。
阿爸用一小截蜡烛生火。德吉知道点柴火灶要有技巧,有的人一张报纸就可以点着,有的人要不弄得满屋子浓烟,要不把自己弄个大花脸,像阿爸这样,用一截蜡烛慢条斯理点着柴火灶的,德吉第一次看见。只见阿爸不慌不忙,拿着一个水桶从院子里提水,德吉连忙去抢,阿爸说:“这点儿小事不用你插手,你去看看冒面是怎么做的。”
这会儿,阿妈在客厅藏桌上架起那个大面板,开始准备擀面的工序,德吉在边上看着,一点儿插不上手。
阿爸那边已经在大铁锅里倒了大半锅水,一边招呼德吉坐在灶口边上,一边给她介绍:这个地方地处茶马古道干道,历史上就是四川和西藏的交通咽喉,许多四川陕西地方的客商路过,有的见这里气候宜人,便停下脚步,在当地安家,娶妻生子做生意。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很会做面食。也因为这里日照充足,气候温润,出产的小麦磨出来的面粉筋道柔滑,所以面食很有名,冒面就是代表。
听阿爸这么介绍,德吉的好奇心更强了。只见阿妈已经盛好了两盆面粉,加入鸡蛋,又从灶膛里筛出灶灰,用水拌了沉淀好,然后滗到面粉里。阿爸和德吉力道大,和几大坨面,用湿毛巾搭上醒在那里。这时,阿妈已经把预备好的牦牛肉、香猪腿剁成肉丁,在煤气灶上放上炒锅,倒少许菜籽油,先把剁好的香猪腿推进去炒出油,再放进牦牛肉碎,炒断生,撒进去姜葱末再炒,一会儿,一股浓浓的香味就从锅里飘出来。
阿爸抽抽鼻子说:“可以了。”从大铁锅里舀了几大勺开水加进去,阿妈再往肉汤里加了些昨天的骨头汤、盐和胡椒粉,把煤气关小慢慢熬起来,德吉看阿爸阿妈在灶台边配合默契,简直是享受。
“这个就是冒面的关键,汤好不好,决定你们家在村子里的地位。”阿爸夸张地说。
接着就擀面。阿妈从面盆里醒着的面里切出一块,揉过之后拿出一根一米多长的擀面杖擀起来,一边擀一边撒上干豆粉防粘连。先上下左右平擀,然后裹在擀面杖上擀,再摊开把面皮换方向擀,一直擀到阿妈气喘吁吁,一直擀到几乎都透明了,才算大功告成。但是,且慢,还有一道最见功夫的工序,只见阿妈把擀好的面皮来回折叠成两寸宽,然后用刀细细地切起来,每一刀下去,出来的是一缕一米来长的金丝,德吉看得倒吸一口气。
阿妈凝神屏气一口气切完,伸直腰杆说:“这就是一刀。”
“阿啧,这些面全弄完得什么时候了!”德吉说,就这一刀,快一个小时了。
阿爸摇摇头:“现在没这个精力了,有现代化工具。”说着从储藏室拿出一个小型擀面机,固定在面板上,调好宽窄厚薄,切下一块块和好的面,手柄一摇,一缕缕的长面条就出来了。
阿妈一边在面板上分长面,一边说:“这一刀手工面是专门给你们做的,快去把云云喊起来,先尝尝。吃完了帮我扫阳春。”
见德吉听不明白,阿爸解释说:“就是帮她打扫卫生,今天大年三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扫除,我们这里叫扫阳春,应该是扫扬尘的意思。”
德吉赶紧上楼去把云珍叫起来,洗漱完,阿妈已经在灶台上排出一溜漂亮的瓷碗,比喝茶的龙碗大不了多少,见母女俩过来,阿妈抓了几缕金丝长面放进大铁锅,几分钟,见长面断生了,捞起来放入旁边的凉开水里,“这样可以漂去碱味。”阿爸说。
阿妈在另一个汉阳锅里舀了些臊子汤,往里面加入切好的番茄,然后把冷水里的面用筷子挑起一撮,手指轻轻一抖,面就理顺控干了,阿妈左右层叠把控干的面放进小碗里,将滚开的热汤舀进去又倒出来,反复好几次。
这就是“冒面”的由来吧,德吉心想。
冒好的面碗放在德吉母女俩面前,精致的碗里只有两三筷子的面条,撒上切碎的香葱,舀上汤,中间一勺肉丁臊子。
“快吃吧!”阿妈阿爸笑盈盈地看着她们。
云珍端起碗,三两下一碗就下肚了,伸出碗来:“嫫啦,我还要。”
阿妈已经有一个添面的“浇碗”在手里,里面是冒好的面,阿妈把面稳稳地落到云珍碗里,一勺臊子正好在碗的正中。“嫫啦这里有的是,多多吃!”阿妈一边对云珍说一边催促德吉:“凉了不好吃。”
德吉双手捧着瓷碗,热热的,像带着两个老人的体温。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十一
看见这样的吃法,德吉有点儿难为情了,照她的饭量,这得吃多少碗哪。“嫫啦,您给我盛一大碗就行,这样太麻烦。”
阿爸坐在灶台前说:“那样吃就不叫冒面了。冒面不能加酱油,可以来点儿熟油辣椒、香醋,要不要?”
“要!”德吉说,双手伸出去,她好像要把这种幸福感牢牢抓住。
吃了第七碗,连云珍也吃了四碗,德吉不好意思再添了。大过年的,要吃的东西还多,阿爸阿妈也不勉强,自己冒了面来吃,这时,一起出去的上坟队伍,稀稀拉拉回来了。
最先到的是阿牡丹,刚进院子门就叫:“奶奶,快冒面!”直奔厨房里来。
“先去洗洗,有你吃的。”奶奶说。
德吉催着要去扫阳春,阿爸说扫阳春大扫除,要一家人都吃完面才开始,德吉不解,阿爸解释说:“冒面要好吃有三个诀窍,一是灶灰拌,二是柴火烧,再就是扬尘飘,如果没有点儿扬尘飘进铁锅里,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要等大家吃过第一锅,然后把擀好的面都煮好凉起来,才能扫阳春。”
“不要听他瞎说,照那样,没有柴火灶的家里,还吃不成冒面了?”阿妈说。
老二老三一起回来,老三背着背篼,阿妈知道小廖回白玉乡值班去了。老二老三好像路上怄了气,老二回来,谁也不理,径直去楼上的房间收拾东西。德吉用眼神儿询问,老三转移话题说:“冒面好吃吗?”
“冒面太好吃了,我还想吃,阿妈啦不让。”云珍说。老三看向德吉,德吉说:“她吃了四碗,我怕她吃撑了。”
老三对云珍说:“这几天早上天天都要吃冒面,你要吃伤的。”
“天天吃,我喜欢。”云珍说。
德吉说:“冒面真不一般,还有那么多讲究。”
老三不以为然地说:“又是我阿爸跟你神吹吧?”
他们在客厅说话的时候,阿牡丹洗完手,到厨房里跟爷爷奶奶说:“其实我的补习班过了十五才开始,他们要到我妈家去,又不好明说。”阿牡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两个老人跟前,称呼自己父母都用“他们”。
“什么时候去呢?”正在灶台前收拾东西的爷爷问,阿牡丹愣住了,他不知道父母没跟爷爷奶奶交底,支支吾吾说:“好像说是明天走。”
“哐!”阿妈把手里的汤勺和漏勺砸到灶台上,说:“那还回来做什么?哪有大年初一都出门的道理!”
“算了算了,人家眼里只有媳妇,哪次听过你的?”阿爸说,“快给阿牡丹冒面吧。”
阿牡丹跑去搂着奶奶:“奶奶别生气了,我留下来陪你们!”
阿妈叹口气,说:“你那个妈我还不知道,你好好考试才是阿弥陀佛。”
十二
老大两口子回家进门,感觉气氛不大对头,老大媳妇高声说:“阿妈,你们做面辛苦了,我来给大家冒面。”
阿妈冷冷地说:“大家都吃完了,你们自己弄来吃吧。”
老大说:“你们真是,也不等着一起吃。”
阿爸哼一声,招呼道:“吃完的动起来,赶紧把扬尘扫完,老三和阿牡丹把春联贴了,老二,你不是明天要走吗,还不帮你阿妈把切玛盒装上。”
老二正埋头吃面,不吭气。老大两口子有点儿不自在了,老大媳妇明知故问道:“老二明天要去白玉乡?”
老二抬起头来要发作,阿妈说:“你们快去冒面吃,吃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春联是驻村工作队送的,两副,一副是“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横批“辞旧迎新”;一副是“欢声笑语贺新春,聚集一堂庆丰年”,横批“合家快乐”。老三和阿牡丹商量半天拿不定主意,老大出来指挥:“合家快乐”贴客厅大门,“辞旧迎新”贴院子大门,“你看嘛,先在大门口辞旧迎新,然后进来合家快乐。”老大这样解释道。
阿爸收拾了一包花茹,把煮好的香肠血肠腊肉什么的各装一点儿,另一个无纺布包里的小汉阳锅装了一锅臊子汤,锅盖上放着煮好的长面,准备出门。阿妈叫住老头子悄悄告诉他,让他顺道去小卖部给德吉和云珍买新年礼物,每次过年他们都要给儿孙们准备礼品,这次德吉母女突然来,有点儿措手不及。
“小卖部有啥好东西?”阿爸为难地说。
“家里也没有现成的,这咋办呢?”阿妈也着急了。
“不行你到拥西家看看,他们家女儿在县城做服装生意,可能有合适的。”阿爸出主意道,阿妈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决定抽空去一趟。
看着阿爸提着两大包东西出门,老二说:“阿爸真把村委会当家了,也不知道那些驻村工作队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可不好这么说,人家工作队的孩子们为了啥,过年都回不了家,这几年没少给村里办事,亏你还在乡里工作。再说,工作队也没少给你阿爸拿东西。”阿妈说。
下村的习俗,除夕的晚餐最丰盛,第二天初一的饮食也要准备出来,阿爸去了村委会,一家人就各自忙碌起来。
老三和阿牡丹从楼上开始,逐个房间掸尘土、拖地,德吉跟在后面擦窗户桌子。阿妈从藏柜里取出切玛盒,开始隆重地工作。切玛盒藏语叫“竹素切玛”,是一个长方形雕花彩色木斗,中间隔开,一边装酥油拌好的糌粑,一边装五谷,再插上麦穗、干花和彩色“孜卓”。“孜卓”是令牌一样的东西,用酥油花装饰,下村的气候暖和,用酥油做容易融化,“孜卓”是画上去的。做完这些,阿妈把切玛盒摆在客厅藏柜上。因为各怀心事,干活儿的时候,大家谁都不说话,屋里静悄悄的。
看准备差不多了,阿妈去隔壁拥西家,也没跟谁打招呼。老大两口子和老二看没什么事,都回屋去补瞌睡,楼房里,就只剩下老三、德吉和阿牡丹在扫尾。最后,阿牡丹接上水管,开始冲洗院子。
他因为心里不高兴,拿着水管到处乱滋,阿妈从拥西家回来,在门口默默看了一会儿,走进来问:“你叔叔他们呢?”
刚才老三带着德吉母女出了门,临走还打了招呼,阿牡丹没在意,他说:“好像说出门转转。”
“两母女昨天坐了一天车,今天又起个大早,也不让人家休息一下。你去眯一会儿。”阿妈对阿牡丹说。
“我不困,在学校天天起大早。”阿牡丹说。
这个身边长大的孙子开始懂事了。阿妈没进屋,坐在客厅门槛上,看阿牡丹忙活,心里有点儿感慨。
虽然是冬天,但太阳很好,阿牡丹冲洗院子的水一会儿就干了。三十下午,本来应该热闹的院子现在却格外安静,孔老五跟在阿牡丹的身后转悠,也安静得一声不吭。
坐在门槛上,阿妈差点儿睡着了,阿爸回来,看见老太婆这样,说:“哎哎,大过年的,不去做饭,在这儿闲坐,小心感冒。”
楼上睡觉的这会儿都下楼来。老三领着德吉母女回来,说是带她们去看村里的泉眼。下村的泉水好,冬暖夏凉,从不结冰,周边许多村子讲究的老人,都到这里打水烧茶。下村出美女,据说是因为这股泉水。前两年,驻村工作队专门花钱把泉眼修葺一新,还把水送到州里省里做了化验,说要开发矿泉水,不过还没有下文。
大扫除,收拾屋子,准备年饭,年三十的时间过得很快。
下村的除夕比古突之夜要隆重得多。一大早摆上藏桌的花茹呀、水果呀、干果呀,各种冷盘,谁要饿了就去抓几个填填肚子,五六点钟,大部分家庭就开始吃团年饭了。这会儿,村子里这里一家,那里一家,陆陆续续响起了鞭炮,那是每家开始团年的告示。
阿妈家的团年饭,照例是阿妈主厨,老大媳妇和老二打下手,今年多了一个德吉,厨房里显得很热闹。几个男的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却没人认真看。阿爸戴着老花镜在翻一本杂志;老大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发信息;老三不知道跟哪些人在发语音,没完没了;只有阿牡丹,既不看电视,也不玩手机,在藏床上呆呆地坐着,云珍躺在他身边,睡得很香。
一会儿,菜做好了,呼呼啦啦上来,六个热菜六个凉菜,月月好,摆得满满一桌。酒有老大带来的绵竹大曲,有村子里自烤的青稞酒,也有新鲜的叫“酉仓”的酿酒,还有啤酒,爷爷还专门从小卖部买了一罐豆奶。下村许多家庭都酿酒,按阿妈家的条件,也应该自己酿酒烤酒才对,但阿妈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酿酒这件事也是怪得很,同样的原料温度,每家酿出来的,口味都不一样。
全家人坐齐了,老大叫阿牡丹去放鞭炮,阿牡丹才清醒了一样回过神儿来,老大说:“这小子,也不知怎么了,一整天愣怔怔的。”
阿妈听说了,在围裙上擦擦手,等阿牡丹回来,就把一撮熏香撒在火盆里,让阿牡丹伸头熏一熏,说:“上了坟回来,大家都来熏熏。”
其实,阿牡丹是因为自己跟爷爷奶奶感情深,父母要提前回去,心里不痛快,加上上午扫墓,想到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又想到了生死这样没法悟透的问题,所以有些郁郁的。
上了山的依次都熏了熏,小云云也去学着,惹得大家都笑起来,气氛活跃一些。老大说:“我们还是先敬爸妈酒呀。”大家站起来,有白酒,有酿酒,有啤酒,有饮料,五花八门,依次碰杯,互道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一时间,好像所有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了。
吃饭间,老大不断起身离席,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打电话,有个电话打了将近半小时。老大媳妇殷勤地一边给大家敬酒,一边解释,老大现在提了单位的副处,相当于县里的副县长了。给老二敬酒的时候就说:“你们家小廖加油哦,级别越落越远了。”
老二说:“我们家那位,只知道攒笨干活儿。”
阿爸说:“小廖不错,实在。”又说,“老大也不容易,成大干部了,驻村工作队最大的领导也是副处长。”
一会儿,老大媳妇、老二也不断起身去接电话,阿妈看着摇头说:“人被电话牵着走,吃饭都不安生。”等老大和老大媳妇都坐定,阿妈挑明了问,“老大你们也明天走?”
老大媳妇说:“是这样阿妈,阿牡丹的成绩我们很担心,给他找了老师补习,只有春节期间有时间。”
“阿牡丹平时学习不是挺好吗?”阿爸问。
老大说:“你们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只有拼命考个好大学才有前途,不然……”他看看老三,把话咽回去了。
老三若无其事地喝啤酒,他的跟前已经堆了一堆啤酒罐子。
阿牡丹说:“人生也不只读书一条路。”
老大蹾下酒杯说:“人生不只读书一条路,你现在的人生就只有读书一条路!”
老大媳妇忙打圆场:“好了好了,你们两爷子。”
阿牡丹说:“还不是你,非要去丹巴!”丹巴是老大媳妇的老家,这句话把老大媳妇弄得很尴尬。老大暴怒道:“你胡说什么,我们还不是为你好!”
“去看看亲家也是应该的,老大你应该提前说。”阿妈平静地说,老大反倒不知说什么了,都沉默下来。
“老二明天怎么走啊,我们可以送你。”老大媳妇转移话题。
“不用,我们几个伴儿一起走,明天一早去格萨尔机场飞成都转机。”老二冷冷地说。
“这么麻烦。”阿妈感叹道,又说,“大年初一出门,你们都小心点儿。”
这顿饭吃得冷冷清清,还不到八点,老大推说头昏,上楼了,大家帮忙收拾完桌子,老大媳妇和老二也上楼去。桌上的许多菜,都还没动一动。
十三
在下村,除夕团年饭没这么早就吃完的。“年饭年饭,要吃一年。”阿妈把没动过的菜都加热,重新拼了几个凉盘,把火盆也拨旺,招呼老三、阿牡丹、德吉母女再围拢来。阿爸一直稳坐在他的座位上,不时咂一口青稞烧酒,眼皮也没抬一下。
老三已经完全醉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说自己没出息,一会儿说要挣大钱孝敬老人。德吉有点儿惊慌失措,倒是阿爸阿妈很镇静,让德吉和阿牡丹把他放在藏床上,用热毛巾擦把脸,马上就睡着了。阿妈问德吉:“他在拉萨是不是常这样?”
德吉说:“过去不清楚,反正我认识他之后,这是第一次。”
阿爸说:“大男人,几瓶啤酒就醉成这样。”
阿妈说:“他心里有事,不痛快。”
“不痛快也不是这样的。”阿爸说。
桌上没人陪阿爸阿妈喝酒,德吉倒上啤酒敬老人,阿妈问:“还能喝点儿?”
德吉不好意思地点头,阿妈说:“大冬天不喝啤酒了,我们喝‘琼擦’(热酒)。”
阿妈拿一个搪瓷缸煨在火盆上,把酥油化开,加上青稞烧酒、蜂蜜,用木碗盛出来。木碗保温,喝起来热乎乎的。德吉在老家初一早上喝过“规颠”,是用热青稞酒加甜奶渣、人参果、红糖拌好,再加糌粑搅成糊糊,味道有点儿像,但琼擦的劲头更大。
阿妈说:“明早我们喝的琼擦,也是加糌粑糊糊的。”
琼擦很好喝,云珍抢着喝了两口,也睡着了。德吉晕晕乎乎,整个人都像要飘起来。阿牡丹喝得脸红红的,但还清醒,他一直催着爷爷奶奶去睡觉,“都快11点了。”阿牡丹说。
奶奶一点儿事没有。看爷爷,也像一尊菩萨样坐着,除了不时咂口琼擦,动也不动。奶奶说:“守岁守岁,不守过午夜怎么行呢,再说等到了12点,我还要去抢头水。初一的头水礼佛,给大家烧茶,最吉祥!”
阿牡丹说:“奶奶,今年我去抢头水,您就不要去了。”
阿妈说:“哪年不是我去抢头水,你一个男孩子抢什么,不过今年你和德吉我们一起去最好。”
像菩萨一样坐着的阿爸这会儿说话了:“德吉还不知道抢头水是咋回事吧,现在不告诉你,等会儿你去看了就知道了。你们那里肯定没有。”
阿妈推老头子一把说:“会不会说话?”说完起身上楼去拿来一个包袱。她把包袱打开,是一件半新的女式藏装。
“德吉,我看你这次没带藏装来,本来应该给你做一件新的,时间来不及,这一件是我年轻时穿过的,你要不嫌,明天穿这件吧。”
“我不嫌我不嫌,走得太急没有带,正发愁明天穿什么。”德吉说。
“家里过年,每个人都有我们准备的新衬衫,也给你和云珍准备了,在卧室里。”阿妈说。
“阿妈,阿爸……”德吉眼睛红红的低下了头。
阿妈说:“我们也看见了,你跟我们家老三挺好,云云也很乖。我们家老三从小娇惯了,没养成好习惯,但人不坏,以后有什么事情多担待他。”
老三其实已经醒了,他静静地躺着,任眼泪流下来。
......
节日与温情——《团年》创作谈
1.缘起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禁足家中,先是为湖北的形势焦虑,后来慢慢平复,在不像春节的春节,遥想曾经在老家过的春节,遥想那种热闹与温暖,许多细节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出来,情不自禁打开电脑,写下来这篇文字。
几年前,年近九旬的父母相继谢世,正如有一首诗说的:爸妈在时/家乡是我的老家/爸妈没了/家乡就只能叫作故乡了/梦见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回去的次数会越来越少。回想在老家过年的某一年,大概是1977年以后吧,生活开始有一些好转,那一年过年,乡下杀猪宰羊,城镇里也热气腾腾地炸果子(花茹)、磨汤圆粉,欢天喜地。再往近一点儿,餐桌日益丰盛,年味逐渐淡去,但一家老小聚在一起,放一挂鞭炮,吃一桌团年饭,还是必须有的。过年,有如一个仪式,是每年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在2020年那个特殊的春节,写下《团年》,也包含着对逝去亲人的怀念。
2.三天
《团年》的背景是在我的老家,川滇藏交界之处,那里是过去茶马古道、麝香之路以及汉藏彝文化走廊的一个结节。那里各民族和谐共处,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别开生面,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小说写了古突之夜(二十九)、除夕和初一(如果算上初二,可以叫尾声)三天,在这三天里一家人的故事。一个发生在一栋楼里面的故事。故事不复杂,但糅杂了许多东西,老陕的面(冒面)、湖北的锅(汉阳)、西藏的突巴、西北的油香(花茹),还有四川的蒸肉、上坟的习俗,等等,天南地北的大杂烩都烩在了这个时空里。我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看似奇特的习俗,实际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故事,演绎下来,多少有一些扑朔迷离,但这也正是它独特的魅力。
3.这一家子
这一家人实际上是五男五女——老家的父母,在外工作的长子夫妇和孙子,在身边的女儿女婿,在外打工的小儿子以及他的女朋友和女儿。父母挖空心思把儿女们召集回来,想热热闹闹过个年,但这栋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建造的小楼,并没有把儿女们留过初一。儿女们有各自纷纷散去的充分理由,生活的重负、精力的分配、情感的需要,等等。一代人与一代人,就这么渐行渐远。
4.冒面和团结包子
我用尽可能细致的笔触描写了冒面和团结包子及其做法,基本是写实主义。冒面和团结包子都极具地方特色,是那一个“唯一”,然而它们又是多种饮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有背后的故事。我不厌其烦地写制作过程(包括炸花茹),不是为了教授烹调,虽然这里面有我为这样的特色饮食骄傲的意思。冒面有过往岁月的味道,有父母的温度,有对远方客人的一片热情,而这个春节的团结包子里,却多少包含了父母辈的无奈和辛酸。
5.抢头水
抢头水是斜逸出来的一支,好像跟主线不搭界,里面有传说故事,有传统习俗,还有现代人的理想和愿望。主要是想把历史、传说与现实贯通起来。驻村工作队的作为和村干部的想法,承接过去、守住现在和面向未来,不知道达到目的没有。
6.温情
匆匆地团聚与分离,每个人都有必须如此的理由,里面也包含着生活中的许多无奈和艰辛。生活依然继续,漫天大雪也拦不住外出的脚步。当然,漫天大雪也拦不住更多的温情。有来自远方的德吉母女感受到了也许阿爸阿妈的儿女们感受不到或者习以为常的温情,有一件衬衣、一条护腰、一点儿酥油的温情,有大雪天前来拜寿的女婿和驻村工作队、村支书带来的温情,更多的,是一家人之间虽然磕磕碰碰但割舍不开的温情。在小说里,阿爸阿妈没有名字,三个儿女也没有名字,他们经历着的,是现在的许多父母和儿女经历的事情。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2期(责任编辑:安殿荣)

吉米平阶,藏族,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在《民族文学》杂志社工作。2004年援藏,2010年调藏工作,现任西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西藏作协主席、《西藏文学》编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近年来创作有剧本、电视专题片、系列散文、小说、纪实文学等作品,出版长篇纪实散文《高原明珠日喀则》、文化散文集《寻找朗萨雯波》、长篇纪实文学《叶巴纪事》《幸福的旋律》,叙事长诗《娜木纳尼的传说》,电影文学剧本《风雪擦亮的青春》《西藏岁月》《海拔5000米》《拉萨 拉萨》等,拍摄电视专题片《金秋时节》《鹰翔》、19集系列电视专题片《西藏文化漫谈》、六集纪录片《天河》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