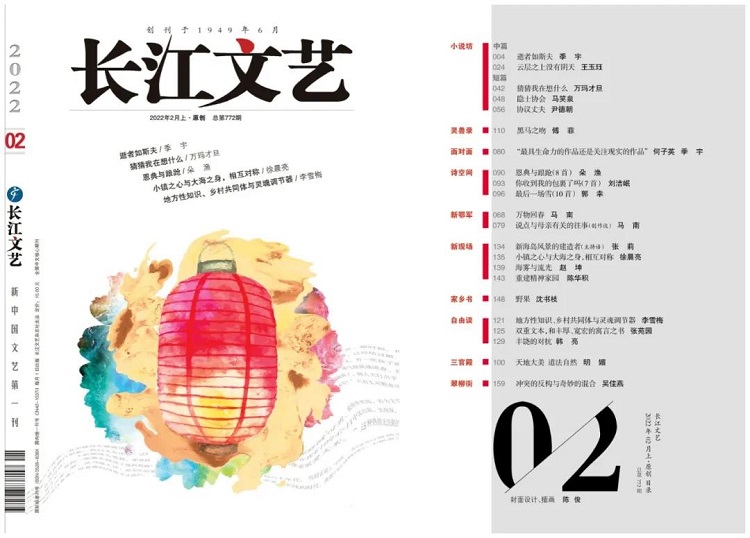
我记住了一场火的样子,那时我十一岁。
火燃烧在一个下着毛毛雪的早上。毛毛雪轻飘飘地散在凹村的天上,可以落下来可以不落下来的样子,让人不对它们产生任何期待。偶有几朵轻飘的雪花一落在凹村的大地上就化了,仿佛凹村那天的地是一个滚烫的大火炉,烤化了雪的身体。有些天上正在往下飘的雪看见地上的雪,半空中就把自己化掉了,它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交给一个滚烫的大火炉去结束自己。雪花在天空中慢慢变得少起来。我不知道一朵雪花是怎样在半空中做到想化掉就化掉的,我想雪冰凉的身体里本来就藏着一种我们从未察觉的热烈,只是雪平时善于隐藏,不想把心中的那份热烈随随便便拿出来让其他事物看见。
雪落在一个深秋,一个不属于雪该落的季节。正因为此,在以后的很多年,我都觉得那个早晨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早晨,虽然当时我身处在那个早晨之中,但那个早晨似乎依然离我很远很远。雪改变了我对一个早晨的看法。这场雪是凹村十多年以来下进村子的第一场雪。
十多年之前,凹村下过一场厚雪,那场雪是半夜开始往村子落的,雪下得悄无声息,下得仿佛只为下而下。那场厚雪把凹村盖得严严实实,夜的凹村只剩下暗里的白。人在暗的白中,做着一场场和雪有关的梦。梦中,他们被雪吸引,被雪追逐,那场梦中的雪的颜色是红色的,下得整个凹村的天空通红通红的。凹村人从来没有见过一场红色的雪,他们在雪中打滚,在雪中喊出一声声生活在凹村里的名字。谁的名字被别人喊出,谁的名字就被那场梦里的雪染成红红的颜色传到他的耳朵里。那场雪中,凹村所有的牲口都在说一句句人话,他们说的人话被红雪染色之后,又变成另外一种凹村人听不懂的外地话飘在雪中,时而高,时而低,时而没了踪影,时而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从某块儿浓密的飞雪中冒出来,变成凹村人的一句话。梦里,树是红色的,天是红色的,大地是红色的,人看进心里的一切东西都是红色的,红染着每个人的梦境。后来人的梦里迎来了天亮,梦里的天亮是慢慢从每个人脚下的土地里亮起来的,人看见一轮蓝蓝的太阳从凹村的土地上长出来,先挂在一棵草上,再挂到一株麦苗上,再挂到一朵俄色花上,再挂到一棵松柏上……太阳越升越高,最后挂到人头顶的天上。梦里的太阳是凹村的很多事物慢慢把它送到天上去的。太阳发出蓝色的光,照得整片大地蓝起来。红雪慢慢在蓝色阳光中停下来,人看进心里的红悄悄在人心里消失。人在阳光普照的蓝中醒过来,这时人才发现屋外的雪还在“嗖嗖”地下,雪拍打着自己家的青瓦、大门、窗户清脆地响。每家每户的门被雪封住了,窗户被雪封住了,楼顶被雪封住了,牛圈被雪封住了,只有一座座房子的烟囱高高插在半空中,像留给一座房子喘气的喉咙。人在屋里急,人用手去推门,去拉窗户,一座房子的门和窗户死死地陷在厚雪里,无论人用多大的力气,门和窗户都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人朝牛圈方向喊自己家一头牛、几只羊的名字,人的声音刚传出去不远,就被一扇封死的门、一堵厚厚的泥巴墙硬硬地返回来,又落到了自己的身上。人哭丧着一张脸在屋里慌,人想这个夜晚的雪是一场收命的雪,人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感觉到自己的命越来越薄。然而,那场雪在人人都沮丧得要命时,并没有改变凹村的什么便离开了,那场厚雪似乎只是想让人知道人的一生中落过一场把自己淹没过几天几夜的大雪。雪可能还想让人知道人的一生就是一场缓缓淹没自己的旅程。
从那次之后,雪久久没来过村子一次,自从那次大雪之后,雪仿佛也把自己一次性下了个够。
十多年之后,又一场雪飘进凹村。雪是轻着身子来到凹村的,落得不合时宜,落得我站在雪中却感觉自己离一切很远很远。
在这场雪中,我跟着凹村长长的队伍往前走。人的队伍行走缓慢,远远看去这支长长的队伍也像是一条去西坡的土路了。敲家什的师傅走在最前面,把手中的家什敲得脆响,后面的人安安静静地埋着头往前走。
雪还在飘,没有声响地飘。这场雪是从热了二十多天的天上突然落下的一场雪。二十多天里,凹村大沟里的水被太阳烤干了,树被太阳烤蔫了,人说出的话干涩涩的仿佛也被太阳烤过,地在人的脚下“啪啪”地裂。这二十多天,一切该生长的植物都停止了生长,该长大的也在二十多天里停止了长大,有的甚至越变越小。比如一些小娃,以前二十多天不见一个小娃,有一天在一条路上遇见他,你会发现一个二十多天没见的小娃,突然就在你面前长高了一截,那二十多天里的成长让你感到时间的魔力。但在遇见干旱的这二十多天,人无事可做,整天盯着一个平时没时间看的小娃看,人发现在你盯着他看的二十多天里,娃还是原来那个娃,身子小小的,走出的步子歪歪扭扭的,娃天天满嘴说着人听不懂的嫩话,一点长大的迹象都没有。比如一只蝉。那只蝉经常在你的木窗上叫,你随手把它捉过来,想喂给家里的鸡,你以前经常这样做,后来你看见那只蝉屁股翘得老高,翅膀扑棱扑棱着,你一下舍不得把它喂给一只鸡了。你翻箱倒柜地从床底找来一瓶你曾经漆过木床的红漆,在它身上点了一个红点作为记号,你放了它。你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或是自己的下一辈子里会不会再遇见这样一只蝉,只要遇见你就会一眼认出它。可自从你放了那只蝉,二十多天里它一声没叫地趴在你睡觉的窗户上,每夜盯着你睡觉,那鼓鼓的大眼睛把整个你印在里面,你不知道一只被你点过红点的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也盯着它看,二十多天里,你把一只趴在窗户上的蝉越看越小,越看越小,你想,一只越看越小的蝉,是不是在往小里生长。
我踏着前面的人走过的步子,往前走。我知道只要前面的人走过的路,一定是一条好路。至少前面的人没在我前面走的时候摔一个跟头,扭一回脚。有前面的人在我前面走,我眼睛不用看地。我一直在看天。天上除了轻飘飘的雪,什么也没有。我在想,这样的天,云哪里去了?雨哪里去了?雷电哪里去了?我在想这些的时候,心空空的,脑袋空空的。刚才想的事情一会儿就从我脑海中消失了。我愣愣地走在人中间,笨拙得像根僵硬的木头插在大地上。那时,我觉得我身上的手不是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它们只是长在我身上,而不属于我。更确切地说,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今天你是主人,你傻里傻气地落在后面,会被人笑话的。”没等我回过神来,松尕拉着我往人群前面走。人见是我,主动为我让出一条道。他们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也觉得自己很可怜似的。穿过一半人群,我不想走了。无论松尕怎么拉我,我都不想跟着松尕往前走了。我插在缓慢的人群里,又恢复成了一截木头。
“牛犟的,不走到最前面也可以,你总得哭两声吧?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松尕收回在我耳边说话的嘴,无奈地说。人从我和松尕的身边缓慢地走过,他们怜悯我的眼神在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慢慢减弱。
“我哭不出来。”我对松尕说。
“想着法子哭。你阿爸走,你家一个个哑巴一样没一点伤心样,人家怎么想,你阿爸在那边怎么想?”松尕说。
我阿爸会在那边怎么想呢?我边走边想。这样一想,我发现我和阿爸生活的这些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阿爸平时言语少,活在凹村的大部分日子都是沉默的。他每天早早出去,很晚才回来。阿爸早早出去的时候,我还没从梦里醒过来,他晚上回到家,我又睡在另一场梦里了。梦隔开了我和阿爸。一年里,我和阿爸相处最长的日子是每年的三月三。三月三龙抬头的日子。每年这天,阿爸都会把我从一场梦里叫醒,我还不习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么早把我从梦里唤醒。我不醒,阿爸一直在床边唤我的小名,只有这一天,他才像一个真正的阿爸一次次地唤我的名字。见我睁开眼睛,他第一句话就是:走,阿爸带你教牛去。我家原来有两头牛,后来从两头增加到四头,又从四头增加到八头,到现在我家已经三十多头牛了。三十多头牛每年都有新产的小牛,三十多头牛中每年都有长成壮牛的小牛。每年三月三,阿爸会挑选一头小牛出来,教那头小牛耕地。那些小牛都是倔强的小牛,没见过大场面,没受过牛轭套在脖子上的苦。牛轭一套在脖子上,小牛就开始跑。阿爸拽着小牛不放,用劲儿往回拉。平时的小牛怕主人,牛轭套在脖子上的小牛像变了一头牛一样六亲不认,拖着阿爸在一片地里乱窜。有时阿爸会在牛屁股后面摔上几跤,有时他会被一头小牛拖着,在地里拉出好长一截,有时牛也会被阿爸的猛劲儿折腾得摔几个跟头。阿爸不服输,阿爸教牛,就是一场人和牛的较量。那时,我觉得阿爸的身体里有牛一样使不完的倔劲。我坐在离阿爸不远的地方看他,第一次看阿爸教牛的时候我很紧张,看着阿爸摔倒,看着阿爸被牛拖在地上走时我吓得大哭。不过随着这样的次数增多,我知道阿爸每次都会从摔倒和被拖出去很远一截之后再爬起来,而刚才摔的那几跤,拖出去好远的那几截对于阿爸来说并不算什么,那时我觉得阿爸就像阿妈手里用不烂的锄头一样受不到伤害。阿爸是铁做的,我有一个铁一样的阿爸。后来,无论是阿爸在教牛中摔倒或被牛拖在地上跑,我都在阿爸为我事先找好的一个比较安全的石头上坐着笑,激动的时候我还会从那块石头上跳起来高兴地拍着手,大声冲阿爸欢呼。有一年,阿爸被一头叫嘎嘎的小牦牛拖出了地坎,牛和人一起掉下几米深的水沟里。我坐在大石头上看着看着就不见了阿爸,我在大石头上等阿爸回来,这种等是一种没有任何担心的等,这种等就像是阿爸在不远处和牛一起摔了一跤总会爬起来一样。那次,我等了好久都不见阿爸从水沟里出来。我跑过去看,阿爸躺在水沟边,鼻子里冒着血,他闭着眼跟睡着了一样。嘎嘎站在水沟边胆怯地有一眼没一眼地回头看阿爸。我喊了一声阿爸,他没答应,我又喊了一声阿爸,他还是没答应。嘎嘎走到阿爸身边,用嘴拱阿爸的身体,用暖暖的冒着热气的舌头舔阿爸的脸。我是被嘎嘎舔阿爸的脸吓着的,我急忙往家跑,阿妈正在为十几头藏猪撒刚割回来的青草。我喘着粗气告诉阿妈,嘎嘎在吃阿爸。阿妈停下手中的活,问嘎嘎在哪里吃阿爸?我说在水沟下面吃。阿妈听完,脸色煞白,她匆忙扔下手中的草,朝阿爸教牛的方向跑。那次阿爸被几个人抬回了凹村,他在床上躺了十多天。十多天之后阿爸又开始下地,忙他该忙的。那时我还是认为阿爸是一个用不烂的阿爸,铁一样的阿爸。
现在想想,阿爸说是带我去教牛,我一次也没有摸过阿爸教的牛。阿爸只是让我远远地坐着看他教牛,看多了,我觉得阿爸也像一头生活在凹村大半辈子的牛。阿爸每年教的牛,无论那头牛怎么难教,怎样的倔脾气,自从阿爸教过之后,牛都会自己耕地了。我一直没弄明白一头不知天高地厚的牛是怎样服气阿爸这样一个人的,阿爸没说,或许阿爸骨子里是和牛相通的。他教牛,就是让我看他教牛而不是让我真正去学那一门手艺,他想让我学的可能是教牛之外的一些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也没太想明白。
我还是哭不出来。我觉得阿爸没有死,不会死,阿爸在我心中像铁一样不会随便死掉。他只是在他累了一辈子的日子里,偶尔和我玩一次躲掉自己的游戏,就像那次他掉进水沟里,就像他无数次被一头牛在地上拖着跑,在某个时刻,他也会自己爬起来。我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不会死的阿爸。
“没出息,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松尕摇着头从我身边走开了,他混进了长长的送葬队伍,我看见他走在敲家什的师傅后面,低着头,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但始终没掉下一滴眼泪地沮丧着脸。阿姐和阿哥也夹杂在长长的队伍里,他们也没哭,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们哭不出来。他们从来没见过阿爸每年三月三教牛的样子,他们心中不会有一个像铁一样的阿爸。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和我不一样的阿爸让他们也哭不出来,那个不一样的阿爸只在我没有在的时候展现给他们看,就像那个铁一样的阿爸只在他们没有在的时候展现给我看。
阿妈没来送葬的队伍。阿爸出事后,她一言不发地坐在和阿爸生活过的屋子里,灯不开,窗户不开,她在久久地和一屋子的黑相处。黑似乎可以让她和阿爸很近。
我有些恍惚,我从长长的人群中走出来,站在路旁边的一个大石头上看这群往西坡走的人。这时的松尕走在前面,没有人再来说我是今天的主人应该走在前面的事。在这支沉默的队伍中,他们的悲伤似乎比我还多出好几倍,他们多出好几倍的悲伤足以让他们忽略我这个人在他们中间正做着什么。
这块石头让我想到阿爸每次教牛时我坐的石头,它安全,让我感觉不到怕。
除了在黑屋里陪阿妈的三四个人,全凹村的人都在这条送葬的队伍中。他们默默地走着,不发出一点声响。村长尼玛走在敲家什的师傅后面,他在一群送葬的队伍中也像一个村长的样子。他一路走一路向天上撒着纸钱,尼玛洒向天空的纸钱一会儿就和着雪落在地上,有的落在村人的头上、衣服上。人默默地捡起落在自己身上的纸钱,重新向天空洒一次,几张纸钱有了两次从人手中飞向天空的经历。它们再次落在地上,和其他纸钱有些不一样了,我看见它们在路边翻滚了几下,再翻滚了几下,像是在给其他纸钱炫耀着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无论怎么样的人生,此时的纸钱没有发现,它们都是从人手中落向一条路的,人在给纸钱计划一条路,一条朝西坡的路。哪怕它们在这条路上落在某个人的头上、衣服上,它们的人生在某种程度、某个时刻有了和其他纸钱不一样的命运,但是这条朝西坡走的路是一条不容改变它们命运的路。这条路是尼玛村长给它们指引好的路,也是凹村祖祖辈辈早就给它们定下的一条路。
尼玛村长停了下来,后面的队伍停了下来。尼玛村长踮着脚看后面的人,埋着头的人把自己的头抬起来看尼玛。他们知道尼玛像下地干活一样清点着一支送葬队伍的人数。尼玛村长自从当了村长之后,养成了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往后看的毛病,他似乎总是对自己身后的很多事情不放心。这几年,村人也习惯了尼玛村长的这种习惯,一旦尼玛村长突然停下来看身后的他们,他们也就在尼玛村长的身后突然停下来看走在最前面的他。那时,凹村人的眼神都落在尼玛村长的身上,人看见尼玛村长才安心下来,继续转身往前走。也有过一些人走神的时候,尼玛村长前面突然停下来,跟在后面的人突然停下来,队伍中的那么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走了神,在突然停下来的队伍中摔了一个大跟头。尼玛村长一看,就知道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心早就不在自己带的队伍里,他破口大骂这一个或两个不安心走在队伍里的人。尼玛村长骂人的话又重又硬,跟石头扔向一个人似的,落在人身上钻心的痛。凹村的牲口也怕尼玛村长的骂,一见他嘴里的骂要出来了,一趟跑得远远地躲着他。凹村的牲口是聪明的牲口,它们知道石头越远越打不痛自己。尼玛村长骂,那一个或两个走神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听,他们知道尼玛村长骂够了,就不会再骂了。今天,人不想在一支送葬的队伍中挨尼玛村长的骂,就像他们不想在下地干活的队伍中挨尼玛村长的骂一样。
尼玛村长越把脚踮得高,人就越把自己踮得高。人是一心想让村长看见自己。人心里鬼得很,在一条去西坡的路上如果被尼玛村长骂了,这句话会永远落在西坡,无论凹村多大的风,多大的雨都无法把这句挨骂的话带走。这句话就像种在西坡路上的一棵草,一株野刺巴会顽强地活自己,等到自己咽气来西坡的那天,跟着自己进西坡的坟堆堆里才算了事。一句在西坡路上挨骂的话,会被带到被挨骂人的下一辈子里。谁都不愿意一句上一辈子被骂的话继续沿到下一辈子再去骂自己。在西坡被村长骂的话,不像在凹村田间地头被村长骂的话,虽然话可以是同一句话,可同一句话落的地方不一样,话也显得不一样了。人都要小心在西坡的一举一动,西坡是凹村每个人下一辈子的入口,下辈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光靠人猜是猜不出来的,光靠人想也是想不出来的。人都要在去这条西坡的路上小心很多事情,尽量小心不出什么差错。人想的是下一辈总不可无缘无故为难自己,一个没出过大差错的人下一辈子也找不到为难自己的理由,人相信下一辈子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下一辈子,要不一切不就乱了吗?
那尼玛就不怕下一辈子吗?去西坡的路离下一辈子最近,尼玛有次就在这条路上狠狠地骂过一个人,骂到后面不解气,还踹了那人一脚。尼玛骂出的那些话和踹给那人的那一脚永远留在了西坡,留在去下一辈子的门口上。一个敢在下一辈子门口上踹人一脚的人,下一辈子也不会对这个人有什么好印象,你想想看谁愿意看见别人在自己家门口踹人骂人,那踹出去的一脚万一踹得不准,伤了自己家的一扇门怎么办?那在门口骂出去的一句话的声音,会通过一扇门的缝钻进自己的屋里,自己家屋里全是那个人骂出去的那一句话,像在骂屋里的全部人。
有人说尼玛不怕,尼玛是村长,村长是一个村子里的大官,你们没看见村长骂一条狗,狗被骂得在一个角落里呜呜地哭吗?你们没看见村长骂几只公鸡打鸣太早,那几只公鸡从此就哑了自己吗?你们没看见村长骂一片地里的玉米长得太慢,那块地里的玉米就在一夜之间长高一大截吗?村长骂什么都是应该的,就像我们挨村长的骂也是应该的。他是村长,即使在西坡的门口村长骂人踹人,下一辈子也认村长这个人,因为下一辈也知道村长是凹村的大官。官是可以从这辈子骂人骂到下一辈去的人。
我高高地站在石头上看这支送葬的队伍,我那天心被什么掏空了一样,让我想不到尼玛村长的骂。这支队伍走在去西坡的路上,缓缓的,遇到小路的弯自己的身体也跟着弯一下,遇见小路的直自己的身子也跟着直一下,遇见路中间长树的,路围绕树转半圈,人也跟着路转半圈。去西坡的人,自己心里没有路。看着他们,让我想到我在村子的土路上见过的一群秋蚁。那群秋蚁是一群靠近冬天的秋蚁。它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向一个自己躲不过的冬天接近,秋风吹着它们,秋风正在带走它们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些丢失在秋风里的东西让它们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薄。它们在一条路上走得无精打采的,走得有气无力的,走着走着有些就倒下了,其他的秋蚁不管那些倒下的秋蚁,它们知道倒下去是每只秋蚁必须面临的事,谁都不知道谁会在哪个地方、哪个拐角说倒下就倒下了。那群秋蚁跟着一条土路继续向前走,土路把它们引向一条凹村的溪流,路不走了,秋蚁不走了。土路在一条溪流边折断了自己,秋蚁想路都断了自己,自己也该了断自己的时候,我看见一只只秋蚁前仆后继地往一条溪流里跳,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一会儿一群秋蚁就到了自己的下一辈子去了。一辈子和一辈子之间有时就是一会儿的事。
去往西坡这条路也是一条断头路。无论凹村人去过多远的地方,走了多长的路,翻过了多少座山,路过了多少个草原,最后都会回到这条去往西坡的路上。凹村稍稍长而更醒事一点的娃,一天东想西想,没长熟透的身子在凹村长,心早早飞到远方去了。娃对远方总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和渴望。他们经常说,自己有机会了,一定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一趟,他们可以在最远最远的地方重新养一头牦牛,盖一座泥巴房,重新开一块荒地,种上一年的青稞,青稞一年比一年增加,他们在远方的家也一年比一年像个家了。上点儿岁数的老人把那十多岁的娃的话听进心里,边听边一眼一眼地看去西坡的路。十多岁的娃往老人看的方向看,一条去西坡的小路已经被他们看了十多年了,他们没有耐心再看下去。老人不向娃点明什么,有些东西是需要自己去领会的。只有老人心里亮堂着,离凹村最近的一条土路,也是带着凹村人走向最远地方的路,远到遥遥无期,远到和下一辈子接上了。
尼玛村长站在人群最前面,像一群放上山的牦牛的头。见我站在石头上,他用鼓鼓的眼睛瞪我,尼玛村长那天的眼睛无论怎么瞪我,都少了一种平时的凶气。但是一旦尼玛村长把头转向其他人,那股凶气又从他的眼神里漫了出来,吓得其他的人急忙把头低下,跟刚刚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似的。松尕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一把把我从石头上拽下来。
“你个牛犟的今天是咋了,叫你哭你哭不出来,叫你走你不好好走,你是诚心要和你阿爸对着干是不是?”松尕说着话,送葬的队伍慢慢往前走。
“松尕,你死了也要走这条路是不是?你死了也要我这样送你是不是?”我边随着人群走,边对松尕说。
“盼着我死?没良心的,枉我对你那么贴心。你放心,我骨头硬得很,石头一样,离死还远着。”松尕气得脸红红的,额头上的青筋从他皮肤下面冒出来,像一条蚯蚓在他额头上爬。
“我刚才站在石头上,看见了好多人的死。我们都是排着队往西坡赶死的人。”我盯着松尕看,他额头上那条像蚯蚓的青筋刚要钻进松尕的脑袋里,又被我的一句话唤了出来。
“你能看见死?你又不是宫巴?你个牛犟的,不是看今天这种场面,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松尕说完,缓了下来。那条蚯蚓一样的青筋,因为松尕的缓,慢慢钻进了他的脑子里。一只蚯蚓在像松一块地一样松松尕脑子里的东西,我想。
松尕说得对,今天是一个大场面,是阿爸这辈子遇见的和自己有关的最大的场面。我不说话了,我想和其他人一样,好好送阿爸。
“你看见第一个死的人是谁?”又走了一段路,松尕突然问我。他斜着眼看我,松尕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忧郁的光。我看见自己映在他的眼睛里,小小的,正被他眼里忧郁的光淹没。我想那只蚯蚓在松尕的脑子里起了作用,虽然我说不清楚那作用是什么,但松尕就是和前面不一样了。
“你是不是松尕?”我怯怯地问。
松尕嘴角往上扬,眉毛朝下耷拉着,他说:“牛犟的,是,当然是。”
我还想给松尕说点什么,松尕也还想问我点什么,敲家什的师傅停止了手里的活,坟地到了。阿哥、阿姐走到了人群的最前面。我知道这时我也该走到人群的最前面去了。
黑黑的棺材斜靠在长满荒草的斜坡上,棺材下面架着粗柴火。几位喇嘛坐在长满荒草的斜坡上念诵着经文。村里的人围在棺材边上,默默地听着诵经声,默默地看着棺材。那一刻,我们都是心中长满荒芜的一群人。
尼玛村长点燃棺材下面的柴火,熊熊的火焰瞬间吞没了黑黑的棺材,所有人的脸上、身上、眼睛里都映着那团火的样子,那时人心里都有一把火燃烧着自己。谁都知道,这把火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终究会落在自己身上,这一生谁也逃脱不了西坡一把火对自己的追赶。
天空中的毛毛雪还在飘。火不只燃烧着我的阿爸,还点燃了飘散在空中的雪。这场被大火点燃的雪落进了我一生的命里。
这场火是燃烧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火。
我在一场毛毛雪中,记住了这场火的样子,它猛烈,汹涌,像是要把自己一起燃烧。这场火的样子至始至终没让我面对它哭出一声,我心中的冰凉一场火无法点燃。
两年之后松尕走了,我们用同样的方式送走了他。我有些后悔,那天在送葬的队伍中,应该把我看见松尕的死早早告诉他,让他早早为自己的死做好准备,让他不至于到自己的死亡来临时感觉自己的死那么突然和仓促。其实,我还想告诉松尕,死并不可怕,这两年死一直默默地陪着他吃饭、睡觉、种地、做梦,死也像一个温和的人。
原刊于《长江文艺》2022年第1期

雍措,四川康定人。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期刊。出版系列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作品收入各种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