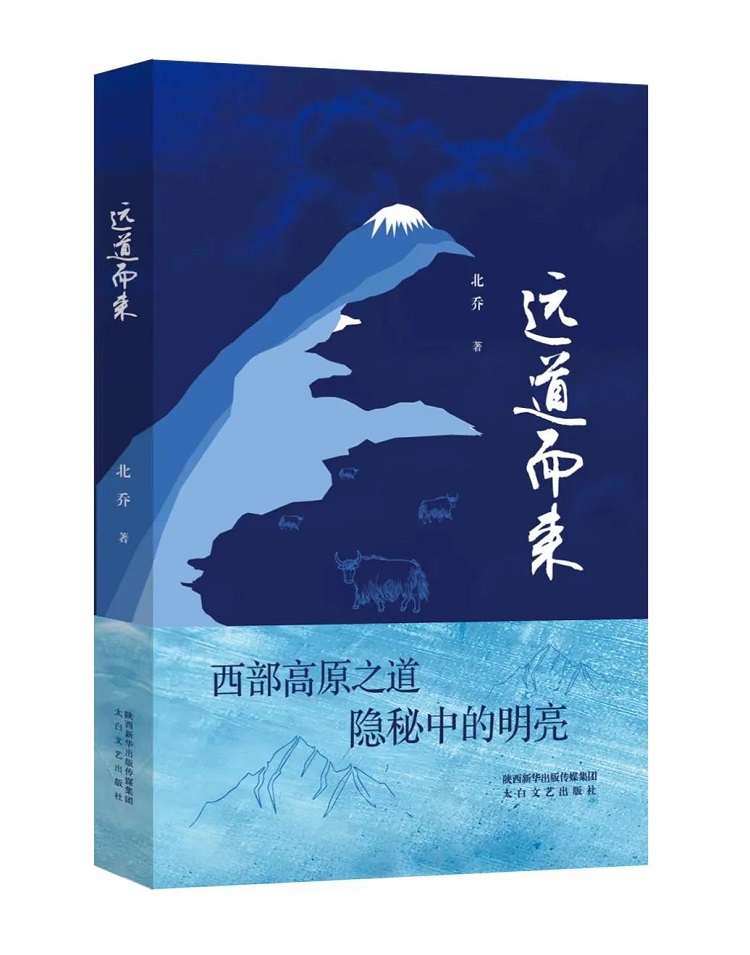
《远道而来》(北乔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从北京去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挂职,确实是我生活中不小的意外。但一旦定下来后,我想在高原上三年,我得写点东西。渐渐,我的目标明朗了,为临潭写一本书。我的动机也走至最朴素之处,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临潭,并能到临潭去体验一下、游览一下。近些年,甘南和临潭,都在发展旅游经济。我愿意尽我所能,做点贡献。
朴素的情怀,需要文学的准备和行动。我不是导游,也不是形象代言人,我是作家,那么就应该用作家的方式书写和表述临潭。以某一地域为书写场域,并力图全面且深入地呈现,我以为散文还是最好的体裁。
问题在于,当下的散文写作纷繁多样,都有一定的成功范式。比如生态散文,比如游记式散文,比如历史散文,不一而足,但共同点在于,都是就着某一路径和向度生猛发力。极致,当然是文学重要的强度和深度所需要的,也是文学力量重要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些“套路”,不是临潭所需要的,自然也不是我想采用的。
常常就是这样,看似下定了决心,做足了准备,但真要开始时,反而是一片茫然。我迟迟找不到我想要的叙述路径。偏偏,突如其来的诗歌写作,似乎又打乱我的节奏。这说明,我的决心有些空想,我的准备其实很虚。是的,前瞻性的准备必不可少,但更需要我们进入现场,有所了解之后,做一些贴近式的实质性的准备。在部队,这叫“实战性训练”。
散文没能如期进行,在彷徨中,诗半路杀出。人生近半百,写作20多年,竟然开始写诗,那么最初几年对诗异乎寻常的激情,自然可以理解。在我挂职期间的2018年7月,诗集《临潭的潭》出版了,散文写作计划尚未完成,这的确在意料之外,绝对的意料之外。当然,除了工作、生活的变动,除了写诗以及时间的挤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究竟要写出什么样的散文,究竟要给高原之上的临潭奉献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是我对散文创作的思考,更是希望对三年的高原生活有比较厚实而真诚的回报。
我确实对书写临潭有整体性的考量,比如我主编临潭70年文选《洮州温度》,意在梳理并呈现临潭文学一路而来的足迹;主编由临潭人自己写的脱贫攻坚的《临潭有道》,真实地叙述写作与现实生活的热烈互动;我的诗集《临潭的潭》,则是记录我瞬间的心灵颤动。那散文呢,理应全面建构文学上的临潭。一切都直面当下,当下又是历史、岁月、人文、风情等全时空的交汇。
到临潭一年多后,我才开始了《远道而来》一书的写作。最终我选择了散文创作不是套路的套路,尽可能回到散文所有特有的辽阔,保持心灵的敏感,牵手散文的无拘无束。这次的写作,时空跨度确实有些大。从高原下来,我还在写。
业余写作,当是一种日常工作、生活的穿越。
这个时间,当然只能会在夜深人静之后。
结束一天的工作,收拾好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当一切可以暂告一段落时,终于可以另起一行。从大世界钻入小书房,从喧嚣溜进安静。这是肉身的归位,也是心灵的觉醒。
当然,我的业余写作过于极端的业余。很不幸,无论我们多么敬畏、尊重文学,但在现实中,文学创作其实基本上还是不务正业。在我写作的最初20多年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如此一来,工作时间不敢写,也不能写;白天没空也没心思写。在当图书馆馆长的那五六年里,工作节奏和内容由我掌握,偌大的办公室,很少有人来打扰。这当是写作的最好机会。为此我曾努力自我治疗,然而几经周折,总是无法打破桎梏。好吧,只好作罢。如此,写作的业余性彻底被坐实了。白天不行,在办公室不行,只能在夜晚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才可以进行文学写作。
有些作家可以不分时间地点,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写作状态,真的好羡慕。
而我,毛病就此落下了,没救了。
说这些,好像是为自己写的少找理由,寻求一些自我安慰。不然怎么办?要保持好的心态,就得如此,当然也别无他法。
其实众多的写作者都是如此,只有在人间某个无人打扰的角落,才能在写作中进入那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抽身而出,在逼仄中宏大,这是业余写作者的宿命。因为业余,多了一份随性,更有了以生活之余音充实人生的愉悦。2019年10月,从高原回到北京,我以为一切又可以回归平常了。没想到,三个多月后,又一次措手不及迎面而来。只是,这一次的措手不及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世界。
凡事总在变化中,但一定也有不变的;我们总会遇到慌乱以及偏离日常轨道之事,继而让情绪不安生,让心情不淡定,陷入漩涡之中,自己也成一个甚至数个漩涡。
路总是要往前走的,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事情总是要做的,有一些目标,总是不能放弃的。
转眼,离开三年的高原生活已两年多,但似乎还没有缓过来。比如长胖了,比如嗜睡了,比如反应迟钝了。在浅显的现实面前,高原又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之外,成了远方的远方。可是,高原已住在我身心里,无法抹去。进入这样的写作,更能让我快速地从日常生活抽离。这时的我、纸上的高原与曾经的岁月,完全在当下之外,不过,谁能说不是另一种当下呢。
如此这般,在一个个夜晚,在狭窄的空间里,我回到了高原的辽阔与深邃。那里的阳光照亮了我的血液,那里的风带我飞翔,那里的草木山水倾听我的呼吸,那里的人们如同我故乡的左邻右舍。
从高原到北京,从一个生活的漩涡到另一个生活的漩涡,算起来,从有创作动意到最后的定稿,再到出版,历时五年有余。这似乎也是一种远道而来。诗歌讲究实时反应,注重爆发力,散文需些一些沉淀,至少我的诗集《临潭的潭》和散文集《远道而来》为我自己作了这样的证明。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远道而来》,我希望这是一部西部高原之上临潭的文化坐标之书。
远道而来:以“归乡者”的身份为临潭立传
潭小融
近日,临潭首部文学意义上的“临潭志”,北乔散文集《远道而来》已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为北乔(本名朱钢)挂职甘南州临潭县委常委、副县长期间的重要收获,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时文化扶贫的成果,从历史、人文、生活情状等多重路径探寻和建构新时代语境下的高原,全景式呈现西部临潭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远道而来》是一部建构西部高原之上临潭文化坐标的书。这里的临潭,是高原平常而又特别的地域个案。这里的文化,是大文化概念。正因为如此,《远道而来》中的临潭,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脚下的一片大地。北乔以江苏人到甘南藏区高原工作生活的身份,将曾经的远方和历史的久远与当下的生活具像实现时空的叠现。文字浸染于诗意中,以朴素的气质出现,行文亲和,但又隐含深邃的隐喻和审美的诗性。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展开心灵对话,厚重中激荡轻盈。作者以当下状态为坐标,体味那些久远的历史、文化在当下日常生活闪现的永恒,实现视线和灵魂上与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性投射,在现实中寻觅历史或隐或显的延续与存在。在宏大的视野中,回到个体性的人,回到现实生活的日常。
《远道而来》以宏阔视野观照西部高原,以细腻笔法书写西部高原,以哲性诗意体味西部高原,点亮历史之光、纵情自然山水、状写人文情怀。既有对史料扎实细密的爬梳,也有荡开一笔对古代人事的遥想;既有对他人日常的描写叙事,也有对自我人生的回眸咀嚼。可视为以临潭为文化个案的大散文,极具哲学意味,在永恒与瞬间、遥远与当下、耸立与隐藏、鼓噪与沉默等诸多中国所特有的意象和意味中,探索或表达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类、大世界与小个人之间的关系。
《远道而来》的“道”,是指时空距离、历史风尘,更是指西部高原所特有的山水生态、生活情状和人文精神。因而,作者、高原和读者,形成了彼此的远道而来,又将建构另一种情感之道、审美之道和人文之道。
北乔在临潭挂职时,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润心,文学助力”的扶贫思路,在帮扶工作中显现了鲜明特色,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作协助力脱贫攻坚的特色贡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用业余时间积极书写和宣传临潭的自然和人文,先后拍摄了1万多张图片,撰写散文30多万多字,创作诗歌600多首,并通过网络新媒体介绍临潭,阅读量达100多万人次;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十月》《诗刊》等40多家国家级报刊发表各类文章560多篇(首),出版了反映临潭人文的诗集《临潭的潭》;首开助力本土作家出版专著之先河(五位作家诗人在作家社出版散文、小说和诗歌专著);写作文学评论推介临潭的文学爱好者,先后在《文艺报》《中国民族报》等报刊发表推介文章10多篇;主持编辑出版了全面展示临潭70年来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成就的《洮州温度——临潭文学70年》(三卷本)和反映临潭脱贫攻坚的纪实文学集《临潭有道》等图书,提高了临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在“洮州大讲堂”、干部夜校等各类培训活动中,为广大干部群众讲授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摄影专业技术、公文写作、临潭文化等,受众人数达到1200多人次。在三年的挂职期间,个人和中国作协先后两次分别被评为“甘肃省脱贫攻坚帮扶先进个人”和“甘肃省脱贫攻坚帮扶先进集体”。
原刊于《甘南日报》2022年5月11日

北乔,江苏东台人,作家、评论家、诗人。出版长篇小说《新兵》、小说集《天要下雨》、散文集《三生有幸》、文学评论专著《约会小说》、诗集《临潭的潭》等10多部。曾获第十届解放军文艺大奖、第九届长征文艺奖、六次武警文艺奖、第八届黄河文学奖、第六届乌金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第三届海燕诗歌奖、第四届刘章诗歌奖等。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