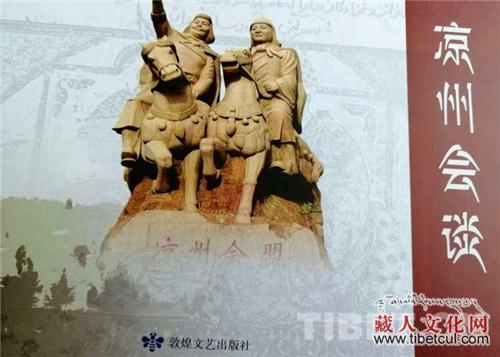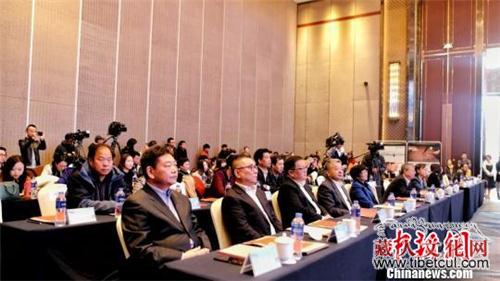写真:藏人在北京
图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 文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贺佳雯
藏人万玛尖措用“微妙”来形容自己二十余年的生活对北京衍生出的感情。“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过客,北京像个驿站。你想要去哪儿都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要坐下来喝碗茶。”
黑暗被一束光点亮,深蓝色地毯上一无所有。在藏乐与银铃的交响中,舞者们以彩色沙粒作画,色彩斑斓。最后毁掉,一地散沙。
这一幕“坛城沙画”是一种藏传佛教的行为艺术。它在叙述生死轮回的观念:“人的一生有不同的欲望,你的经验、记忆可以成就你一个非常灿烂的人生。但当你死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也是让你放下那份执著。”

万玛尖措,青海安多藏区人,生于1979年,舞蹈编导。 一粒粒细沙汇聚成绚丽画作,却在顷刻被毁。这一“坛城沙画”的场景,是舞剧《香巴拉》的高潮。万玛信仰藏传佛教,生死轮回,万物皆空。 很长一段时间,万玛整个人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在藏族文化与主流汉文化之间,找不到身份认同感。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2014年4月20日下午,由万玛尖措编导的舞台剧《香巴拉》在798白玛梅朵艺术中心举行答谢演出。
十二三岁来京,万玛尖措在中央民族大学念附中、大学、研究生,一路学了十年舞蹈。早期的实验舞台剧《狼魇》,讲述一个牧民到城市打工,从身体里分裂出一种狼性的故事。“他的本性和他的城市化生活一直对立,从而进行一些非自我的判断,像那时的我。”万玛尖措解释。
万玛尖措的舞蹈创作,大多依附于藏族文化,融合现代舞剧元素,找寻着自己心底的民族归属。业余画家吾要称万玛尖措是自己的藏族朋友里一个优秀的后辈。

吾要,青海省玉树人,生于1963年,美术编辑,业余油画家。 吾要画画就在家里,基本在晚上,或用一些零碎的空隙时间。但他说自己随时很快进入状态。一进家门,左手一伸就能摸到一墙书,书架上一半以上是藏文书,而编者一列印有吾要名字的不乏少数。白天,他在民族出版社的藏文编辑室里工作。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吾要习画喜欢用藏纸。他揉搓着藏纸,说藏纸粗糙,但可能由于高原植物所造,更有朴实自然的感觉。
年轻时,吾要的自行车有两个用处,一是飞骑到圆明园画家村,和自由画家们说画;二是赶去大钟寺买菜,因为传统市场的蔬菜相对便宜。
在朋友看来,尽管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吾要的生活仍一如既往地单调,少外出活动,无非办公室、画展、家三点一线。
“不是住了多少年,就能了解多少,认可多少。”吾要坦言,“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文化上的内心情怀,都不同。”
屋子里弥漫着藏香,家中摆件都是吾要夫妻俩一件一件从老家玉树带来北京的,大至书架上的野牛头,小至佛珠挂饰。四年一次探亲假期,一次假期十余天,路程往往就耗掉一半时间。
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张黑色面具,是吾要在家和弟弟合做的。玉树地震中,吾要的父母和弟妹遇难后,吾要很少再回老家,不敢问候老乡,“不知道怎么问候,想知道又不想知道”。
相比于吾要的健谈,他的朋友导演万玛才旦寡言,说话时一直眉头微皱。
他在工作室和剪辑人员沟通,说藏语,终于笑了。
但就在他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简笔漫画,只勾勒出鼻子以上的脸,竖直的头发、倒八字形浓眉和眉心两道皱纹,再架上一副眼镜。题为:万玛才旦发飙图。“朋友画的,挺传神。”他说。

万玛才旦,青海省海南人,生于1969年,导演。万玛没能带我们去他的片场,因为他一直在藏区拍摄。和其他导演大同小异,他作息无规律,工作的时间一直长于生活的时间,忙起来一天20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在工作。工作室到家步行两分钟,因为就在同一个住宅区里。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2005年,万玛才旦正在编导自己的处女作——纪录片《静静的嘛呢石》,当时14岁的杨秀措也参演其中。那年春节,杨秀措第一次到北京,在欢乐谷做了一个月的舞蹈表演。其间唯一一次出行,她想和朋友们一起去北京最繁华的地方逛逛。他们辗转三趟公交找三里屯,结果走错路,误入雅秀服装市场,以为是三里屯。“原来也就那样,还不如我们西宁。”杨秀措有些失望,和朋友们吃了一顿肯德基。
再到北京发展,已是六年之后。杨秀措很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嗓子干哑,饮食方面亦有很多为难之处。工作饭局,自己不能吃海鲜,有忌口,但很少表现。“毕竟好不容易来了。”她一直逼自己适应和努力。
“大声地跟着念,现在看来有点傻。”第一年,杨秀措全国各地忙,作息很不规律。但有一件事她坚持做,每晚七点,跟着《新闻联播》里的主播,学说普通话。

杨秀措,青海省海南人,生于1991年,演员。 杨秀措以演唱藏族民歌见长,在2010年《花儿朵朵》选秀中获全国4强。但2011年春节后一来北京,因为难以适应气候,嗓子变哑。之后调整一年,才适应了北京的干燥。 那一年,她全国各地赶通告,但天天惦记着家里的藏餐。
与杨秀措熟识的措东,也说自己难以适应北京饮食,只喜欢藏餐的酸、辣。
在15岁学习马术之前,虽然出身马背民族,措东却一次都没有骑过马。他之所以加入西藏马术队,是因为他向往这项“绅士的运动”。
1992年,措东来到北京体育大学。自此,他跑了11年的舞步马。“比西藏还冷!”当时的北京体育大学还没有室内马场,冬寒使得训练异常艰苦,措东骑马时两腿直哆嗦。
十年前,措东与一位江苏姑娘结婚,一天内操办了西式、中式和藏式三场仪式。西式婚礼上,新娘骑着措东的爱马“珠穆朗玛”,一袭婚纱配一匹白马,甚是浪漫。藏式婚礼上,三百多位观众为新郎新娘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祝福。
从山东坐火车到青海的格尔木,再坐汽车沿青藏公路驶进拉萨。“一共是8天8夜,人和马都在车里,闷在一个空间里。每到一个站,先给马打水喝,他们是战友啊!”离家两年后,措东第一次回到西藏。“过了那曲,汽车一点一点接近拉萨,我们开始能一点一点看到布达拉宫,一看到布达拉宫的屋檐边角,所有人都流泪了。”

措东,西藏林芝人,生于1972年,国家马术教练。 措东背部带有痼疾后,就很少上马背了。现在,“东哥”手下带的西藏骑手,常在国内外比赛中跑出佳绩。杨坤、沙宝亮等人也曾拜师门下。 谈国发马场的马,措东如数家珍。他把每一匹跟随自己的马当作战友。“来,小伙子!”他和马对视着,马就安静下来。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措东说自己在外面受的苦,从不跟家里说。只有曾干过马匹养殖的父亲,能明白一二。
而今,离措东上一次回西藏,已经过了六年。他打算今年回家看看。
万玛才旦让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休学半年,回老家学习藏语,再回来考初中。他自己则计划着近几年内整合在北京的资源,回到藏区。
吾要觉得自己回不去了,工作和家庭都在北京。但他对家的概念仍停留在小时候“藏区的家”。北京于他而言,“只是在这儿生活”。儿子今年20岁,正是当年吾要离家的年纪。但他生长在北京,喜欢篮球,不懂藏语。
万玛尖措用“微妙”来形容自己二十余年的生活对北京衍生出的感情。“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过客,北京像个驿站。你想要去哪儿都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要坐下来喝碗茶。”
今年初,万玛尖措在新浪博客里发文《一朵莲花求包养》,为万玛舞团集资。如今,他正在串街走巷为舞团寻觅地价便宜的排练场地,也在想着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文化,将自己的舞蹈与之结合,演一些北京的故事。
“感觉,很陌生。”吾要说北京时,像是在说一个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