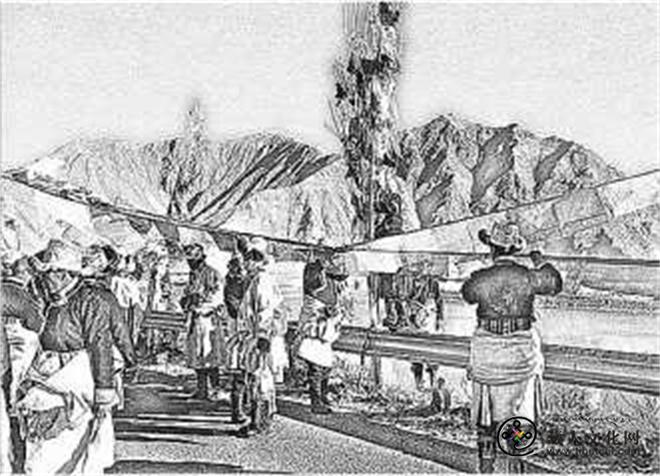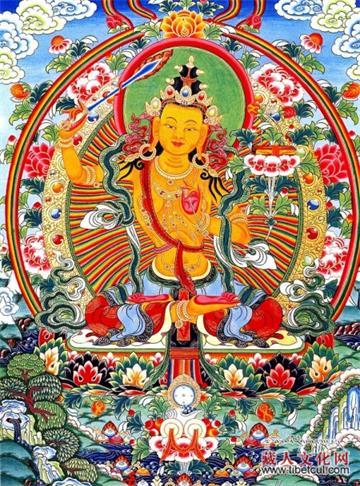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内容摘要:由于不稳定的历史环境和宗教政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复杂多变。本文为论证宗教与政治相互攀附与共生的关系,以明代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进行梳理、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木氏土司;噶玛噶举派;政教关系
一、引言
近代以来,宗教在一个国家或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日益凸显,正如罗伯逊所言:“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宗教主题在于宗教政治的问题,全球化同时导致了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过程。”政治是人们在一定基础上围绕着特定的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而宗教具有理想和现实的两重性,即形象形容为:“宗教的花朵盛开在天国,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没有自己的宗教,宗教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部落、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两者相伴始终,此消彼长或共生共荣,是一个密切联系的统一体。
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汇集云南,共生发展,和谐相处。在此,笔者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为切入点。纵观中国古代的佛教史,不难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直接影响了佛教的兴衰发展”。当统治者崇信佛教时,正如梁武帝“溺于释教”时,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教盛况。南诏时期,“信奉佛教的是以国王、王妃为主的贵族、统治阶层。特别是造寺、造塔都是由王室承办”,王室对佛教的提倡使得南诏以及大理国佛教繁荣兴盛。相反,当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僧侣集团危及到统治阶级时,统治者会毫不留情打击佛教,如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几千年来,经过一次一次的打击限制,僧侣佛教始终在统治者的掌控范围内,并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
二、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分析
(一)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发展。纳西族先民在古代有“摩沙夷”、“么些蛮”之称。在唐代吐蕃王朝向东扩张,纳西族至迟与与藏族毗邻而居,至宋代,今云南丽江一带的么些酋长已有相当大的势力,大理政权竟无法征服。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蒙古军抵丽江后,木氏土司家族的先祖阿琮阿良内附,任茶罕章管民官,后又因功升茶罕章宣慰使。明初,统治者为防止北退蒙古草原的“北虏”南下与“南番”(藏族)联手威胁明朝在西南部的统治,这种情况下,“洪武十五年置丽江府。洪武十六年,蛮长木德来朝贡马,以木德为知府,罗克为兰州知府”,把镇守滇西北的边关要塞交给了对明廷忠心耿耿的丽江木氏土司。“丽江木氏土司历经元、明、清三朝传世22代,共470年,而尤以明代木氏土司承先启后”,在滇西北曾盛极一时。“北向藏区扩展,遂占今中甸、维西、德钦、理塘、巴塘、江卡(芒康)、木里及雅碧江一带的滇西北和康南藏区。”木氏土司军事扩张的同时,在宗教上积极结缘和笼络藏族宗教势力,在其统治境内采取“多教扶持、以教治教”宗教政策的同时尤为尊崇藏传佛教的支系噶玛噶举派。
丽江地处滇、川、藏交汇地带,具有多民族多宗教的属性,是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多民族的属性要求多宗教去满足其宗教信仰的需求,因此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及道教等宗教教派及同教不同派系汇聚于此,明代丽江白沙壁画生动体现了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宗教政策。表现出木氏土司吸收各种文化思想、融汇多种宗教派别于一堂、实行兼收并蓄政策的意旨。由于地缘就近原则和民族基础,藏传佛教在丽江更占优势。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言:“木氏土司,盛于明,多留遗迹唯宗教以喇嘛教为最多。”
(二)噶举派佛教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噶举派的分支噶玛噶举派是最早传入滇西北的派别之一。11世纪末,噶玛噶举派从西藏和康区两条线路传入云南的德钦、中甸、宁蒗、永宁以及丽江等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聚居的滇西北地区。该支派的开创者和名僧大多出自康区,其创始人都松钦巴在康区活动时,曾到过丽江一带,与木氏家族有过联系。
噶玛噶举派的发展轨迹多少与木氏土司有点相似,都是发迹于元,盛于明而衰于清。噶玛噶举派与中原王朝有较为密切的交流,在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时会见了该派首领噶玛拔希(1204~1283);随后,元文宗、宁宗下诏宣黑帽派第三世攘迥多吉(1284~1339)进京弘法;明初,第五世黑帽活佛得银协巴(1383~1415)应召到南京,在1407年被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这是藏传佛教徒视为最尊贵的封号,这封号在明代成为黑帽系的历代转世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一直到明末。
(三)土司与噶举派结缘,政治与宗教相互攀附与共生。历代木氏土司积极结缘宗教首领。自从第七世木氏土司木定(1484~1526)开始,木氏统治阶级就开始信仰藏传佛教中的分支噶举派,随之,也在其统治领域内传播开来,信众附归,佛塔林立。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木定邀请噶举派第八世黑帽系活佛弥觉多吉(1507~1554)到丽江弘法,受到木氏土司及其属民的盛情款待,并为王室成员灌顶祈福。值得一提的是,噶玛巴活佛与木氏土司达成协议“木氏土司应允在13年中间不向藏区派兵,并每年派僧差500名,建寺院百座”。这份协议的签订表明木氏土司和噶玛噶举派成为同盟关系。在木氏土司政权的庇护下,丽江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主要传教区,著名的“降13大寺”陆续建成,木氏政权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滇西北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支持。
大藏经《甘珠尔》是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第十三任木氏土司木增(1587~1646年)执掌大权时期,他资助并邀请了六世红帽活佛却吉旺秋(1584~1635年)到丽江王宫主持刊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这部《甘珠尔》称之为《丽江版甘珠尔》,是折装本。大藏经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总汇,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是佛语部,收入赞颂、经释、咒释等。刊刻期间,噶玛巴活佛的众多活佛弟子以及噶举派其他教派的僧人也来到丽江参加这一浩大的工程,并成为噶举派高僧们的神圣聚会。这套共108卷的《甘珠尔》历经9年,终于在1623年完工,这是佛教史上的创举。后部分毁于战火,现拉萨大昭寺还珍藏着朱印版的《甘珠尔》,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
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1604~1674)时期,“正是明朝晚期中央王朝权势衰落、蒙藏两族地方势力相互要结、甘青一带和卫藏地区纷争扰攘的时候”。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之间的资源争夺一直较为激烈,其中,噶举派和格鲁派的斗争既是宗教派别的斗争,也是宗教背后政治力量的较量,最终,噶举派落败,“噶玛噶举及其他一些教派被迫改宗格鲁派,从此噶玛噶举派在迪庆藏族地区日期衰落”。在和硕特部的军事打击下,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也由康南逐渐退缩到云南丽江木府所在的根据地。在此阶段,共同的敌人使得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之间关系更加亲密,形成同盟关系。
政教关系并不是绝对稳定的,也会因为政治利益和社会环境有所调整变动。赵心愚认为,从双方接触,建立关系,到清康熙年间木氏土司势力彻底退出中甸,这一关系维持的时间长达四五百年。在此期间,“土司面对康藏地区教派林立、各有其宗、互为牵制这一状况,为了稳固和加强自己在藏区的统治势力,积极遵循并具体实践了明王朝‘多封众建、以教治教’的治藏宗教政策”,采取多派扶持、宗教宽容政策。这其中,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更具典型和特殊。虽偶有摩擦,总体上保持着和谐相处的政治关系。
三、宗教与政治保持着一种利益至上、松散的联盟关系
“宗教与政治的互动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由此形成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即所谓政教关系,一般指的是特定的政权与存在其治下的宗教之间的各种关系。”政教关系因历史条件的复杂性也呈现不同的型态,通常有“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种形式。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应归于“政教分离”的形式,该派活佛僧侣们长期周游各地,传法收徒,以保持该派的实力和宗教地位,据史料记载,该派并未参与到木氏土司的政权中来,双方一直保持着一种利益至上的、松散的联盟关系。
木氏土司和噶玛噶举派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前提是各自双方拥有势力以及利益,这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基础上相互依赖和利用的关系。一方面,从统治阶级视角来看,佛教教义有利于安抚、教化百姓,麻痹群众的反抗意识,因而扶植佛教对维护当时的统治大有裨益。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藏传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天堂地狱”等思想,对纳西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个社会阶层的信仰统一化,有利于增强治内百姓对木氏土司统治的认同与拥护,忠诚并捍卫木氏土司的权威。即“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借助宗教信仰来支持其统治意识形态。统治者的主导意识形态经常需要某种宗教或者准宗教的信仰体系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后盾,以赢得民众的支持,避免社会动乱,防止政权垮台。”另一方面,噶玛噶举派则利用木氏土司在滇西北和康南的势力为其宗教传播保驾护航。木氏土司武力开道,噶举派宗教收心,合作共赢。
总体而言,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互动是一种良性的政教关系,权力利用宗教,宗教依附于政权,两者牢牢地把控了本地区的信教群众的经济政治生活。时至今日,政教关系仍是国家乃至地区和谐安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处理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是政界乃至学界仍然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余嘉华等.木氏土司与丽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黄海涛.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4]何其敏.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J].世界宗教研究,2001,4
[5]赵心愚.略论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J].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6
[6]南史.武帝纪论(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8](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王尧.走近藏传佛教[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冯智.丽江藏传佛教壁画及其历史研究[J].西藏研究,2008,1
[11]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147
[12]王彦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滇西北的传播及其影响[J],西藏研究,2014,3
[13]顾肃.政治与宗教[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4]徐丽华.藏文化与纳西文化的交流[J].青海学院学报,2001,2
[15]施仲军.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J].学术探索,2003,1
作者简介:颜学珍(1993~)女,重庆奉节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原刊于《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年第18卷第6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