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第三世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述丰盈,涉及佛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等多学科领域,影响深远。本文以其历史名著《如意宝树史》为文本对象,分析松巴堪布对历史文本的选择、运用和批判,探讨其历史书写的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和话语特征,多维度阐述其治史方法和写史风格。
关键词: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历史文本:历史书写
青海佑宁寺第三世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年)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代名师。所著《如意宝树史》(全称是《印度、中原、藏区、蒙古等地之正法源流史一如意宝树》)是一部材料和思维并驾齐驱、考证和解释双管齐下的通史类著作,其修史风格体现了后世法国年鉴派奠基人马克·布洛赫和加拿大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等人提倡的“世界史”(global history)、“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和“关联史”( connected history)的治史方法,从而奠定了松巴堪布在藏族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国内外藏学和蒙古学学者对松巴堪布及其著作关注较早。20世纪80~90年代,《如意宝树史》被陆续译成汉文,引起国内学术界密切关注,相关成果主要围绕松巴堪布的生平事迹和其诗学、史学和佛学造诣展开①。国外研究松巴堪布的主要学者是印度的Sarat Chandra Das[1]、日本的长尾雅人等②,这些成果聚焦于松巴堪布的生平事迹和《佛历表》及文集的目录。从已有的成果中不难发现,学界对松巴堪布的历史书写风格,尤其是历史名著《如意宝树史》的修辞结构及话语特征未能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分析和考证。本文以《如意宝树史》为考察对象,阐述其在考据历史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区别、运用和处理不同的史料,探讨其历史书写的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和话语特征,多维度剖析其治史方法和写史风格。
一、史学传统与叙事创新:《如意宝树史》的史料运用与考证
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学界诸如“史学就是史料学”等论断强调了史料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在《如意宝树史》里,松巴堪布不仅对传统的核心史料进行了严肃的考证,更是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奠基人马克·布洛赫提出的那些边缘的“无意的史料”[2]作细致入微的甄别和取舍,这对于藏族传统的史学家而言可谓是重要的一步。从形式上看,史料包括实物、口述和文献史料。文献史料作为最主要的史料类型,是了解过去和考证历史最主要的依据。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对文献史料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考证创造必要条件。然《如意宝树史》的史料来源极其多元,不仅网罗了藏文大藏经、高僧名人文集传记、先人史学论著和格言哲理著作等主流文献,还涉及到实物遗迹、口述材料和旅行见闻等小众史学素材。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讲述中原汉地和蒙古各部的情况时,松巴堪布还引用了汉文文献和蒙文文献考据历史,并将其与藏文文献相比较,根据文献记载的异同,提出最终看法。《如意宝树史》极大地丰富了藏文史料的范围和类型,对不同史料恰当的运用和异同关系的深刻分析,成就了这部佳作在藏族史学之林中的典范地位。[3]
(一)实物史料
实物史料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包括建筑古迹、文物遗迹和绘画雕塑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类实物,是了解历史最为直观的证史材料之一。尤其对于没有文字的史前社会或者是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而言,实物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松巴堪布在《如意宝树史》之藏地所出律统与教派部分讲述藏地下部、上部和班钦等三大律统时,结合相关史料,分门别类地介绍和梳理了每一个律统在藏地的起源和传承次第。由于相关史籍对三大律统的顺序次第众说纷纭,他提到:“上述律统有许多不同的依据,桑耶寺壁画上说婆罗门罗睺罗的亲教师是舍利子;在有关律统传承的古籍中说萨罗诃的亲教师是黑色尊者,此与以往付法藏师传承似乎相合,但尚未见到可信的依据”。③为了厘清三大律统的先后传承次第,松巴堪布博览群书,发现各类史书对此事记载不一,随即考察了年代久远且保存较好的桑耶寺壁画,指出对婆罗门罗睺罗的亲教师是谁的问题,桑耶寺壁画与相关古籍的说法各异,松巴堪布虽然表明了文献古籍的说法似乎更为可信,但是没有找到其它可靠史料加以佐证,因此很难判断哪种说法较为确凿。在考证藏地三大律统的传承次序时,松巴堪布同时引用了实物和文献两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并加以比较,得出两者的异同。在没有第三方材料支持的前提下,松巴堪布认为两者各有千秋,无法判断真伪,反映了他对历史考据的谨慎态度。
松巴堪布对史料概念的拓展和史料类型的延伸得益于其广游四海、亲临其境的生动体验。他三赴北京和五台山、两赴西藏和蒙古等地,期间不仅深度观察了他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把这部分直观体验记录于自传和历史著作中,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丰富了史料的类型。
(二)口述资料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口述史料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材料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重视。口述史料是当事人凭记忆回忆过去,由史学工作者将其付诸于文字的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当文献史料对某一历史记录不详或有错漏,或是文献史料流失的情况下,口述史料能够修正、补充和替代文献史料而发挥独特的史学价值。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学者,松巴堪布在《如意宝树史》中使用大量篇幅论述宗喀巴大师的前世、此世和后世。该书的至尊上师宗喀巴部分是整本书中引文最多、内容最详细、篇幅最长的专题内容之一。对于宗喀巴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松巴堪布写道:“大师一生业绩中最为殊胜的是他经三量伺察而写成的清净著述。其中,有开示从因乘学规依止善知识的情况到寂止胜观、具足四大特点的广中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两卷,并从我的上师处听说另有一卷,故为三卷”。④至于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另有一卷的情况,作者明确提到这个消息是从上师那里听说的。在《如意宝树史》印度部分介绍印度的山川河流和城市居民的情况时,提到:“这些均按诸译师口传写出,至于汉和尚的《旅途纪实》中所述情况,将在后文述及”。⑤从中可知,松巴堪布对印度山川地理部分的介绍是基于远赴印度求学的藏族译师们的口头所言,这部分口述材料由于出自亲历印度的当事人的描述,这对于了解印度的地理概貌和古代城池,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三)多语种文献史料
1.汉文史料
在松巴堪布的史学著作中,多处引用了汉文和蒙文史料,实现了文献史料的多元化,有效地避免和订正了藏文史籍对有些历史问题的语焉不详和偏颇错漏之处,为厘清相关史学疑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为藏族史学之林中的典范之作。
《如意宝树史》专设独立篇幅讨论印度、中原和蒙古地区的王统世系和佛教的发展传播情况。松巴堪布在处理这些域外知识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参阅汉文和蒙文文献,并将其与主流的藏文史籍相比较,通过仔细甄别和反复比较不同语种文献史料的记录,归纳出不同史料的异同真伪,为澄清相关史学问题做出了极大努力。如,《如意宝树史》书中在言及元明两朝皇帝的在位年代和顺序次第时,曾有两处明确使用了诸如“根据部分汉史”和“还有一部汉文史册”等来表明相关引文和观点出自汉文史书;[4]又如,书中的第一总目简论佛陀出世说法及佛法住世情形之佛法住世部分,对于佛教自佛陀释迦牟尼以来传人世间已有多少年的问题,松巴堪布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印度、汉地和藏族史籍中的十余种不同说法来阐明问题的复杂性,并提到:“一些汉文典籍以及《青史》则认为佛于木虎年降生,水鸡年圆寂,佛教已住世三千零五十四年或二千四百九十六年”。⑥此处,虽然松巴堪布没有明确点明他当时参阅的是哪部典籍,由于佛教传人汉地早于藏地,因此他认为汉文史籍对佛教传播情况的记载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予以引用。
2.蒙文史料
除了汉文史籍外,松巴堪布在《如意宝树史》相关章节多次引用了蒙文文献考证历史疑难问题。如,有关成吉思汗的生卒年代和身世家族,“成吉思汗生于火虎年,且认为是孛儿帖赤那的后裔,但在霍尔人自己的所有新旧历史典籍中,说汗朵奔蔑儿干去世后,一道光明入其王妃之体,后生下三子,其中孛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另一部霍尔史书中说王妃梦中与神子相遇,而生下一子。但无论怎样说明成吉思汗为朵奔蔑儿干的后裔,于水马年降生,《青史》所载于此矛盾。《青史》中对汉、蒙王统的大部分记载同汉、蒙本身的记载不相符”。⑦《青史》作为藏族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对于汉蒙古王统的记载多有偏颇之处,松巴堪布把《青史》和汉文蒙文史料加以比较,指出《青史》记载多有错漏,表现了松巴堪布不迷信经典,也不单一引用任何一类资料,他总是在认真比对不同类型的史料并逐一分析每种史料异同真伪后,归纳出一个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松巴堪布对蒙文史料的重视和引用在《如意宝树史》中比较凸出。对于蒙古王统的起源,松巴堪布提到:“现今蒙古地区的部分史册说孛尔贴赤那的父亲是色赤巴,似将天赤七王的最后一位斯赤巴误称为色赤了” ⑧以上表明,松巴堪布不仅引用了同时代蒙文史料,还指出把蒙古第一个王的父亲说成是色赤巴是一种讹误,很可能是将其与斯赤巴相混淆而导致了这一错误,反映出松巴堪布既重视蒙文史料,又严格把关的严谨学风。另外,关于从成吉思汗到妥懽帖睦尔的蒙古诸汗王的在位年代,松巴堪布在《如意宝树史》中也引用了蒙文史料进行了考证,书中指出:“蒙古诸汗王在位的年代,在一蒙古史册中,说成吉思汗从木牛年登位,在位三十五年,窝阔台在位三年,蒙哥汉在位六年,……另一史书中则说成吉思汗从木牛年至火猪年间在位二十三年……”⑨虽然松巴堪布没有在文中说明他参阅的具体是哪部蒙文史书,但对蒙文史书的大段引用却贯穿于本书蒙古部分的始终,表明了松巴堪布对原始史料的重视。
3.藏文史料
藏文文献是松巴堪布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支撑材料,不同类型的藏文文献在松巴堪布的笔下得到相得益彰的运用,使松巴堪布对历史一般问题和疑难问题的梳理和考究成为可能,最终成就了一位既浸染了传统史学的熏陶,又洋溢着鲜明个性和勇于学术革新的史学奇才。
从松巴堪布的史学巨著《如意宝树史》中能够体现出他在史料方面的高超造诣和对不同藏文资料别具匠心的选取和甄别。该书涵盖了从《甘珠尔》和《丹珠尔》佛教典籍到古印度大师的经典佛学著作、藏族史家学者的经典之作。书中反复引用的《甘珠尔》⑩《丹珠尔》⑪中的内容,以及《八十四大德传》《青史》《柱间史》《莲花生传记》《噶当文集》《布顿佛教史》《白琉璃》、《白琉璃除垢》《黄琉璃》《嘉木样协巴佛历表》《西藏王臣记》《三律仪差别论》《萨迦格言》等引用最频繁的藏文著作。据笔者粗略统计,《如意宝树史》仅引文注释达460余条,明确指出书名的参考书目达250部,不论在引文注释和参考书目的数量还是规范程度方面,《如意宝树史》代表了藏族史学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其成就不仅在于其海纳百川的信息容量和旁征博引的资料支撑,更在于对这些材料的分类解读、存疑批判、谨慎甄别和严格考证,反映了松巴堪布崇尚考据的史学特色和以史料说话的史学态度。细究松巴堪布的历史著作,不论其讲述佛教传播历史的鸿篇名著《如意宝树史》抑或是介绍青海蒙藏历史的小篇幅著作《青海历史梵曲新音》,还是他与第六世班禅罗桑班丹益西(1683-1706)和第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等同时代的巨擘泰斗以书信探讨学术疑难问题时形成的《清净经论除垢之澄水珠宝》和《内明典籍中部分名言疑难之答案汇编》,均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松巴堪布对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以及在考证历史的过程中对史料选择、史料辨伪、版本校勘、文本批评和历史话语分析等方面的独到见解。松巴堪布把哲学的思辨带进了史料甄选和历史书写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史学传统,在藏族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学批判与历史写作:《萨迦格言》对《如意宝树史》的影响
不同于一般历史著作的严肃性,细读松巴堪布的史学作品,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写作充满着生动鲜活的个性,通俗易懂的写作方式和深入浅出的推理风格,使读者甘之如饴、回味无穷。如此避免了史学论著在表达方式上的枯燥晦涩,强化了阅读和学习历史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实为对藏族史学写作传统的一次大胆革新。
松巴堪布的史学作品具有鲜活的个人特征,这一点从作者大量引用《萨迦格言》这一文学作品能显示出来。《萨迦格言》作为藏族文学史上的瑰宝,朗朗上口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比喻使其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著作。据笔者统计,《萨迦格言》是整个《如意宝树史》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学作品,格言本身的语言特点和说理风格与松巴堪布对历史的表述和评论融为一体,反映了松巴堪布在历史书写风格方面的革新和突破,可谓是运用马克·布洛赫“无意的史料”之典范。
对于在宗喀巴大师师徒之前,在藏区历史上出现过一系列不纯正显密修持法,松巴堪布在《如意宝树史》藏区其它教派概说部分的末尾,专设题为诸学者对藏区所出不纯正显密修持法驳斥的一小节篇幅,较为全面地厘定了藏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对戒律、闻思修和密宗修法等方面的诸多错误认识和谬论,以及民间崇拜日月星辰和动物祭祀等不符合甚至违背佛教教义理念和佛教道德标准的伤风败俗乏举,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指出这些大张旗鼓地盗用佛教名义的伪佛教法事活动、祭祀仪式和对佛陀教义的歪曲解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佛教的名声,而且对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对这类错误的修行和理解必须加以驳斥,以正视听。在相关部分,松巴堪布引用《萨迦格言》的诗句,以犀利的语气和充满哲理的思辨对背离和歪曲佛教教义的修行和观点做出如下评论:“没有父亲虽多子,不能列入家族中;如此无源之教法,佛法之内难相容”;⑫指出那些没有根据的修行犹如没有父亲的弃子不能名正言顺地加入一个家族一样,这些错误的观点和修行也不可能被称为佛教而被人们接受。松巴堪布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表述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正是借用了佛教的名义或者是把错误的说法跟佛教的教义搀杂在一起,鱼目混珠、蒙混过关。对于此类做法,他指出:“如在所食佳肴中,搀毒能令众人死,已知纯粹是毒物,部分人亦难伤害”。⑬松巴堪布的言下之意非常明确,毒物是不能够单独发生作用,倘若把毒物加入美味佳肴中,人们由于难以辨识而往往会断送性命,旨在指出藏族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种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大部分往往都以佛教为名或者是夹杂在佛教传统中而得以传播的,一针见血地总结出伪佛教或非佛教修行实践的发生学和传播学特点,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他还提及:“对所谓伏藏经函,及他处偷取教规,假如有国王之法,给予惩处最适合”。⑭亦即有些人企图利用来路不明的伏藏典籍来捍卫错误的修行、对于来路不明伏藏典籍和偷窃自他人的宗教教义者,如有王法应该予以惩治,显示出松巴堪布对佛教在当下社会的传播和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担忧。
《如意宝树史》对《萨迦格言》的大段引用还集中在藏地佛教史之“主尊上师宗喀巴传”和历任噶丹金座两个专题中。松巴堪布在讲述宗喀巴大师如何四处求学、开创善规、著书立说、利益佛教和众生的殊胜传记时,言及当时的大遍知博东乔列南杰和绒敦麻维僧格、俄尔哇衮噶桑布、阁吴热绛巴索南憎格以及达仓大译师西热仁钦等各教派藏族学者们对宗喀巴大师的思想和学说曾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当他们真实地领悟到大师的深广智慧和无量功德后,纷纷作诗称颂大师对佛陀教义的精湛认识,宗喀巴大师声名远播,引得四方智者顶礼称赞。在讲到这部分历史时,松巴堪布引用《萨迦格言》的经典诗句:“学者具德诸众生,不用招唤自汇集;具香鲜花虽然远,自有蜂群如云聚” ⑮,以及“大圣贤哲居住地,其它学者有谁敬:太阳照射天空时,行星虽多亦不见”。⑯以此来表达自身对宗喀巴大师的无上崇敬之心。对于其它学者就宗喀大师学说和思想的质疑和批判,松巴堪布继续引用《萨迦格言》的著名诗句诸如“没有知识的诸人,对智者尤为嗔恨”⑰“蹄印痕中水易满,无大智者易自满” ⑱“智者智解善言义,愚者却不这样做”等经典段落体现了对宗喀巴师徒继承、发扬和丰富佛教教义的伟业的仰慕之情,并深入浅出、生动灵活地揭露了一些对宗喀巴大师的思想持有异见的学者们的肤浅、粗俗和易于白满的本质。⑲
松巴堪布对《萨迦格言》的引用赋予了《萨迦格言》新的语境和诠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如意宝树史》作为一部生动形象、轻松诙谐而不乏严肃客观的历史巨著,以及松巴堪布作为一名个性鲜明.勇敢大胆而不乏缜密细腻的历史书写者和研究者的辉度。
三、余论
历史是无法被直接碰触到的,人们对过往历史的理解往往是建立在记忆和史料的基础之上。从某种角度讲,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的名言“历史是记忆的女儿”(History is a daughter of memory)“历史是基于史料的一种知识”(History is aknowledge through documents)的论断,都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家虽然是“我们共同记忆的保持者,”史料虽然也是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但记忆和史料本身则不等于历史,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认为历史学家对于记忆和史料的筛选、切割和重组决定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是充满断层的。因此,历史学家对不同文献史料的选择、运用和处理是历史知识得以发生的主要语境之一,反过来,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看法和把握也反映了其对历史本身的认知和态度。
作为一位把史料放在历史研究制高点的史学家,松巴堪布的三种史料观使得《如意宝树史》成为藏族近代新史学的典范之作。第一,对边缘史料和“无意的史料”的重视。传统史学的史料类型比较单一、范围也较狭窄,限制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史学表述。松巴堪布把处于边缘地位的非核心史料作为其史学写作的立足点,生动的口述材料和极具哲理性的文学格言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写作的形式和风格,使历史表述在个体经验和文学话语的作用下获得了新的生机。第二,对史料批判的重视。传统的史学家在参考文献史料时,一般会全盘接纳和引用,不太重视对史料的订正考究。然而,松巴堪布不仅充分肯定史料工作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更坚持对史料高标准、严把关、细考证原则,成为其史学建树的主要特色。第三,对参考史料的重视。参考史料的多少决定了一部历史作品的纬度和可靠度。在史料工作方面,松巴堪布延续了《贤者喜宴》的作者巴沃·祖拉臣哇和《红史》作者蔡巴·贡嘎多杰的史学传统,参考了大量的史料。根据笔者的统计,这部巨著参考了250部文献,而实际参考文献量在250部以上,仅从引文数量和参考文献数目而言,《如意宝树史》堪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史学巨著,是史料工作最为细致、史学批判最为深刻、史学表述最为生动的藏文史著之一。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与史料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对所使用史料的存疑批判、甄别鉴定、解读考证处处反映出松巴堪布认为史料工作是一切史学研究之核心的基本看法,也是松巴堪布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最根本的问题上给当时的史学界和后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
参考文献:
[1]S.C.Das.The Life of Sumpa Khanpo, also .styled Yeshe Dpalhbyor[M]. the Author of the Rehumig(Chronological Table).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58, 1889, pp.37-84.
[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8.
[3]伏尔泰.论历史:对新闻工作者的劝告[A]//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C].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79~80.
[4]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松巴佛教史[M].蒲文成,才让,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507.528;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933.973.
注释:
①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额尔敦白音的《松巴堪布诗学研究》(2004年);杨和缙的《松巴堪布及其所著之青海记》(1979年);德·孟克巴特尔的《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尔及其著作》(1991年);昂青才旦的《松巴·益西班觉生平及其学术成就考证》(2008)和当增扎西的《18世纪造像量度文献佛像、佛经、佛塔量度经注疏花鬟与作者松巴益西班觉》(2015年)等。
②长尾雅人根据内蒙古所藏松巴堪布文集目录详细介绍了松巴堪布文集的情况(1947年);Jan Willem de Jong的论文(1967年)综述了研究现状,比较了四种文集目录之间的异同:印度学者Lokesh Chandra根据木刻板整理出版了9卷本松巴堪布文集:R.E.Pubayev的两篇论文(1981年,1981年)论述了松巴堪布佛教史《如意宝树史》及其所载《佛历表》相关问题;Matthew Kapstein的两篇论文(1989年,2011年)考察了松巴堪布有关藏传佛教经典真伪问题的主张:SolomonCJeorge Fitzherber (2009)探讨了松巴堪布对格萨尔的根本看法;HanungKim的博士论文Renaissance Man from Amdo: Lifeand Scholarship of the 18th Century Amdo scholar Sumpa Khanpo (2018年),从“安多复兴”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松巴堪布的生平学术,论述了松巴堪布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是英语世界有关松巴堪布最详细的研究。
③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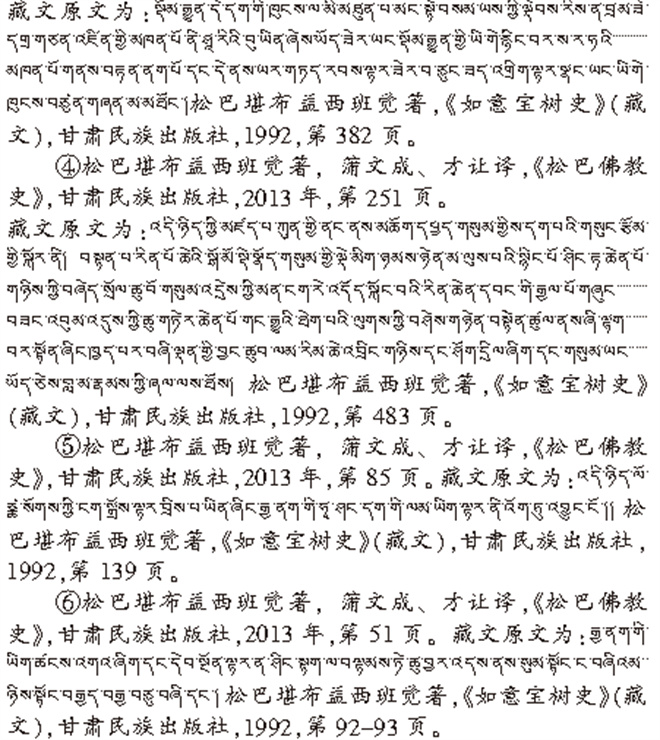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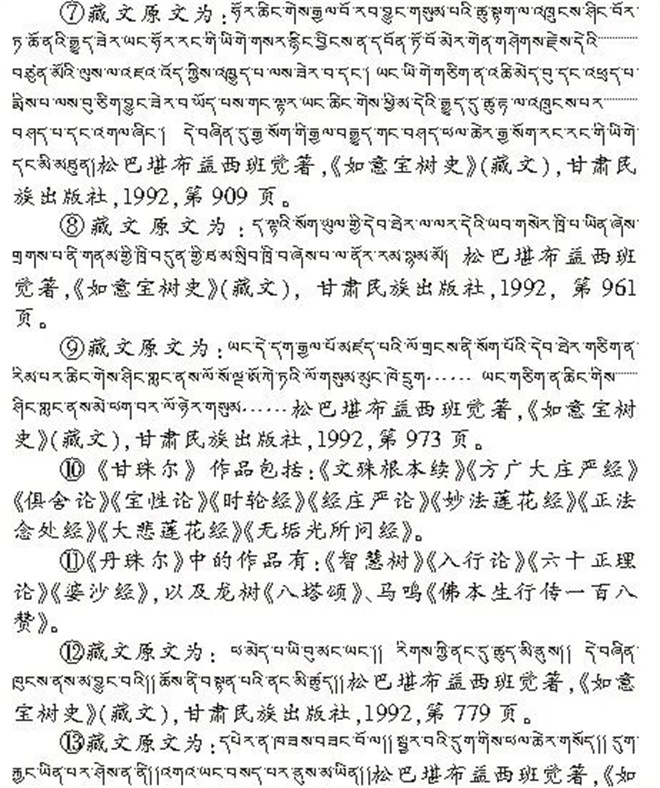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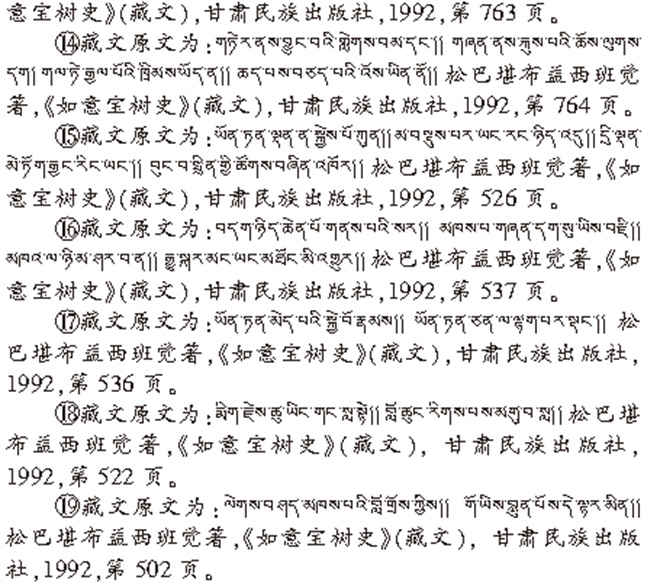
作者简介:德格吉,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清代藏族史、史学思想史研究。
原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9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