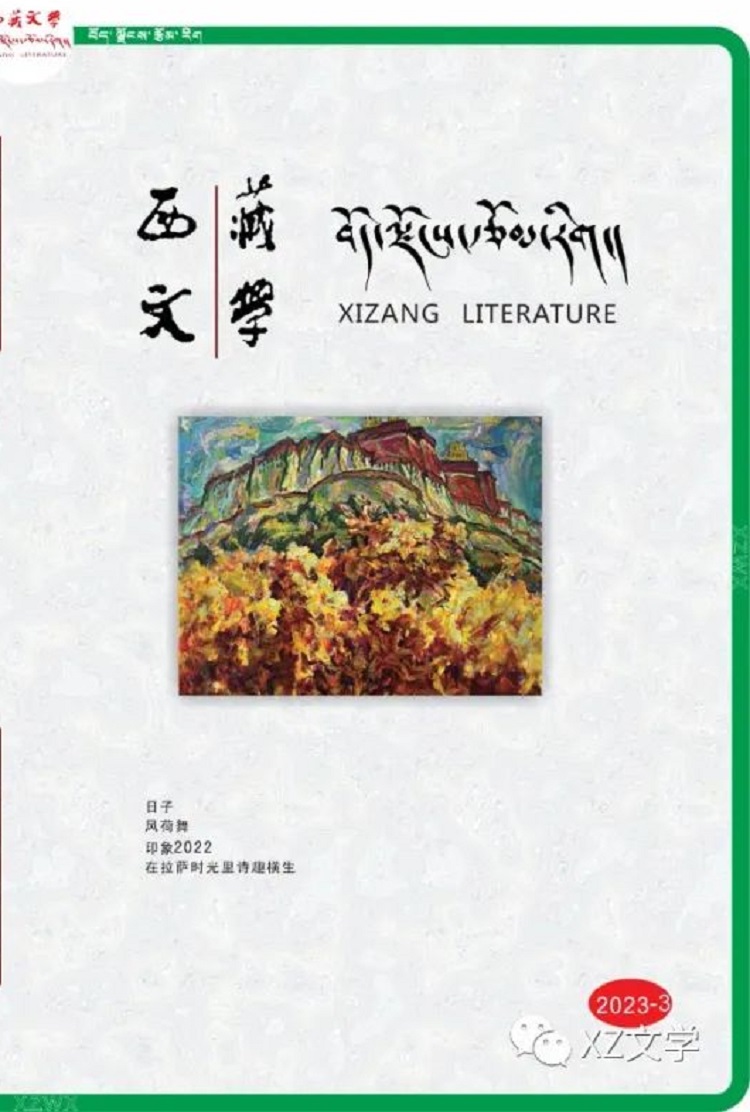
【摘 要】纳穆卓玛的诗歌给读者一股难得的安静,诗中着力建构的“拉萨形象”、趣味人生”、“日常经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热泪中安顿我最终的不安”。在她的诗歌中,现实拉萨得到审美“再现”,拉萨成为记录人们美好生活、体悟世界真如妙理、安抚现代焦躁灵魂的多向度文化载体。纳穆卓玛的诗,总能感受到她一方面感受热爱的现世生活的乐趣,一方面积极从这些世俗乐趣中肯定生存的意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纳穆卓玛的诗歌,没有掉入“日常生活”的幽暗陷阱,给读者一种澄明敞亮的感觉。
【关键词】纳穆卓玛,《半个月亮》,拉萨形象,诗趣人生,日常生活
《半个月亮》是藏族女诗人纳穆卓玛于2021年8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总共选入了诗人近些年来创作的149首诗。诗集《半个月亮》呈现了一座城、一个女人,以及女人在城里的日常生活。处在纷纷扰扰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能真正置身于各种繁杂琐事之外,但纳穆卓玛的诗歌却给读者一股难得的安静,诗中着力建构的“拉萨形象”、趣味人生”、“日常经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热泪中安顿我最终的不安(《时间》《香格里拉》2021年春季号)”。[1]
把纳穆卓玛诗歌的主题设置、审美趣味、艺术特点纳入整个中国新诗范畴考察,也是可圈可点的。纳穆卓玛的诗歌和拉萨文化关联密切。无论是题材、审美,还是艺术特点都体现出了拉萨城的深刻和独特。所以说,纳穆卓玛的诗歌在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方面有它的实验意义。同时,纳穆卓玛的诗歌并非对拉萨城简单的咏叹或是在拉萨日常中获得片刻的顿悟,而是出于“安顿灵魂”的创作目的,和拉萨万物同行,因此具有很强的美学批判性。
一、诗情画意的圣城拉萨
纳穆卓玛长期生活在圣城拉萨。她对养育她的拉萨城饱有极大的深情。她把她对拉萨城的所感、所思、所忆、所见全部压缩到了拉萨形象中,在诗歌中建构出了一个具有丰厚审美蕴藉的拉萨空间形象序列。在她的诗歌中,现实拉萨得到审美“再现”。拉萨成为记录人们美好生活、体悟世界真如妙理、安抚现代焦躁灵魂的多向度文化载体。
首先,纳穆卓玛诗中的拉萨是一个温暖甜蜜而值得爱恋的城市。“在清晨灿烂的窗前,会听到小鸟的歌”,生活在期间的诗人满心欢喜,因为“遇见的就是/冬天最美的阳光(《拉萨 遇见最美的阳光》)。”现实中的拉萨有“阳光之城”的美喻。拉萨河谷较为温和的气候,一年四季大多数日的灿烂阳光,布满城市街道的粗大古柳、历史遗迹,以及围着桑烟袅袅、佛号声声的寺院转经的信众,这些使得拉萨城成为众多现代人趋之若鹜的一座圣城。因此,纳穆卓玛确信,拉萨城的第一场春雨“都有一个非凡的使命/——缝合万物间所有的裂缝(《拉萨夜雨》)。”在诗人眼中,拉萨的一切都值得去爱,“我把一面湖水爱过/林间小路爱过/山坡上野花也爱过(《在秋天的门口撞见花海》)。”
纳穆卓玛对拉萨万物的“爱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进入到了一种想象中的精神空间,这是在佛教文化的滋养下形成的虚拟空间,蕴含着诗人的超验意识和生命超越。[2]佛教认为万物是“色空”,因此痴迷万物是“贪嗔”。佛教提倡的爱是大爱,是一种慈悲为怀。在纳穆卓玛的诗中,对拉萨城的热爱仅仅是“爱恋”的第一个维度,更多的诗人的爱是在拉萨日常中领悟众生平等、佛性平等。例如,在诗歌《坠落》中,诗人写道:“爱,是没有住处的/一个人。”又如,在诗歌《野花》中,诗人这样说:“每次深入大自然/我越来越偏爱于野花/ 那些一尘不染的面孔//如果你经过它们/如果你也喜欢/不必采下来/成为饰物或药料/只需用风的口吻/向它们表达最深切的致意。”诗歌《野花记》中对“野花”的想象更是妙不可言,“它们把果实和种子献出来/慰藉两首空空的大地时/她也会从中领走一片宁静/布施给自己空的地方。”《野花记》中所塑造的空间已经与现实中野花没有直接关系了,完全是主体一种具有佛教色彩的修行体验,是一种高度心灵化的空间。“野花”和“大地”平等修行,互相布施,互相慰藉,你帮助了我,我成全了你。正是基于佛教的这种认识,让纳穆卓玛的两个在新诗中常见的意象“野花”和“大地”获得了重生。
其次,纳穆卓玛诗中的拉萨是一个能让人静心体验美好生活和能够安顿人们灵魂的城市。无论在滚滚红尘中多么焦躁的人,面对圣城拉萨,也会“伸手向空,放下对峙 痉挛/……/看河流缓慢/看河流奔进夜色(《走进拉萨河边的黄昏》)。”拉萨不仅可以让人体验到岁月时光的美好,也可以对人的灵魂进行“安顿”。书写“死亡意识”是现代诗歌的一个标识。纳穆卓玛的诗歌也勇于面对这一话题。诗歌《在天葬台》没有忌讳藏族独特的丧葬仪式,书写了在仪式中人们从质疑到超越的体验,最终从仪式中获得了对“死亡恐惧”的拯救。这首诗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展示了拉萨这座城市可以包容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虽说书写死亡意识是新诗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一直以来,新诗中的死亡书写普遍让人感到绝望和痛苦。比如闻一多的诗《夜歌》,让人毛骨悚然;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人伤感不已。客观地说,从五四时期新诗诞生之初至今,新诗一直未能解决好“人的死亡问题”,这或许也是新诗不断丢失读者群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深入本民族文化中的死亡观念,拨开现代文明的重重迷雾,重返颇具原始味道的死亡仪式,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对死亡的超越和达观。例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一系列涉及死亡意识的诗,就从彝族火的仪式中消除了对死的恐惧。善良、宽容的纳穆卓玛在生活中乐观积极,自然在她诗作的表层少有对死亡的直接关注,但作为一名喜欢思考的诗人,她又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比如她在诗歌《天葬台》中写道:“万物混沌/你漂浮如尘埃/无法确定秃鹫给你带来了什么/又会带走什么/……”,就写出了诗人对“死亡”的某种恐惧,但正是在这“天葬”的仪式过程中,诗人突然领悟到“巨型翅膀再次盘旋上升时/风也有了神性/在世俗无法抵达的高处”,从而达到了对“死亡”坦然的态度。
第三,纳穆卓玛笔下的拉萨历史绵长,故事富有,和人的生命经验融为一体。 “它把记忆剪成一缕青烟/或随清芬的花瓣颤抖/或在一叶飘零是流浪(《拉萨时光》)。”拉萨城随处可见“阳光”、“烟火”、“风铃声”和“古树”, 这些“千年交错的光影”“覆盖着”人们(《八廓街的晨光栖息在时间的窗棂上》)。正是如此,长期生活在拉萨的诗人总能体悟到世界的真如妙理。例如诗歌《悬浮如尘》,就道出了生活的某种真相。深受佛教“无常”思想影响的诗人,面对生活中的一次意外,就发出了如此的吁叹:“刚刚还在一朵金盏花里/阅读你的微笑,试着在鸟鸣中/领走一片光的人/徒然,被风声劫走。”是啊,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常,“只剩下盛大的欢喜/如浮走的空/悬而未决(《悬浮如尘》)”。行走在千年佛文化积淀的拉萨,诗人自然面对这种“无常”,对“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首诗的妙处还在于把“空”作为一个意象进行了书写,丰富了“空”的意蕴,点出了“空”的历史感。在诗人看来,拉萨绵长的历史上,不知道有过多少这样的意外,留下了多少盛大的欢喜,而这些皆为“空”。 不少诗人在面对文物古迹的时候,不是膜拜不已,就是感慨往事,所以其诗歌很容易停留在浅吟低唱的层面而无法深入。纳穆卓玛则不然,她的诗把人的生命经验融进文物古迹中,仍然以探究生命的存在状态为核心。再看诗歌《站在废墟上》部分:“可你始终是时间垒砌的一面墙/风雨掏空的身体/除了旁人的各色声音/听不到回声//两首空空的我/只能站在乱石覆盖的虚无上/无所适从。”诗人的现代性很强,她很理性的对待废墟曾经的辉煌,合理运用佛教的“空无”观念来解释眼前的一切。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并没有陷入宗教的悲观和消极,而是利用佛教的义理,深入了对历史文明的思考,使自身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解放和自由。
总之,在诗集《半个月亮》中,现实中的拉萨和想象中的拉萨、物质的拉萨和审美的拉萨、生活的拉萨和理想的拉萨融合成一个诗性的空间。大量诗篇通过对拉萨空间本体的“本质直观”,将物质性的空间载体融合了诗人的强烈情感,完成了从审美话语到生命存在的探询和生命意义的追问。[3]这个空间,一方面表现了纳穆卓玛对故乡拉萨的无限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通过拉萨形象来对现代人不安的灵魂进行救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纳穆卓玛丰富了作为城市空间的拉萨审美形象,在新文学“文学与城市关系”史上有关拉萨部分,有其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二、趣味横生的诗意人生
强调审美趣味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但五四以来,由于反对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需要,文人诗的趣味遭到诟病不少。纳穆卓玛的诗有很浓烈的审美趣味,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纳穆卓玛的诗并没有掉入传统文人狭隘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文人趣味。阅读纳穆卓玛的诗,总能感受到她一方面感受热爱的现世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她也积极从这些世俗乐趣中肯定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只有在显现生成中才能具有其自身,这一生成不是本质的显现,而是通向未来的可能性之路,“此在”没有先天的本质,能再就是本地的所具有的可能性的存在,因此也是“此在'' 存在的本性。[4]具体来说,纳穆卓玛诗歌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趣味:
一是象趣。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纳穆卓玛的诗歌撷取的意象充满灵动之趣,生命之趣。纳穆卓玛诗歌意象虽大多在中国诗中经常出现,但纳穆卓玛总能或通过陌生语言,或使用陌生叙事,从而创出新意。比如月亮、森林、夜雨、春光、风等自然物象,纳穆卓玛对它们的精神都进行了重塑,完全不同于古诗中的意蕴和新诗中的象征。其次,是一种新颖的空间意象的建构。比如前一部分论述的“拉萨形象”。再看诗歌《桃花源》部分:“每一树桃花抱过的人间/都有相似的面孔/守林的奶奶说:/来年,繁华还会重生//此刻,浮云飘过我的天空/就此别过吧/有一朵,应该在前方/等着我经过。”意象“桃花源”完全不同于我们读者熟知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是引申义上理想主义的桃花源。纳穆卓玛的意象“桃花源”更多是一种哲理象征。“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5]这个桃花源虽建构在现实桃花林的基础上,但这确是诗人精神空间的某种释放。
二是形趣。次仁罗布指出,纳穆卓玛对诗歌表现形式孜孜探索。[6]很明显,纳穆卓玛的一些诗歌形式受到了藏族谚语、史诗格式的影响。比如诗歌《错高湖》中写道:“孤岛的背后是湖水/湖水未老去,可长满了皱纹//湖水的背后是森林/记忆在疯长,闪现鸟鸣//再背后是无序的群峰/站姿万千,皆有法相//再背后是来路不明的云朵/再背后是无处不在的空。”藏族谚语语言形象生动,喜用修辞手法,尤其是对比、顶针、比喻,句式整齐多样。[7]《错高湖》中大量使用了顶针手法,两句一节,因此读来非常上口。类似的还有诗歌《没有别的意思》:总共三节,每节最后一句都是“没有别的意思”;第一节第一句是“青石板反射的光”,第二节第一句是“榆树根下的净水”,第三节第一句是“湖水里的云朵”。也就是说,每节第一句都是偏正结构名词短语;每节的第二句都是由“没有”这个副词开头修饰的动词短句;每节的中间都有一句由副词“只想”开头的短句。诗歌《没有别的意思》在形式上的苦心营建使得诗歌和藏族谚语一样具有很强的音乐感。
三是理趣。藏族诗人的诗歌普遍具有“神性”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纳穆卓玛的诗歌也不例外,但她也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和呈现。首先,纳穆卓玛的理趣很多充满了生活乐趣,具有很强的烟火气息,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出家人似的禅思。比如诗歌《雪地上》:“被雪覆盖的万物/没有边界 没有分别/像一张无字的经卷/在风里流动//站在白茫茫里/我仍是攥在风里的一粒沙/不敢多迈出一步/生怕凌乱的脚印/最先带出泥水的伤痕。”这首诗意表达了人的渺小和卑微,呈现的是对大自然的尊崇。因为形象“我”的重度参与,使得诗歌贴近了人的生活。其次,佛教的精深使得纳穆卓玛的诗哲理精微,而不仅仅是顿悟。抓取刹那间的顿悟是中国理性抒情诗的普遍特征,但纳穆卓玛的短诗却并不尽然。藏族诗人的诗歌因为与佛教文化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们诗歌中的哲思往往能够体现一种深思或者是修行体验。例如诗歌《未来的日子》中的一节:“有一种疼痛/以分秒递减的趋势/从现实抽离 /它曾咬噬的部分/现在可以克制疯狂的眼泪/可以治愈隐疾反复无常。”“疼痛”本是我们世人都不喜欢遭遇的,但《未来日子》里去要我们正常面对“疼痛”,包括还有“枯枝”“琐碎”等,这些在我们世人眼中躲避不及的负面东西在佛教看来都是一种经历和劫,是在帮助世人的修行,因此不要纠结于“疼痛”。
四是情趣。狭窄意义上的诗趣一般就指情趣了。“抒情”是诗歌的固有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诗歌都是抒情的。纳穆卓玛诗歌的情感可以大致分为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几种。诗人在抒发这几种情感的时候,很少悲悲戚戚,而是展示出一种达观的生活兴趣。首先是以佛性视角看待世间万物,往往生发出一种超验的趣味。例如,诗人写《酿过青稞酒的陶罐》:“它们的体内收藏过青稞、雪水以及空气/直到酿出的酒歌,浇灌人间的情爱。”如果没有佛性平等的意识,绝难体验到“陶罐”的经验和价值。这几句诗的来源还不能归结为“禅趣”,也不同于内地诗人的“触物生怀”。遍观纳穆卓玛笔下的万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丰富的轨迹,甚至比人类更为高级。其次是从生活和自然中去观察细微之处,往往产生一种感动的趣味。例如,诗人会观察“一只云雀在院落的花枝上安家落户/这份小小的信赖,让我几次感动的要落泪(《幸福》)。”诗人看到“一只从远方回来的鸟/在抖落身上的雪/瞬间,细小的白,从羽翼上/继续落向更白的人间(《我从未听过鸟的悲鸣》)。”这是诗人对细节的关注,所以看到了花枝上的云雀、鸟身上抖落的雪,这些生活的细节给诗人带来了一种共鸣和共情。第三,是对颜色、气候、时空、感官的特别喜爱。在纳穆卓玛的诗中,表现颜色的常见词有:青烟、白发、绿叶、黑夜、青石、白茫茫等;表现气候的常见词有:春光、夜雨、春风、浮云、秋叶等等;表现感官的词也不少:柔软、疼痛、热泪、坚硬,总之,纳穆卓玛通过这些语词极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感受。
本部分开头提到纳穆卓玛的诗歌充满了各类趣味,绝少现代诗歌的苦涩之感。作家次仁罗布也发现了这个特点,并认为这是西藏诗歌的别样内涵。次仁罗布强调:“正因这种宽容、怜爱、敬畏、眷念等,少有颓废、喧嚣、讥讽等,这种精神气质使得西藏的诗歌葆有了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精神指向。”[8]笔者在认同这种说法的同时还要指出,虽然以纳穆卓玛的诗歌为代表的西藏诗歌少有“戾气”,但并不代表缺乏“审美的现代性”。第一部分以纳穆卓玛笔下的“拉萨形象”为例已经分析过,温馨甜蜜能够安顿现代人灵魂的“拉萨空间”,既是藏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也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味。
三、澄明敞亮的日常生活
有学者在讨论“日常生活”进入新诗的时候,认为:“时代之中的公共生活是敞开的、光明的,那么个人的日常生活更是封闭的、幽暗的。”[9]确实,以写“日常生活”获得盛名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反讽和戏谑解构现实社会,比如李亚伟的《中文系》,描述极其繁琐的大学中文系日常,抒发生活的无聊和意义的虚无。所以说,第三代诗人笔下的日常生活是幽暗的。但同样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纳穆卓玛的诗歌,却给读者一种澄明敞亮的感觉。例如诗歌《在小小人间》中,诗人的快乐“源于细小的事物”,“阳光源源不断地穿过玻璃送进来/兰草、清茶以及随意堆积的书/都投身其中,不悲不喜/你在阅读之外/找到了另一个光源”。诗人对日常生活关注如丝,蝴蝶、金盏、暗香,风、经幡等都是诗人关注的对象。诗人感受着这些对象,体验着这些对象,从而获得了生活中的无尽快乐。这些快乐是澄明敞亮的,不是低级感官的快乐,因为诗人平等地、认真地对待世间万物,通过与万物的一体“修行”,在万物的帮助下,打开了一个个“澄明的世界”,从而“诗意地栖居在了日常生活里”。如果仅仅把纳穆卓玛与第三代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同体验的原因归咎为城市生活的差异,这是违背事实的。除了口语诗歌的日常生活是幽暗的以外,2000年初创造了诗坛热点的女诗人赵丽华,她的诗歌也有很多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样也是幽暗颓废的。正是因为同样书写日常生活的纳穆卓玛的诗歌呈现出了与内地诗人诗歌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所以我们更要追问日常生活是否与“幽暗”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很显然,纳穆卓玛的诗歌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写日常生活同样可以澄明敞亮。
再请欣赏纳穆卓玛的诗歌《碎片》:雨水倒挂,缺口的金盏菊/堵不住偷袭的秋风//一片叶子走失后/草木收紧繁华的记忆/从深处拉开命定的距离//濒死的蝴蝶,翅膀下面/是无法安身的灰尘//黄昏脱落的影子/在空茫的山体里摇晃/溢出的,并非是融化的冰。通读诗集《半个月亮》,可以看出女诗人纳穆卓玛对日常中的自然之物非常喜欢,她的日常就是与自然之物相伴的日常,比如花草木、风雨雪等。拉萨城相对和缓的生活节奏、拉萨百姓对家宅之美的追求,以及对物质财富的相对淡薄,都使得诗人诗歌中的日常离不开自然之物。以佛性傍身的自然之物为重要元素在拉萨百姓生活中的无处不在,促使纳穆卓玛的日常书写容易形成 “澄明之境”,从而处在生活在乐趣之中。
出生于1960前后的第三代诗人他们诗歌的“西化”一直未为诗坛有效清算,甚至忽视。成长于文革、兴起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人在诗坛占据主流位置的时候,正是西方文化相较五四时期第二次高潮般涌入中国的时期。他们的诗歌在诗艺上有一定的成绩,但正是从口语诗开始,新诗开始大量的失去基层读者。究其原因,以西方文化养育的第三代诗人诗歌始终无法在中国土地上扎根,虽外形是参天大树,但营养不良,经不起疾风暴雨。而纳穆卓玛们的诗站在中国西藏文化大地上,扎根在传统文化滋养了上千年的藏地,他们的诗歌总有一个核心主张:“慈悲护生。”他们的创作目标是用同体大悲的感念知性对待一切生灵,培养出极其厚道的、仁爱的、报恩的、喜悦的精神品质。[10]
请再看纳穆卓玛的诗歌《1008个台阶上》:“拾阶而上,时间卸下了/你身上沾染的灰尘/抱一抱群峰抱过的虚无/端详草木跟青稞一样低头结出的籽粒/树木在秋风中脱衣/一片云躲在枝桠间虚度时光//在万物生长的宫殿里/你的微妙才显得如此珍贵/拾阶而下,比你更欢畅的/是那条奔走相告的河流/它一边向低处奔走,一边把/自己的露珠留在草尖上/给疲倦的鸟解渴。”这是一次走台阶的日常书写,就是这么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细节,但被诗人经验化了。诗人联系到了时间、草木、云朵、河流、露珠、鸟儿。诗人以一颗“慈悲之心”去反思自己,去感恩万物,从而照亮世界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
结 语
当然,纳穆卓玛的诗歌也有一些不足,这正是诗人以后创作可以努力的方向。比如对现实世俗生活的关注深度不够。这或许正如次仁罗布所说,这是西藏诗歌崇尚宽容、慈爱的品性所决定的。希望纳穆卓玛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拓展题材与主题,进一步丰富审美趣味,还可以重新致敬《诗经》,学习《诗经》中日常生活的展开。[11]“中国文化及其审美的情理结构是以此世人生为根基、为极限、生活的意义就在生活之中,就在自觉地享用这状似琐碎平凡却正是人生实在之中。”[12]再比如在形式与内容的整合上出现了一些伤痕。这恰恰说明诗人是一位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优秀诗人。新诗的形式问题本就比较棘手,纳穆卓玛引入谚语、史诗的形式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实验。
注释:文中所引用纳穆卓玛的诗歌如没有特别注明,均选自诗集《半个月亮》。
参考文献:
[1]纳穆卓玛.前世埋下的一粒种子[J].香格里拉.2021年春季号:96
[2]裴萱.空间美学的意义生成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建构[J].云南社会科学.2019(1)
[3]裴萱.空间美学的意义生成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建构[J].云南社会科学.2019(1)
[4]李革新.论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与此在的共属关系[J].学术月刊,2002(12):45-50.
[5]王佥崇. 存在主义与梁启超新民思想异同比较 [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6]次仁罗布.序言//纳穆卓玛.半个月亮[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8):2
[7]宁世群.藏族谚语散论[J],西藏研究:1990(2)
[8]次仁罗布.序言//纳穆卓玛.半个月亮[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8):1
[9]陈亮.一块蓝手绢也是意义重大的——梁小斌诗歌论[J].理论与创作:2009(1)
[10]参见刘元春.佛教论人与自然.佛学研究网:2021-1-25
[11]杨增艳.日常生活视野下诗歌的生命关怀意蕴探索——以《诗经∙卷耳》为例[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科学版).2020(5)
[12]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5-126
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2019年汉语言文学特色基础学科项目:新世纪西部诗歌的精神考察(2019HYKY03)
原刊于《西藏文学》2023年第三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王四四(1978-),甘肃陇西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现攻读西藏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新诗、民族文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