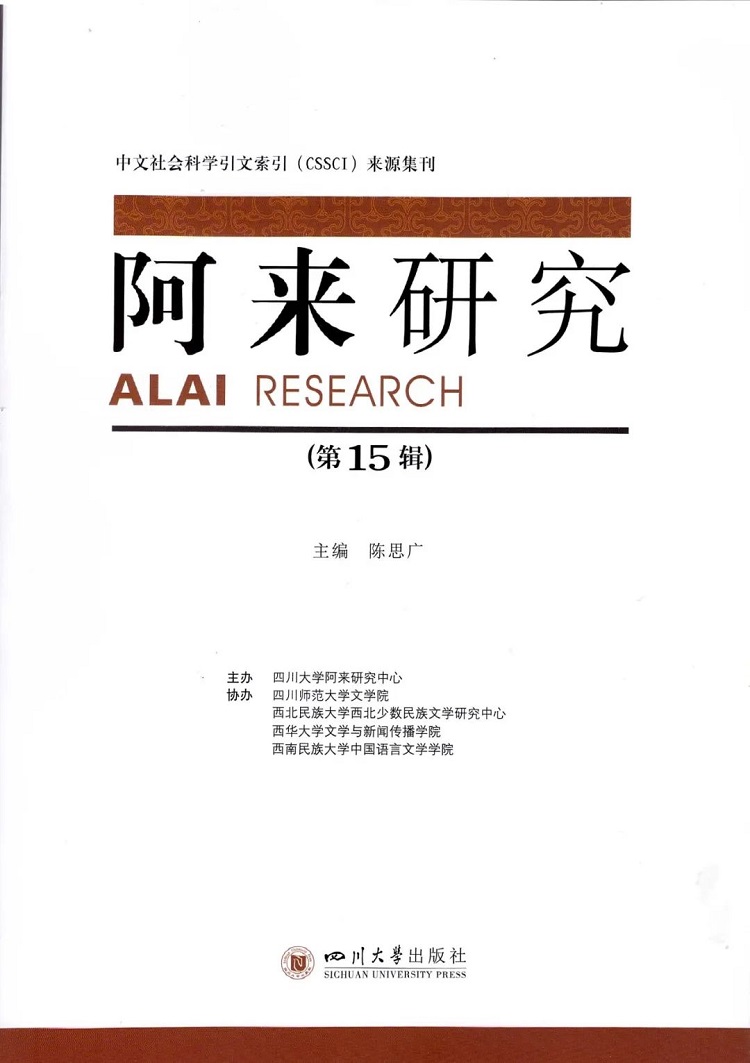
初读梅卓的这部名为《走马安多》的散文集,便面临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度,或者说是一种散文语境的阻隔:她的散文创作中有大量深奥的佛学术语和陌生的藏地方言。要消除这样的难度或阻隔,就必须详细参阅相关的专业工具书和文献史料,准确把握这些术语、方言的内涵及其在语用方面的相关规律。唯有如此,才能阅读流畅,才能充分领受到美文欣赏那份特有的愉悦,进而探知作家意欲在文本中倾诉的情感,隐藏的思想密码。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家在她的这部散文集里,无论是展示出的文学视野,还是表现出的思想蕴意,抑或是传递出的审美价值,又显得相对的单纯和易懂。正是在这种难与易相互交叠的阅读中,笔者能够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
顾名思义,这部散文集里的文学视线投向的是一个叫安多的地方,它不仅仅是幅员辽阔的青藏高原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更是涵容了藏族文化内涵和文明特质。按照作家本人在文中的准确解释:安多是指屹立在青藏高原中部的阿庆冈嘉雪山与东北部的多拉仁摩雪山之间的广大藏族地区。①一个知名的藏族作家,何以对这样一个地方有着如此深沉的情感眷恋?何以对这片大地有着如此执着的心灵向往?唯一的答案就是:这里是生她养她、成就她的故乡,这里是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地方,这里是藏族人民创造自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方。正是带着这份醇浓的情感眷恋和心灵向往,作家不惜以数万公里的艰难行程,踏遍了整个青海、西藏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甘肃西南部等广大藏族地区,以一个忠实信徒的虔诚来顶礼膜拜这里的自然山水与神性文化,以一个精神行者的内心来深刻感知这里的宗教文化和人文景观,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笔触来多姿多彩地抒写它们的丰厚内质和博大蕴含。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在《走马安多》这部散文集里所呈现出来的,既是对情感故乡与心灵故乡的深刻感知,又是对藏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领悟。
一
每一个人都必然具有自己生命的来处,这个生命的来处就是被人们普遍称为故乡的地方。故乡可以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充满人文意义的文化符号,这取决于人们的不同体认和价值判断。有些人一生一世都缱绻于故乡之中,有些人则为了生计和理想而离开故乡,这都是体认与判断的结果。尽管如此,无论是对于故乡自始至终的生命缱绻,还是对于故乡万水千山的别离,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镌刻着或浓或淡的故乡,随着岁月的不断冲洗,慢慢积淀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或心灵影像,令人无法忘却、终身铭记。也正是因为如此,故乡成为从古到今绵绵不绝的文学母题之一,被难以计数的文学家纵情抒写,作家写作故乡时表现出极其成熟的写作丰仪。置身于当下这个充满现代性意味的文学艺术时代,如何展开对故乡的审美抒写或艺术描绘,才能够凸显文学的拓展和审美的创新,且最终实现对故乡的本质意义的抵达?这既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也是一个审美精神的问题。梅卓在其散文创作时的坚定选择,就是恪守散文艺术的真实品格,以真切的感知与领悟来全力抒写和描绘一个真实的故乡。
从不同的散文视角出发,通过对众多生活事件、生活场景、生活细节的描述,着力表现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的藏族百姓自始至终所保有的对礼仪的尊崇、对善良的坚守、对信仰的忠实、对自然的呵护,及其中蕴含的人文之美和精神之美,这是作家散文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这部散文集的开篇之作,《在青海,在茫拉河上游》以散笔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个普通藏族牧民家庭在接待贵客时的真诚之心和礼仪行为。为了隆重欢迎孩子的老师,兰本加一家的大大小小都十分自觉地融入这场欢迎仪式:即将前往寺院接受信仰教育的长子牵着马到远处的山口恭迎老师;已经出嫁的大姐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赶回家里帮忙;叔叔加华医生同鲁仓寺的一位僧侣不辞辛劳,从远方前来;母亲果姆太进进出出,忙碌地为客人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吃用;一家之主、父亲兰本加端坐家中,一门心思地等候着贵客的光临。这样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绘,真可谓是人未到、情已暖。作家的描写并未就此停歇,而是以更加深入、更显真实的笔触展现主人和牧区民众对客人的热情款待。当又一个晨曦降临在茫多草原上,主妇果姆太一大早就为客人呈上了特制的油饼和新鲜的奶茶、精耙,她要让客人感受到一个女主人的殷殷之情;早餐后,男主人兰本加牢牢地盯住羊群中那只最肥硕的羊,他要用最鲜美的食物来招待这位珍贵的客人;长子作为学生则是带着老师,赶着牛羊,迎着灿烂的阳光,慢慢地走向一望无垠的茫多草原,他要让老师充分享受草原的宁静之美、辽阔之美和生态之美。在客人极为短暂的逗留期间,一些牧民纷纷前来探望,既是为了一睹客人的尊容,也是为了给兰本加一家以真心的祝福;当客人即将离别的时候,几个青葱少年主动放弃了那天的牧羊任务,他们围绕着客人蹦蹦跳跳地嬉闹,然后以一曲宛如天籁的童稚之歌为客人送行。这一连串细腻而深入的描绘可以说完整地表现了一个藏族牧民家庭对尊贵客人发自内心的热情接待。
除了主要叙写兰本加一家的友善待客外,作家还用一些看似随意的闲笔,勾勒了茫拉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其中既有对给格拉姆本松神山由来的解释、卡约文化遗址的发现、鲁仓寺创立的叙说,也有对孩子们在草原上自由放牧、拾干牛粪、扔掉废电池等眼前细节的刻画,还描绘了兰本加在祭祀山神时的庄重表情、给耗牛剪毛的小心翼翼,果姆太操持家务时的辛勤,加华医生为村民免费诊疗和提供草药的情形,以及作家对自己生命感怀、生存领悟的真实表白。就作家本人的抒怀与参悟而论,我们可以视这篇散文为献给茫拉河、茫多草原乃至整个大自然的美丽颂词,同时文中的这些历史叙说、细节刻画、形象描绘似乎还隐含着别样的思想深蕴。或许,作家意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茫多草原上的牧民们之所以保持简朴的生活、单纯的思想、慈善的内心、笃诚的敬畏,正是因为这里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倘若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任何一位带着善意而来的客人,这里的人们都会献上最衷心的欢迎和最庄重的礼仪。
散文《孝的安多方式》以松更节这一地方风俗作为切入点,力图通过对其主要内容、活动过程、现场情境等的叙写,透视其中的孝道观念、敬老思想,表现故乡的藏族百姓质朴与真实的本性、单纯与善良的内心。从这篇散文的叙事内容看,它首先以对松更节之名的诠释起笔,然后逐一讲述松更节这一习俗的由来、流传的原因、主要目的和意义、举行的时间和地点、活动的主角和参与者、需要筹划和准备的各种繁杂事项等。这篇散文以松更节之前的准备工作和松更节当天的现场情形为重点。关于松更节之前的准备工作,作家为我们概略地讲述了这样一些事实:为了给自己的父亲过一个满意的松更节,已是一家之主的长子桑杰才旦早在一年之前就开始认真细致地谋划此事,并积极着手相关的准备工作;他几乎倾尽全家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购买了数千斤小麦、菜籽和大量的大米、酥油、水果、饮料,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准备好充足而丰盛的食物;他向所有的亲戚、贵宾、村民一一发出诚挚的邀请,期盼他们前来参加为自己父亲举办的松更节。关于松更节当天的现场情形,作家则为我们细致地描绘了这样的细节:这是金秋十月某一天的早晨,年过花甲的索南才让老人穿上干干净净的僵着藏装,他首先前往本村的保护神莫洪的神庙点燃了第一炉桑烟,然后才到玛尼堂安安心心地做今天的主角;松更节的大幕准时拉开,儿女们给父亲献上深深的感恩,来宾们也纷纷呈上各自的礼品和真诚祝福;在几十位僧侣一齐发出的诵经声中,所有人都慢慢沉浸于一日三餐的美食美味和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中,直到夜色悄然降临,这场活动才得以完美谢幕。可以说正是作家的这种叙事重点选择,既突出了松更节活动特有的地方文化内涵及民间意义、传统价值,又凸显了藏族百姓充满仪式感的孝道观念和尽孝方式。不但如此,作家还在文末写了一个对话细节:在索南才让老人看来,儿女们为他做了松更节,其实就是为自己修好了“来世之路”,使自己不仅不会误入歧途,更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细节进一步拓展了散文的思想内蕴。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作家对题材开掘的深度不够,在叙事内涵、场景描绘、人物刻画等方面又显得过于简略,情感注入明显不足,致使本文的思想表达缺少丰厚而深邃的蕴含。
如果说上述两篇散文是以外视角来抒写广义的故乡,那么《伊扎三题》和《故土群山》则是以内视角来抒写狭义的故乡。这个狭义的故乡是对祖先、父辈、血缘、家族等亲情联系的深刻指认,它自始至终都悄无声息地在作家的血液里流淌,所以这两篇散文无论是用情用心力度,还是思想深度,都是之前两篇散文所无法比拟的。《伊扎三题》分三个小标题,着力书写了作家在重返故乡的亲历亲见、深沉感怀和所思所想。“香达玛尼堂”主要写在“我”抵达故乡后,曾经的少年玩伴、现已是花甲之年的阿妮龙毛吉接待了“我”,“我”随其引导游览了这座深居于故乡土地、供奉着巨大玛尼经筒的玛尼佛堂。在作家情感摇曳的笔下,玛尼佛堂的建筑格局、内外装饰、佛像供奉及其历史沿革和周围环境等便一一呈现出来。既然是对狭义故乡的书写,作家又为何把玛尼佛堂作为三题之首呢?因为它是“我”的祖祖辈辈悟得佛心、参明佛义的地方,因为在它那里能够依稀看见祖先的影子、父辈的足迹。在作家的内心感知中,玛尼佛堂已经不只是物态的建筑,而是血脉、家族、亲人融合的化身,或者说是两者高度统一的结合体。这与其说是作家的一种爱屋及乌的心理表现,不如说是她对亲人爱之深切的情感传递。“香伊柏老屋”主要从童年记忆、青年记忆、中年记忆,抑或说作家以对自己三次返乡的不同体验,来写故乡的老屋。在作家的童年记忆里,老屋不过是伫立在香伊柏村中的几间陈旧的房子;在作家的青年记忆里,老屋依然只是祖辈、父辈曾经住过的房子。笔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对童年、青年返乡时的记述里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老屋。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作家的创作策略。当作家第三次回到故乡,以一个成熟中年人的目光重新进行审视时,老屋所承载的两百多年历史和五代家族亲情竟然是如此的深沉而厚重,不仅令她充满深深感怀和无限想象,而且驱使她拿起手中的笔奋力书写。可以说,作家有机地融入了这三种记忆的不同体验与认知,既写出了老屋对于整个家族而言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也充分表达了作家对老屋的深沉情感。相比较而言,“故乡情结”则主要是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方法来写故乡,虽然其中不乏对幸福场面、温馨事件、甜蜜细节的生动描绘,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作家深厚的故乡情结,但从总体看,它没有突出的叙述重点,在艺术上表现出碎片化的意味,在抒情写意方面流露出些许浮泛与轻浅。
如果仅仅从散文的标题看,我们会以为《故土群山》是作家在对故乡群山之美的抒写。实则不然,作家是在写自己家族的历史,写自己的父亲,甚至可以说是在给自己的家族立传。就此而言,这篇散文有如关于家族、父亲的纪实小传。这篇散文从伊扎部落的诞生起笔,首先对家族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作家按时间顺序展开梳理,从最早的太太祖父智华开始,到太祖父多吉,再到祖父仁青本,最后是父亲宦爵才郎,既对祖辈婚姻生活、子嗣生育、血统融入等有详细交代,也对家族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经济状况等做了简略说明,几乎完整地呈现了整个家族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传承脉络。然后作者对父亲的身世和父亲15岁之前的生活等进行更为详细的叙述。这不仅是叙事重点,也是作家抒情之所在。因为祖父仁青本的过早离世,高祖父和太祖父、太祖母又在几年之中先后离去,父亲年幼时身边就只剩下高太祖母和祖母两位亲人。父亲的曲折人生也由此开启。父亲曾做过小沙弥、小乞丐,也有过在外漂泊的酸甜苦辣,更备受饥饿与穷困的煎熬,尽管如此,父亲从未放弃过勤奋而努力的学习,最终彻底改变了人生。显而易见,作家意在凸显青少年时代的父亲自立自强的决心和毅力。在作家的心理与情感、认知与判断中,父亲已经不单单是亲情的指称和象征,而已俨然成为永远的精神榜样。这篇散文的叙事的确展现出了较高程度的真实性,完全不像有些作家在写作这类题材时那样极尽夸张和炫耀之能事;这篇散文的情感表达无疑是强烈的,抒发了作家最为真挚而深沉的情感。
二
无论是基于地理知识的间接把握,还是源自身体力行的直接感知,我们都知晓青藏高原是中国面积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面对这座雄伟而又神秘的高原,中国作家一直没有停歇过对它的文学书写,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对它的书写可谓达到了高潮,不仅涌现出一些优秀作家,而且创作出不少堪称精华的作品。单就其中的散文创作而言,深情讴歌青藏高原的壮美山河,深层抒写青藏高原的历史文化,深入表现青藏高原的宗教信仰,无疑是最主要的三个题材。梅卓的这部散文集正是对这三个题材的延伸与深化。这种延伸与深化主要是指作家对历史、文化的艺术表达更抵近它们的内层本质,这正是这部散文集的显著特点之一。
大凡阅读过这部散文集的读者,都有着这样一些非常明显的感知或体验:从题材构成看,辑录于这部散文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皆是对藏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深入开掘和深层抒写,其间注入了更加丰富、更显新意的历史场景、现实画面、文化意味和主体性认知;从文本形式看,虽然每一篇散文都有各自的侧重,或是对历史文化的表达,或是对宗教信仰的传递,但将二者结合成文本形式,却是整部散文集最主要的写作特点;从创作心理和情感看,作家之所以会不厌其烦地对这两类题材进行抒写,正因为对它们具有深刻的心理感知和深沉的情感关注。这种创作心理和情感固然与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紧密关联,但更源于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高度重视。在这部散文集的后记里,作家这样写道:“我出生并生长在高原。群山之中,最美的莫过于万里长云蓝天,青翠苍茫草原,红墙金顶的寺院群落,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这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平和,时时刻刻警示并安慰着我,这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土地。”②这些话语,莫不是对创作心理和情感的阐明。为了更全面而深入地探知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化,作家行程迢遥,不惧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游历了不少遐迩闻名的历史古迹,探访了许多蜚声中外的寺院和宫殿,也拜谒过佛学大师、活佛的诞生之地,仰视过巍峨屹立的神山。每每面对历史古迹、文化遗址时,无论是看到它们业已显露出的落寞景象,还是看到它们依然夺目的辉煌容光,作家都始终有庄重的仪式感,全身心沉浸其中。每每从旅途归来,作家又费尽心思地去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之进行的详细阅读和深入分析,获取更加充实的理性把握。正是在充分的现场情境体验、文献资料研读及两者高度融合的基础上,作家展开了对藏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层抒写。
就对藏族历史的抒写而言,散文《古地三叹》和《洁白的仙鹤永在飞翔》,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作为一篇游记性散文,《古地三叹》分三个小标题,分别对普兰、门士、古格这三个“古地”的不同历史进行描述,揭示了它们在藏族历史、宗教文明、文化传承中的特殊价值。在作家看来,普兰之古在于它拥有玛旁雍措圣湖和冈仁波切神山这两个流传千古的著名圣地。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这两个圣地,作家对古代传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些古代传说都是在藏地民间广为盛行、影响深远的神话故事。正是这些神话故事,不仅再现了玛旁雍措湖泊和冈仁波切雪山的亘古缘起、历史演绎及其人格化象征意义的演进生成,而且显示出一个共同的审美指向:至善至美。两者的区别在于:玛旁雍措被人格化为圣女,并成为冈仁波切的仙妻;冈仁波切则化身为威武英俊的男神。显而易见,作家所写的普兰之古,既是对历史之古的一种确指,也蕴含史前史之意向。作家也用简练的笔法叙写了普兰的著名寺院——香柏林寺,着重指出它是整个青藏高原唯一一座以赎罪之名建造的寺院,进一步丰富了普兰之古的内蕴。对于门士之古,主要是通过一个细节展现的。作家来门士的主要目的是探访古如甲寺这座苯教发源的寺院,借以获得直观感受和情感认知,令作家没有想到的是,她在此遇到了对苯教历史了如指掌的高人次成南杰先生。在交谈过程中,次成南杰不仅向作家历数了古象雄国诞生的历史,苯教始祖敦巴辛饶对苯教的创立与大力传播及其彪炳史册的伟大功业,还拿出珍藏的苯教历书作为有力佐证,非常明确地告诉作家:苯教的历史并非只有两千年,而是长达四万多年。对于次成南杰的这种说法,作家尽管半信半疑,但内心受到的冲击却是无可否认的,由此作家对苯教历史源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寻。正是这样的叙事凸显了门士之古的历史悠久和深沉蕴含。对于古格之古的抒写,则主要在于对古格王宫遗址和隐于其后的那段动荡历史的描述与感知。梅卓之于古格王宫遗址的描述并无独到的审美发现和新意,这样的描述早已出现在其他作家的散文里。但梅卓表达出的感知却殊为不同,她拂去历史的尘埃,看见昔日王宫的辉煌,看见精美的佛像和不凡的古格绘画艺术,看见许多无名者的创造,这展现出作家不同一般的历史意识。
如果说《古地三叹》主要是从历史事件、历史场景,或者文献记载、物态呈表的角度来写藏族历史,那么散文《洁白的仙鹤永在飞翔》则主要通过对人物的审美观照来写历史,突出人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形象阐发“所有历史都是人的历史”这一历史观。作家在文中叙写的人物绝非普通的黎民百姓,而是在藏族宗教文化发展进程中,在藏族僧俗民众的内心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宗教人物。这篇散文首先以抒情笔调、写意手法描绘了雪花纷飞的理塘的自然之美和圣洁之美,含蓄地交代了作家此行的动因:理塘曾诞生过多位著名的宗教人物,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宝地。接着,作家仍然分三个小标题,细致地描写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诞生地、五世嘉木样活佛丹贝坚赞的故居、理塘寺三个地点。既然是一篇以写人为主的游记性散文,作家便有目的地将写作重点放在对格桑嘉措、丹贝坚赞这两位活佛的事迹的讲述上。具体而言,“仁康古屋”重点描述了格桑嘉措充满神秘色彩的诞生过程、学习经文与悟道的过程、生活简朴与为人谦逊的作风,揭示了这位活佛深得全藏僧俗爱戴的根由。文中关于这位活佛诞生的细节,比如屋内的木柱上流淌着狮子的奶,屋外正下着有色的雨,远方的天空挂着一轮彩虹等,不仅再现了充满神性的历史场景,更增加了文本的审美内蕴。“嘉木样故居”的叙事重点有二:一是细述了丹贝坚赞在抗战期间不同凡响的伟大善举一一为了支持国民政府抗战,他捐献了足够买30架飞机的巨款;二是概述了这位活佛对拉卜楞寺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杰出贡献。“理塘寺”则既描绘了理塘寺这座著名的佛教寺院的恢宏气势,又通过与一位名叫加央洛洛的年轻僧人的简单谈话,表现了新一代僧侣正在成长、宗教文化事业后继有人的光明前景。这篇散文不仅表现了梅卓对著名宗教人物的无比景仰之情,更形象地刻画了“人”在宗教文化演进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位熟悉青藏高原历史、人文的人都知晓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在整个藏族文化的丰富构造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长期、稳定而深沉的宗教信仰。如何看待藏族地区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或精神现象,又如何对其进行恰当而准确的艺术表现,是每一位文艺家都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在价值观极其单一的时代,绝大多数文艺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认知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文艺家们的认知才趋于科学理性和客观公允,愈发感知到青藏高原宗教文化独树一帜的魅力。正是因为被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及其展示出的魅力深深吸引,当今的文艺家们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对之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审美表达。
梅卓对藏族文化的抒写首先是从对宗教文化的审美表达开始的,散文《朝圣者之旅》便是其中代表性篇章。在这篇散文里,作家以一个精神行者的审美直觉与切身感知描绘了她在前往拉萨的路途上目睹的几幅朝圣者的画面。在从波密前往林芝的路上,作家首先看到的是三位男性朝圣者,他们一步一叩首,然后将整个身躯匍匐在地上,再慢慢起身站直,以不断重复的这一系列动作向着圣地的方向坚定前行;从色齐拉山下来时,作家又看见了两位来自江达的二十多岁的朝圣女子,她们在朝圣的路上已经走了一月有余,因为要充分表达自己内心的虔诚,每天只能走6到8公里路;在经过林芝县后,作家再度看见由全家七口人组成的朝圣队伍,他们在路上已经走了整整两年时间;在经过加兴乡时,作家最后与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朝圣者队伍相遇,这些人一律是年轻男子,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不等。面对这样的朝圣画面,作家的内心可谓感触良多,所以她才会在文中情不自禁地写道:“阳光是那么好,阳光温暖着我们每个人,宗教的力量就像这温暖的阳光,给了藏人以无限的力量,转化为能量,阳光让万物生长,宗教给了万物以灵魂。”③在作家看来,信仰就是一个人的灵魂,信仰的力量就是温暖的阳光。作家之所以会表现出这种由衷的赞赏,固然与其深层文化心理及思想认同有深刻的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就是朝圣阵营中的一员。这在作家随后的文字中便能够得到很好的证实。行程进入拉萨,作家首先描绘的是她在大昭寺看见的给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上金的过程,接着,她马不停蹄地前往拉萨附近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进行探访;在从拉萨到萨迦县的行程中,她又先后探访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江孜的“十万佛塔”和萨迦县的萨迦寺。且不说作家在探访这些寺院时的情感和思想、感怀与景仰,即便是这一番不辞辛劳的长途跋涉,也足以说明她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朝圣者,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青藏高原的数百座著名寺院烂熟于心,对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历史能够耳熟能详,这无疑是作家“朝圣”的有力佐证。
与《朝圣者之旅》类似的散文还有《阿坝的方向》《清静世界》《嘉那玛尼石经城》等。《阿坝的方向》主要描写作家在川西北高原的游踪及感知、领悟。作家由甘南进入川西北高原,从若尔盖到松潘、九寨沟、茂县、黑水,再到红原、马尔康、壤塘,可谓是风尘仆仆,作家寻觅和拜访所经之处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由此不难看出,川西北高原之行旨在探寻青海之外的藏族地区的宗教文化。《清净世界》主要记述作家在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短暂游历。它着重描写了“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和四大著名神山之一的梅里雪山。这篇散文既有对松赞林寺、梅里雪山的直观描绘,也有对作家心理活动、情感体会、思想认知的主观表达。文中对某些精彩细节写得细腻生动,比如作家在看见梅里雪山时突然哽咽;又比如司机在开车时,虽然手握着方向盘,但他的脸却一直朝着梅里雪山的方向。《嘉那玛尼石经城》主要通过对“世间第一大玛尼堆”形成历史的记叙和对其独特文化价值的分析,极力表达作家的深刻感知和深沉领悟。在作家看来,这一块块玛尼石上刻着的六字真言,这座由二十多亿玛尼石组成的庞大石经城,不仅充分展现了藏族人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认知,而且非常形象地传递了藏民族对于生命哲理的深沉探寻。相比较而言,《活佛世家》和《蛇月法会与改加寺的尼姑们》这两篇散文则主要从现实出发,着力表现作家对“人”的现实关怀。前者详细讲述两代活佛——二世敦珠仁波切、三世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分别在佛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在宗教文化传播中的杰出贡献,表达了作家对于他们的崇敬和景仰之情。后者真实描绘一群现代尼姑的现实生存状态,表现了她们出于虔诚而接受的锤炼和磨砺。
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都不会是一种单一性的存在,而是在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基础上的多样化存在,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作为一个成熟的少数民族作家,梅卓自然深谙这样的道理,所以她的散文创作一方面是努力进入藏族文化的内层和深层,另一方面尽力拓展审美视野,由此表达藏族文化所具有的多样而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新年画卷》《当七月的彩云飘来》《当卡寺的女神节》《神山和神山之间》等便是这类散文。在这些散文里,既有对欢欢喜喜的新年、热闹非凡的赛马节和充满宗教意味的女神节等节日文化的概要介绍,也有对食品制作、卫生习俗、结婚礼仪、祭祀等传统文化风俗的细腻描绘,还有对服饰、歌舞及其仪式感、程式化等审美表达的具体呈现。作家力图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凸显藏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人文风情、精神图腾及隐于其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作家为了更深入地表达藏族文化的多样性及独特的魅力,做出种种尝试,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除此而外,作家还通过对藏族特有的某些知识及其内涵的介绍来表达别样深蕴的意义。比如,《新年画卷》一文对神舞法会僧侣着装要求进行了逐一说明,《嘉那玛尼石经城》一文对六字真言做了仔细诠释,《神山和神山之间》一文对神山的分类有详尽叙写。这些知识不仅揭示了藏族文化密码所具有的意义,也有助于读者,特别是汉族读者阅读和理解散文。
稍微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梅卓的这部散文集里,那种纯粹描写自然之美的作品非常少见,散文《天境祁连》可谓是其中唯一,即使如此,这篇散文在结尾处仍然又回到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中。作家何以表现出这样的遗漏?这的确有些令人费解。究其原因,或许与作家擅长的文学体裁有关,因为作家以小说、诗歌创作为主,小说的中心是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自然环境描写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诗歌创作则偏重对意象的凝练和情感的发抒。这也或许与作家的思想认知和创作观念有关。在梅卓看来,纯粹的自然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自然都是历史的、文化的自然,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然,或者说只有被赋予了人的意义的自然,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这在《神山和神山之间》一文,以及其他散文的某些小节,如“普兰:冈措圣地”“梅里雪山”等片段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在这些散文里,纯粹的自然要么成为艺术烘托,要么与人类的生活融为一体。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个可能,就是作家把写纯粹自然的散文都编入了其他散文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它无疑是这部散文集的一个缺失。对于散文读者而言,这种缺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读者的阅读范围;对于散文研究者而言,这种缺失令其无法感知到作家更丰富的创作才能。这是作家需要思量的问题。
三
中国一直享有散文大国的美誉,散文写作在中国源远流长,每个重要的社会历史时期或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都曾涌现过许多流芳千古的散文名家及堪称典范的散文精品,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又十分珍贵的散文创作遗产。这个遗产库里,无论是散文创作的具体实践,还是对散文艺术的经验总结,抑或是对散文美学的理论探寻,都系统而完整。一名当代作家应当如何继承这些散文创作遗产,同时充分展现当代散文的发展与创新?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究的问题。曾几何时,我们过分地推崇西方现代美学,走过了一段弯曲的创作道路,但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创作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方法的借鉴,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新里程从此开启。
从某种意义上讲,梅卓的散文创作正是这个新里程上的一道风景。她以一个精神行者的感知与领悟,充分展现出一个当代作家的善良,或者说她的散文是一种善良文本的艺术构建,这是梅卓散文最为突出的特点。笔者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从题材选择、内容抒写、审美对象上看,作家选择以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宗教题材为主,无论是已然过去的历史,还是正在进行的现实,抑或是宗教文化本身的发展历程,都不可能只是以“善”的单一面目呈现,而是充斥着林林总总的“恶”,但作家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其中“善”的极力推崇和高度认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倾向,作家才会在散文内容的抒写、审美对象的描绘上均表现出“善”的思想蕴含和精神指向。其次,从情感与内心的表达上看,无论是在旅程中遭逢不快之时,还是置身于佛教寺院的庄重氛围之中,抑或是在极目远眺神山神水的奇异景象之际,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要么是真诚的宽容与理解,要么是由衷的崇敬和景仰,要么是深沉的情感注视和内心领悟,从中不难看出,作家对亲历亲见的事件、情境、对象始终充满善意。最后,从散文的语言表达看,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作家对佛学术语的借用,同时又多用“纯正”“健硕”“优美”等词语,充分展现出语言的美与善。这是作家散文话语的基调。在这样的散文话语中,没有尖酸刻薄、明嘲暗讽、批判指责,展示出灵魂的高洁。综上,无论是题材的选择、内容的抒写、情感的表露,还是语言、语境,都证明了作家的散文创作是一种善良艺术的建构。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作家的这种散文抒写并不是完整意义的价值呈现,甚至还有可能是对假丑恶的掩饰和回避,但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作家的价值观,作家基于此价值观做出自己的审美表达。
无可否认,梅卓的散文创作也存在某些局限,或者说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是文学视野相对局限。立足于自己十分熟悉和感知深彻的生活,写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的确是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首选,因为它能够充分凸显文学的地方性特点,更是跻身世界文坛的重要标识。但我们毕竟置身于一个信息传播技术相当发达的时代,无论哪一个少数民族的作家,都不应该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学视野,而应当努力拓展自己的审美视域和写作范围。因此,既深深根植于藏族,又努力在藏族之外进行勘探,才是作家更好的创作选择。唯有如此,我们的散文创作才会具有更全面、更丰富、更深邃的思想蕴含和美学意义。其次,就作家的散文语言表达而论,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将汉语词汇和藏语音译词混合,这种话语表达方式的确能够充分标识其作为藏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能够给读者带来新颖别致的感受,但同时也会给散文的理解造成阻碍。作家既然采用汉语写作,那么就应当尽力减少藏语音译词,更多使用规范化、标准化的汉语词汇及语法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扩大审美接受的范围。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以接受为主的文学市场。
上述之说,不过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旨在深入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有益于作家更好地从事散文创作。这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若有不妥之处,敬请作家理解与海涵。
注释:
①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②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③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孔明玉,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影视艺术研究,先后在《文艺评论》《当代文坛》《四川戏剧》《中华文化论坛》《中外文化与文论》等期刊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

晓原,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