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闻悉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于昨日18时在北京去世,为了缅怀王尧先生,小编特意编辑转发此文,以期更多读者了解先生事迹。
“ 我一辈子跟西藏打交道,在藏区待了20多年,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带老伴去了西藏。她没有福分,高原反应太强烈,没怎么体验西藏的风土人情,就回北京了。”
“老伴是小学老师,一直在北京。长年来,我不是在西藏考证就是在国外研讨。藏学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我接触、进入西藏学领域,正是从学习藏语文开始的。”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话锋突然转到藏学,房间的气氛瞬间清畅。
从民间开始
大凡对藏学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知道王尧。因为涉及藏学研究的许多学术著作,都能看到他的大名。
王尧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初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研习藏语和藏文,在我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祖师于道泉教授指点下,投身于藏学研究。
“刚开始,我对西藏和西藏学一窍不通,胸中茫然无绪。只是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报考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
谈起往事,王尧头脑还十分清晰。他回忆道:“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感谢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教导我们。当时,我们作为中央民院第一批学习藏语的大学生,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云南迪庆藏族钟秀生先生和四川巴塘藏族格桑居勉先生作为助教,帮助于教授做辅导工作。那时,整天听到嘎、卡,噶、阿的拼读声,弥漫在北海公园的侧畔。不久,我们远离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
贡嘎寺是年轻的王尧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噶活佛是他们的老师。贡噶活佛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聪慧伶俐,博学多才,曾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他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噶活佛选用西藏哲理诗《萨迦格言》《佛陀本生纪》作为教材,让学生们逐篇通读精读,这是王尧初次接触藏文古典作品。后来,王尧将《萨迦格言》译为汉语,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后又结集出版,让内地读者了解到藏文韵文经典著作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初,王尧(左二)同于道泉教授(右二)在一起 (资料图片)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至今萦怀:“那段时光,既紧张又活跃。”他们到离寺几十里的玉龙榭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第一次直接了解了藏族的礼俗,热烈的场面,送亲迎亲各种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尤其是赞礼的人长长地诉说本地本族历史的赞词。刚刚入门的王尧还听不大懂,只能靠着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大概。
“美丽的姑娘啊,你就像个木头碗。”婚礼上的歌词让王尧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把姑娘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了解到,藏族每个人都有自带碗的习惯,而且都在藏袍里贴身揣着。“碗”是最私有和最亲密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知识给了王尧很大动力,他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了自己最早期的研究。
“最有收获的是1954年9月,有幸作为助手随贡噶上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协助藏学界一些大学者,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五部法律文件。”王尧回忆说,“那些大学者的风范和学识让我终身受益。”
王尧以《藏语的声调》一文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他说,在广阔的藏区,“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在所有的藏区都能通用,但文字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藏区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拉萨、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遵循于道泉和贡噶上师的教导,王尧一直努力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根据赵元任对《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王尧就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归纳,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
这一篇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小小的论文,受到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重视,并在《汉语史稿》第一分册中加以征引,使王尧倍感鼓励。
此后,王尧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究上。50多年过去了,他十余次深入藏区,访遍雪域高原的山川胜迹、古刹庙堂、农牧宅帐,这些经历让他的藏语毫无生涩的书卷气,著书立作却又渊博地道。
在藏学领域,王尧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对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起到了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王尧研究藏学六十余载,撰写了10余部专著、百余篇论文,主编多部藏学研究丛刊,在藏语的分期和方言的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译释、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轨迹、藏传佛教和藏汉佛学、藏族民间文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将吐蕃时期的三大藏文文献(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引入西藏古史研究,对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1985年,王尧与东噶活佛(右)在当时的西德慕尼黑 (资料图片)
王尧将自己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的结集视为“回馈社会、仰报师友”的一份文化使命。5卷本《王尧藏学研究文集》气魄宏伟,第一册《藏文碑刻录》、第二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三册《藏传佛教考述》、第四册《汉藏文化考述》、第五册《藏传佛教考述》。从对藏学一窍不通到授命学习,再到兴趣所在、潜心研究,最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五本沉甸甸的著作展开了王尧一个甲子的生命画卷。
“藏族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内容广博。我国的藏学研究有优势,但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另外,宗教学在我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在西藏,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不能够脱离宗教的啊。”86岁的王尧依然心系藏区。
成全读书人
王尧的父母不是读书人,家中三子,他是唯一的男孩,名字取做“尧”,寄托了父辈的希望。
北京图书馆是王尧的精神家园。1951年,他从南方到北京求学,住在北长街78号后院,旁边就是十世班禅大师在北京的办事处,许多藏族人士和家属在这里工作、生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王尧迈开了学习藏语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靠近北海,近水楼台,他几乎一有空闲就到北图去读书。
北京图书馆前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1917年在国子监南学旧址开馆。“在北京图书馆,我真正享受到了读书的快乐。那里真是书的海洋、书的宝库,过去许多想看而不可能看的书,都能在这里借到、看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住在安定门,离北图远了些,但一有机会就会来参加北图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比如,在李煜词的讨论会上,作为听众,我听到了郑振铎、冯雪峰、何其芳等一些大家的发言。特别是王仲闻先生,我只知道他是安定门邮局的工作人员,谁知道他竟是王国维先生的二公子。他的发言语惊四座,有很卓越的见解,令人叹服,经久难忘。”
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文革”期间,王尧作为“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下放劳动,不敢摸书,更谈不上读书。可是,他“贼心不死”,经常偷着藏着掖着读一点东西。比如,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于道泉给他的练习英文的读本)。
另外,王尧还把敦煌卷子藏文原文,抄成小卡片放在兜里,或在农田工作之闲,或在厨余饭后空档,掏出来琢磨琢磨。生活因为有书的存在,还是美好的、有希望的。
王尧时常记起年轻时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他认为袁枚说出了穷苦读书人的痛苦和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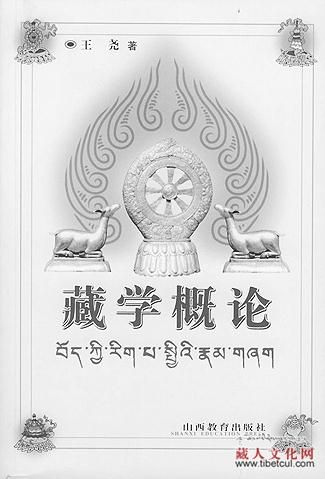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如今,公共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王尧特别欣慰:“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了100多年的血与火的锻炼,多少读书人、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发展。古今中外的知识传承,通过读书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公共图书馆这项公共设施,实在是非常伟大,成全了多少读书人,功德无量啊。袁枚先生地下有知,也可以另写一篇‘借书记’了。”
王尧爱书,但从不据为己有。前些年,儿子将他堆满房间的各类书籍拉到了一个寺庙存放,并将居所翻修一新,希望父母能在更好的居住环境下安度晚年。不想,失去书的生活,王尧很不开心。
这几年,王尧将自己大量的藏书,尤其是珍贵的外文藏学文献,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4年5月,王尧更是将130多包、各个版本的全套大藏经捐给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成全读书人,唯有这样处理自己的“宝贝”,才能如王尧所愿。
2011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捐书仪式,学校领导和藏学研究院师生代表80多人到会。王尧所赠图书共计500余卷(册),包括《西藏大藏经》(日本版)15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101卷,新纂大藏经《续藏经》52册,《大藏经》(法轮图标)110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4卷。
王尧在捐赠仪式上说,他非常同意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理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国学,就要研究包括汉学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中,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大家认真研究。
王尧以自己的经验告诫学生,研究藏族文化,非掌握藏族语言不可,语言是钥匙。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入手,才能把藏族文化学通学精。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大了,退出教学一线,但仍不忘老师之责,同学们如有藏学研究之疑,尽可来咨询。
记者再次拜访王尧已是初秋。问及生活与家庭情况,老先生三缄其口。但谈起藏学,谈起对他本人学术生涯有巨大帮助的人和事,则是滔滔不绝。
与大师结缘
藏区的长期生活,加上明师的点拨,成就了王尧丰富的藏地阅历和深厚的藏文修养。他师从贡噶上师、东噶活佛,多次为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担任翻译,同大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最重要的老师还是引他进藏学之门的于道泉教授。
从入校之始到耳提面命,王尧始终对于道泉怀有崇敬之情。在中央民院开办“藏文研究班”时,于道泉将从海外带回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巴考等人合编,巴黎出版)交给王尧学习。从此引起他对海外藏文文献研究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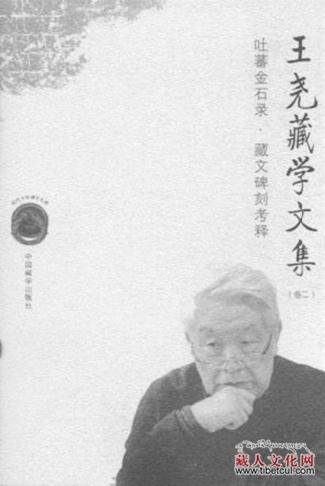
在于道泉的帮助下,王尧成为中国藏学界首开研究敦煌藏文卷子的学者之一,并获得丰硕成果。1983年,他受法国藏学家石泰安邀请访问巴黎,石安排他的助手陪同王尧多次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阅读敦煌写卷文书,尤其是反复阅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一核对卷号材料,“目验手批,逐字对读,发现我们初版所根据拉丁文转写,有若干阙漏、伪误和脱失,均将其一一订正”。
除了于道泉教授和贡噶上师,还有一位西藏活佛学者对王尧有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西藏著名的东噶·洛桑赤列教授。东噶是西藏东部林芝扎西曲林寺(东噶寺)第八世活佛,曾在西藏若干大寺庙和上密院学习,获得西藏最高佛学学位“格西拉让巴”,先后担任过中央民院及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出版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大辞典》《西藏目录学》等,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院开设“藏文研究班”,从西藏请来东噶讲学,王尧除了担任助教,还多次随东噶出席国际上的藏学研讨会。他评价东噶“是西藏最为通达的大师级权威”,“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
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初次见面是在1951年,时年13岁的十世班禅到中央民院做报告,5分钟的演讲,翻译用了半个小时才诠释清楚,王尧当时就在台下,藏汉语言交流如此困难,他如坐针毡。
时隔多年后,王尧的一个学生告诉他,扎什伦布寺的文物室有一幅古画,非常值得注意和保护。王尧前往查询后,认定是一幅唐代密宗的坛城图。后来,在北京,王尧对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谈到了这幅画,赵朴初向十世班禅提出借观的要求。班禅把那幅画提出来,郑重地交给了赵朴初并称:“这是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供养中国佛教协会的礼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历辈班禅大师”和“当代班禅大师”两个词条的编写由王尧负责,这加深了他与十世班禅的接触。在班禅大师佛邸的多次对话,他们已经完全能用汉语交谈了。
一次,十世班禅邀请王尧携眷一起到其佛邸吃饭,班禅接待热情,并亲自削苹果递给了王尧夫人。王尧夫人不好意思直接接下,王尧连忙提醒:“赶快接下,谢谢大师,连苹果皮也要接下,按藏族的规矩,这是添福增寿,以作纪念。”那次宴请,十世班禅还邀请王尧的父母一起用餐,这是藏族中尤其是活佛喇嘛中的最高礼仪。
1989年,国家决定在扎什伦布寺修建五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本来,十世班禅邀请王尧同行进藏,但他当时因有出国任务不能前往,谁知,这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王尧与高瓦喀寺的转世活佛曲杰建才的交情是从拉萨开始的。曲杰建才是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古建保护工程师,他对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以及三大寺的辉煌建筑研究颇深。
199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王尧和曲杰建才活佛重遇。曲杰建才《布达拉宫——古建的修复和整容》的演讲让他记忆深刻:“他把布达拉宫整修的全过程做了介绍,并从原始资料调查入手,彻底摸清了这一雄伟建筑的档案,近三百年来木结构的腐朽、颓坏,香火的熏习,鼠啮虫蛀,破损十分严重。整修过程有时要偷梁换柱、有时要托上换下……所有都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他的发言使国外关心西藏的人十分惊叹,而一些不协调的声音说我国在破坏藏文化,如何消灭藏文化等谣言就此不攻自破,成为笑料。”
“后来,他还邀请我去看他拍摄的‘贡噶上师的故居’,贡噶活佛在俗家中简单的陈设,朴素的藏民家庭环境,圈养着牛羊,焚烧着牛粪的茶炊,亲切的话语保持了藏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行,这一切令我肃然起敬。”回忆起与曲杰建才活佛的交往,王尧感叹,由于自己师从贡噶上师,贡噶上师与高瓦喀活佛曲杰建才是“金刚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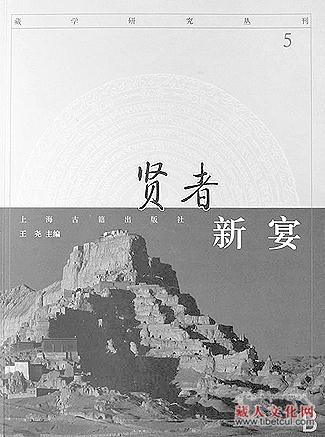
人才多出“王门”
陈庆英、沈卫荣、谢继胜、熊文彬、陈楠、储俊杰……这一串名字是当今中外藏学研究舞台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他们都师承王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最大快事。对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王尧曾经用周谷城的话劝导同行:“教学生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
王尧是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的穿针引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