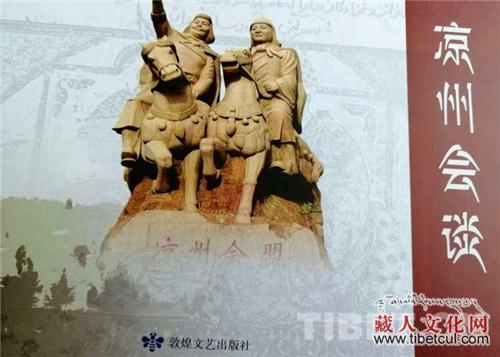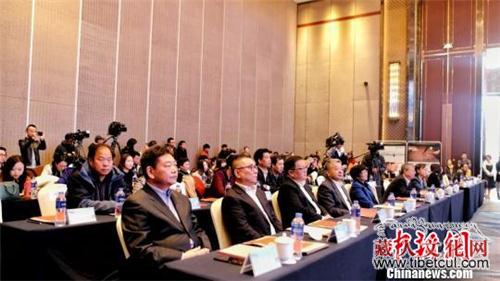白驹过隙,韶华易逝。虽然十个春秋过去了,但深受明清佛教造像艺术震憾的那个场景,却依然珠烁晶莹,鲜如当初。
那一天,当我虔诚地走进李巍金铜佛像展厅时,便有了置身旷世古刹的感觉。眼前藏香缭绕、佛光辉映,耳际梵呗飘渺、似远犹近。端祥数以百计的各类佛像,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款的金铜佛像,风格汉藏交融,外观雍容华贵,给人以不可名状的视觉冲击与绵想冥思。
在千姿百态的佛像中,佛祖诸像面庞方正,长耳垂肩,神态庄严,似在观照众生的福祉。菩萨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优雅,似在倾听信众的诉求。护法神像威猛英武,手执法器,目极大千,似在守护天国的净土。伎乐身态婀娜多姿,各俱丰采,让人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绚丽盛景。这些造像艺术中的东方瑰宝,以其古雅幽深的沉静和纤尘不染的光鲜,净化人的心灵,慰籍人的感情,使我们一行观瞻者久久驻足,流连忘返。
“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这批堪称国之瑰宝的金铜佛像初次面世,学界业界方家始则为之一惊,继则趋之若鹜,前往观瞻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大德高僧数以千计。从2007年起,季羡林、饶宗颐、冯其庸、王尧、谈锡永、步连生、孙国璋、金维诺等国学界、藏学界和佛教造像界的耄宿,对这批珍贵文物的考证和研究给予密切关注与具体指导,著名藏学家、佛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教授,著名佛教造像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王家鹏研究员,更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联手国内外资深学者,分别对这批藏品进行了文献考证和实物鉴定。青铜器文物鉴定专家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以及专程来华的美国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科学家皮特 梅尔斯博士,还分别用现代精密仪器分析了这批藏品的化学成份和成像年代。在这之前,故宫博物院罗文华副研究员捷足先登,于2004年年底,先后在成都、兰州和银川等地对这批文物中的数百件金铜佛像进行跟踪研究拍照,并对其中的上百尊写出了言之凿凿的鉴定结论。
近几年来,参与研究这批文物的专家学者苦心孤诣,通幽洞微,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对于佐证并拓展汉藏文化交融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同时也从一些侧面对蕴含其中的丰厚历史信息作出了耐人咀嚼的解读。
解读之一:永乐造像风格,贵在汉藏交融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虽几经兴废,仍在变革中发展。在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甚至生活习俗的同时,佛教造像也逐步淡化梵像风貌,展现出本土造像的神韵,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汲纳与包容。
藏传佛教造像、汉传佛教造像以及汉藏交融风格的佛教造像,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在吸收犍陀罗和印度佛教造像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造像,是佛教演变的精神载体,是人类智慧的文化遗存,更是汉藏历史交融的艺术结晶。
汉藏佛教文化交融源远流长,自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版图,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日趋深入。永乐时期的宫廷佛教造像,在继承元廷造像风格的基础上,从汉藏信众共同接纳的艺术形象着眼,把各美其美的汉藏造像元素有机融合,铸成了美美与共、汉藏交融的永乐金铜佛像。解读这一艺术瑰宝蕴含的历史信息,既有助于了解汉藏佛教交融的历史缘由,更有助于认清汉藏民族和谐的历史必然。
纵观我国近两千年的佛教造像史,永乐宫廷造像所具有的标程百代的地位是无以替代的。其时,在隶属于“御用监”的“佛作”中,技艺精湛的工匠在官吏的监督下,依据宫廷要求和藏传佛教定型的造像模式,融入内地传统的审美情趣、表现手法和工艺特点,按照严格的量度和仪轨统一制作佛像。由于选材用料考究,制作规范精细,600多年来永乐造像以神韵精美曼妙、仪态华丽端庄而独步中外;以造型匠心别具、风格兼容汉藏而冠绝古今。时至今日,美仑美奂的永乐宫廷金铜佛像,依然让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僧俗信众为之倾倒。
永乐造像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巧不可阶的工艺水平上,更体现在汉藏交融的造型特征上。这种亦藏亦汉的殊特造型,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蕴含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和谐的原始信息。是汉藏交融历史本真的艺术表现,展示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血脉共通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为我们研究西藏的发展史和明代的治藏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金铜见证与确凿无疑的人文标识。
明成祖朱棣是否诚信藏传佛教,《明史 西域传》谨以“兼崇其教”(指藏传佛教)一笔带过。治史诸家虽各有断,但因史料见绌,迄今尚无定论。不过出于政治目的,成祖以推崇藏传佛教为名,设法笼络藏僧上层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金铜佛像作为回赐入贡藏僧首领的贵重礼品,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造像元素精心整合,使之成为汉藏佛教信众都能认同的造像艺术,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翔实的史料探究形成这一艺术风格的具体过程,但成祖主导下的宗教理念和价值取向,无疑是永乐造像风格的基本依据。这是朱棣对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宝贵贡献。
解读之二:借重藏传佛教,旨在安疆固土
宗教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形式的宗教艺术,都是与其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背景紧密关联的。永乐造像亦不例外。这种造像的汉藏交融风格和流金溢彩身价,就是成祖借重藏传佛教,感化藏区僧众,增强藏民对大明王朝的国家认同,进而实现其安疆固土目的的治本之作。
为了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元朝皇室在西藏归顺元廷前后,就特别支持藏区势力最强的萨迦派发展。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更尊奉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加封其为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在元朝中央的推动下,喇嘛教在藏、蒙和汉族地区加快传播,其布法之广,教徒之众,影响之大,一度臻于极盛。鉴于喇嘛教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影响力,明初诸帝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怀柔远夷”策略,不但没有中断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而且继续沿袭元朝的政策,给喇嘛教以优渥礼遇。通过“仰僧善道”,“化愚俗,弭边患”,积极凝聚藏传佛教僧众对明朝皇权的向心力,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防止西藏上层因中央政府改朝换代而裂土自重,脱离大明一统。明廷的治藏政策,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方法,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制定和实施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永乐造像艺术独特风格的出现,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藏族群众全民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领袖在藏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争取藏区宗教上层人士为明中央政府所统辖,是治理西藏的根本途径。据此,明立国伊始即遣使入藏,告谕各个部族教派,明朝已经建国,并招谕元朝旧封官员入朝受职。洪武六年(1373),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入朝,被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60人悉数封授。次年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被尊为帝师。这几次重要封授,为喇嘛教接受明朝的管治奠定了基础。
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教更为重视,在改变独尊萨加派旧制的同时,对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政教首领均于敕封,共尊厚待,不断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喇嘛的直接联系,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制度安排和统治秩序。其主要政策举措是:
众封多建。永乐年间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其他僧官受封者不计其数。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分设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级别。为了保持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绝对统治权威,朝廷规定,法王以下各级僧官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敕书勘合”。要求三教领袖“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抚安一方”。
厚赏羁縻。明廷规定,凡三教受封为“国师”以上的僧俗官员,都有资格派代表进京朝贡,贡品自定。对入朝进贡的藏族官员,明政府给予优厚回赐,赐品价值往往数倍于贡品。由于各类佛像特别是金铜佛像乃佛门法身且价值昂贵,入贡者极为看重,夙夜欲得,朝廷亦作为极品礼物予以赏赐。明政府允许朝贡人员来往经商,有些受赐物品还在沿途出售。因为朝贡名利两收,藏区首领竞相前往,代代相效,随行人员也日渐增多,以至后来朝贡使团踵迹于途,络绎不绝,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数千人。鉴于入贡人数激增,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建置行政。元朝末年,随着萨迦派的衰落,藏区教派纷争迭起,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矛盾加剧,刀戈相加时有所见。这些乱象促使明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变通。从洪武时期起,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完善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把西藏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委任不同级别的官员,依据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不干预宗教事务;册封的五王为宗教领袖,直接隶属于中央,各王之间互不相辖。这些政策的实施,加强了藏区政教首领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关系,形成了藏族喇嘛和地方势力的权力制衡,使教派、部族互相牵制,平衡发展,保证了藏区的社会稳定与政令贯彻。
扶植新派。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起初虽影响不大,但内部戒律严肃,且创始人宗喀巴熟悉佛教重要经典,长于从事宗教社会活动,又与明廷建立了密切关系,格鲁派在藏区的声望与日俱增。永乐十二年(1414)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明廷即封授他为“大慈法王”。黄教势力后来日益扩大,是同明廷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褒奖格鲁派的举措,为西藏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其他教派整饬寺院、严格戒律、约束僧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修寺建庙。永乐时期,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多达十座以上,在京番僧均由朝廷供养,寺庙修缮亦由朝廷负担。不仅如此,朝廷还抽支重金,在藏区修建寺院。青海西宁瞿昙寺创建人三罗喇嘛因有功于明,成祖多次派出钦差监督扩建该寺,并于永乐十年(1412)封瞿昙寺班丹藏卜喇嘛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封素南坚参喇嘛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敕封的两位国师,由其后传弟子世代承袭。瞿昙寺不负皇恩,在明朝治理青海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祖的策略,使“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益寡”。藏区各地上层僧侣和俗官,协助朝廷抚化部族,劝善属民,社会秩序稳定,民族关系融洽,保证了西北、西南边疆的安全和巩固。定期朝贡与回赐的政策导向,还形成了藏区上层尊崇明朝中央政府的局面,增进了藏汉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监督和管控。据《明实录》记载,对于来往于内地的喇嘛,只要不参与政务活动,不传播淫晦之术,朝廷允许他们随意游历内地名山佛刹,驻锡安禅,授徒传教。许多藏僧久居内地弘法译经,有的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寺院道场。
“从封多建”、“厚赏羁縻”,使藏青甘川的地方权贵和僧侣集团受益匪浅,倾心内附的愿望更为强烈,成祖借重藏传佛教安疆固土的旨意如愿实现,但其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却未见增加。后来武宗阁臣梁诸论及个中缘由时说道:“西番之教(喇嘛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永乐、宣德)虽曾遣使,盖因天下初定,籍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佛也”。这大概是对成祖借重藏传佛教根本目的的最好诠释。
解读之三:误导臣民崇佛,意在巩固皇权
朱棣崇佛并非信佛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借助佛教的光环,为其篡嗣夺位制造“君权神授”、“顺应天意”的舆论,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强化皇权政治,实现其“人间共主”的宏图大略。
朱棣在位22年,始终以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核心。但是,元朝覆没的教训和白莲教起义的后果让成祖看到,佛教所具有的社会张力和潜在的政治能量是不容低估的,放纵或禁绝都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动摇王朝的政权基础。依据这个判定,朱棣即位后,以正统儒学为主,以释道兼而辅之,实行儒释道三者结合的治国理念。在成祖看来,愚民的最好办法,是让百姓拜佛问道,用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理念安身立命。为了给臣民造成皇帝崇佛的印象,成祖还对洪武时期的佛教政策作了调整,把利用、控制兼施,着重加强控制改为适度控制,重在利用,并且颇见成效。
沿袭太祖崇佛传承。明太祖朱元璋是落发为僧、造反称王的开国皇帝,17岁于濠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入白莲教起义军。这些所谓的非统经历虽为称帝后的朱元璋深忌,但他的8年僧龄及目睹元朝崇尚放纵喇嘛所产生的诸多流弊,使其对佛教内幕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为了防止佛教惑众滋事甚至造反起义,朱元璋对寺院人数、僧尼年龄、度牒年次及给牒考试都有严格规定。但因其出身微妙、善待高僧、论经讲道、敕封喇嘛的表象,仍被《明史》列为“颇好释氏教”的皇帝。朱棣以藩王夺统,名份不正,底气不足,国人多有所诟。在这种情况下,信守父为子纲的古训,沿袭太祖的传承,显然为其崇佛找到了祖脉。
重用有功僧人道衍。朱棣在“靖难之变”中以“清君侧”起兵,以“夺皇位”收场,本来有悖“四维”,却假道衍之名,以佛助其成为幌子掩人耳目。僧人道衍是发动“靖难之变”的主谋,成祖即位后,复其姚姓,赐名广孝,使之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皇帝的偏爱使道衍和尚成为当朝第一高僧,天下僧人莫不仰慕,朱棣亦被视为崇佛好僧之帝。
平衡汉藏佛教关系。藏传佛教虽然明初在汉地还有较大影响,但汉传佛教无论在宫廷、民间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成祖不仅要安抚藏传佛教,还要关照汉传佛教,不使朝廷的礼佛政策失衡,防止因借重藏传佛教而引起汉传佛教的不满。永乐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就是兼融两者的最好实证。此外,成祖还于永乐十七年(1419)御制佛曲,钦颁大报恩寺乐奏,其他佛寺皆趋而奏之。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为《法华经》作序,之后又亲撰《僧人传》,树立僧人救世恤民形象。道衍攻击程朱理学的专著《道餘录》虽为儒家所不齿,但在成祖的恩准下亦大行其畅,成为一时流行之述。永乐初年,上书道衍“诋讪先儒”的朱季友,竟因此罹祸。被人誉为华夏第一钟的永乐大钟(北京大钟寺),重达46.5吨,内壁铸汉文23万余字,内容多与佛事有关。诸如此类举措,逐渐消除了成祖“靖难之变”的阴影,淡化了他残酷屠杀建文遗臣的暴行,成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皇帝。
成祖以崇佛误导臣民,在于发挥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让人相信善恶报应,而不是让人削发出家。相反,对私自披剃者往往严厉惩处。永乐五年(1407)正月,成祖得知江南军民子弟私自披剃为僧者1800余人,盛怒之下悉数发配辽东、甘肃戍边。此举足以证明,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教,都是帝王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永乐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也只是成祖政治舞台上的一种“道具”。然而这种作为“道具”的永乐造像,不仅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积极的政治作用,即使今天乃至将来,她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和艺术价值也无可替代,因为她是我们民族和谐的历史见证,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衣钵。
解读之四:安邦治国之举,成在审时度势
永乐金铜佛像蕴含的历史信息,让人想到四川成都武侯祠的那幅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当年毛泽东曾把这幅名联推荐给到成都军区任职的刘兴元将军,足见一代伟人对审时度势的非常重视。今天用这幅名联分析成祖治藏方略的成功所在,审时度势是为至要。
检索600多年来的史典论述,总的说来,诸家对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是给予肯定的。有明一代的近300年间,基本保持了太祖、成祖时期治藏政策的连续性,西藏社会相对稳定,农牧生产日益发展,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保持着正常的隶属关系。这个局面使明王朝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力量征伐蒙古,稳定社会,恢复经济,重建皇权,也使国家在四五十年内基本实现了由乱到治的目标。
明朝自洪武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仅太祖在位的31年中,对蒙古的征伐即达20年之久。永乐迁都(1420)以后,成祖六次御驾亲征,五次鞭指蒙古。虽然蒙藏之间有着长达100多年的政治、宗教、军事和经济联系,可谓百年世交,但在明军伐蒙的屡次交战中,藏区政教首领始终未见出兵援蒙。事实表明,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举措是正确的,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与引导,可谓审时度势,抑扬适当。这样既保证了藏区的稳定和发展,又保证了西北、西南方向大片疆域的完整和巩固。
洪武、永乐时期,因连年征伐,军需频繁,民力凋弊,以致“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朝廷财力因之窘迫。在明政府恢复生产的努力中,西藏及邻近藏区虽无力援助内地,但内部社会稳定,对外没有冲突,使明政府能够集中精力繁荣经济、化解矛盾,同样为安藏治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政府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内地与藏区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除了绵延不断的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的茶马互市贸易更加活跃,“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永乐八年(1410),只陕西河州卫一地,就以茶叶换得各番族役马2714匹。永乐年间开通的雅川(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驿站,成为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经济互补的重要通道。
永乐年间的明朝,被史家誉为“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的泱泱大国;明成祖则被明史誉为“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的一代明君。分析这两个方面的成就,藏区僧俗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功不可没。由此可见,在多个民族、宗教并存的统一的国家里,审时度势地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于国家强大和民族和谐的至关重要。这就是 永乐金铜佛像所含历史信息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
解读之五:多元文化交融,实现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民族。永宣金铜佛像汉藏交融风格所蕴含的汉风藏韵和汉魂藏脉启示我们,文物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物证,而文化交融则是民族交融的先导。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条共同规律。文化交融的实质是思想的交融,精神的交融,是生存观念、生产观念、生活观念和生育观念的交融,因而是优势互补的交融,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中筑牢根基,把定方向,扬长补短,才能使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不断丰富,与时俱进,不为人制。
文化认同是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前置条件。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应当成为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研究民族文化交融史,不仅要尊重各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更要展示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一性与共融性。让全体中国人清楚,以中华民族为中国的唯一民族认同,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国唯一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我们不首先确立一个包括所有民族在内的国家认同,不首先确立一个包括所有民族优秀文化在内的文化认同,片面地强调各个民族各自的民族认同,甚至罔顾史实的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否认各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交融,那么一切片面构建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股离心力量。放眼全球,这种教训酿成的悲剧,经常会在我们的视野中闪现。
民族文化交融史的研究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既是回归历史真实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学术工程,更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集力、生命力的固本工程。因为历史与现实都已昭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主要象征、是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
为汉藏交融历史研究提供实物和图像的李巍先生,是佛教造像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他让我们看到,收藏文物是在为民族为国家收藏历史、收藏文化、收藏生生不息的中华根脉。文物虽然是历史的见证,但文物不等同于历史。不同时代的文物,必然打有那个时代人间悲欢离合、民族强弱荣辱、国家兴衰成败的烙印。虔诚地收藏、鉴定与解读文物,是对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观照与敬畏。只有把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文物的历史价值才能展现出来;文物才能穿越历史隧道,重新绽放出奇光异彩!
我以为这样做,才是对习近平主席关于“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要求的理解和贯彻。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