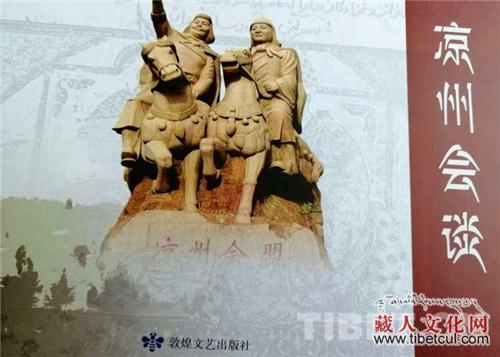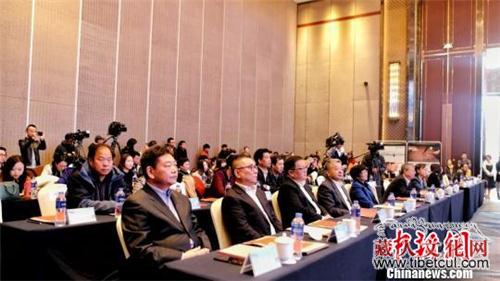五世达赖与清顺治皇帝
一、 历史背景
(一)、藏传佛教文化的东向扩展
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格鲁派是在对藏传佛教各教派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革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一教派相对于以往的藏传佛教教派而言,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首先,格鲁派要求僧人必须严守戒律。这也是格鲁派顺应宗教发展的内部要求和其最鲜明的特点。其次,格鲁派具有严格的寺院组织系统和严密的教学程序。格鲁派寺院具有由堪布、协敖和翁则等组成的僧官系统以及扎仓、康村和米村等组织机构。僧人们在宗喀巴大师系统总结佛学体系基础上而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指导下修习佛法。再次,格鲁派创立以后,每年定期在拉萨举行传昭大法会。僧人不分教派、不限地域,均可参加。传昭大法会这一活动,对于扩大格鲁派的影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格鲁派继承了由噶玛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其内部最有影响力的两大转世系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日后西藏宗教、政治,乃至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影响。
就在格鲁派发展壮大的同时,蒙古的势力开始逐渐南下进入青海、并向西藏地方逼近。据《蒙古源流》记载,早在1566年,鄂尔多斯部就与藏传佛教有了初步的接触。时鄂尔多斯部首领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兵进攻藏区,在一个叫锡里木济的三河汇合口处,曾派代表与当地宗教领袖接洽,要求他们归顺、以共同信仰藏传佛教。当地宗教领袖经过商议后,决定从命。于是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带了勒尔根、阿斯多克•赛音班第、阿斯多克•瓦齐尔•托迈•桑噶斯巴等三名僧人返回。 此后,俺答汗于1573年攻打甘青及四川藏族地区,并从当地延请了阿哩克喇嘛、固密•苏噶等藏传佛教僧人。阿哩克喇嘛还曾向俺答汗讲解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藏传佛教教义。
如果说上述史实是藏传佛教文化东向发展趋势的初露头角,那么俺答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则是藏传佛教东向扩展的继续。1578年5月,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见于青海湖西北的仰华寺。在此次会晤中,二者仿效忽必烈与八思巴,事实上解开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大规模传播的序幕。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蒙古地方圆寂后,格鲁派僧人将俺答汗的一位刚出世的曾孙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俺答汗的曾孙遂成为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他也是历世达赖喇嘛中唯一的一位蒙古人。这也为格鲁派在蒙古地方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新的、更牢固的基础。
(二)、藏、蒙、满统治阶层的政治互动
17世纪30年代,格鲁派处于藏巴汗、却图汗和白利土司的夹击之下,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之下,格鲁派遣使秘密向时驻牧于天山南麓的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求援。1639年到1640年,固始汗率军进入康区,击溃了白利土司,取得了对康区以及包括云南丽江木氏土司部分辖区的控制。1641年底,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并于1642年结束了藏巴汗政权,开始了其与格鲁派上层共同统治西藏政教的历史。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形势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当时,明朝的统治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呈微垂之势。而在东北地区,新成立的满清政权正逐渐崛起。清朝在入关以前,便已同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建立了联姻关系,并订立攻守同盟,同时大量吸收蒙古贵族加入政权,并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清政权的重要辅佐力量。
“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是贯穿清朝始终的统治政策之一。早在清入关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对广大蒙古地区有强大宗教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及其发源地西藏。在公元1639年,皇太极正式派遣察汉喇嘛等出使西藏。在致图白忒汗的书中曰:“大清宽温仁圣皇帝致书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 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尔乃图忒之主,振兴三宝,是所乐闻。倘即敦遣前来,联心嘉悦!至所以延请之意,俱令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汉格隆、察汉格隆、玉噶扎礼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哀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伊思谈巴达尔扎、准雷俄木布、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又与喇嘛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掌佛法大喇嘛:联不忍古来经典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唯尔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 。 几乎与此同时,固始汗为了让自己在西藏的权力得到清王朝的认可,也派出了一个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朝清使团。这一使团同时还携带了藏巴汗和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写给清朝皇帝的书信。
皇太极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人的来访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给予了很高的礼遇。皇太极亲率众人迎接,并对天行三跪九叩头礼,以此来表明伊拉古克三一行人代表西藏政教各派的来访是出自天意,以对藏传佛教的扶植来团结蒙古广大部众也是天意的安排。伊拉古克三朝见时,皇太极起迎;进上达赖喇嘛书信时,“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伊拉古克三一行人在盛京停留期间,皇太极为首的满州统治集团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和礼遇。据《清实录》记载,在到达盛京的第二个月,1月17日,皇太极“以朝鲜贡物分赐图白武部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藏青俄木布……等缎、布、腰刀、顺刀、貂皮、水獭皮、胡椒等物有差”。 次年2月19日,皇太极“召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及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众喇嘛,赐宴于笃恭殿。”皇太极曾下令:“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率众喇嘛在盛京活动了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公元1643年6月2日开始踏上返回西藏的路程。察汉喇嘛等人受皇太极的派遣,跟随伊拉古克三一行人回返西藏,带去了清政权对藏传佛教集团的问侯,对各教派的代表人物和实权首领也分别赠送了礼品和书信,这反映了清政权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实力现状的承认,除了特别重视以达赖喇嘛为首、并受固始汗支持的格鲁派外,也兼顾到其它人的情绪和利益。还给与济呼图克围、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等喇嘛教不同的人物以书信和礼物,以示慰问。公元1646年10月3日,随同伊拉古克三使团前往西藏的察汉喇嘛等,结束了在西藏各地的观察和活动,返回了北京朝廷。
二、五世达赖喇嘛朝觐始末
(一)、觐见地点之选择
顺治五年(1648年)五月二十日,清朝派遣以席喇布格隆为首的使团前往藏区。给达赖喇嘛的咨文中称:“瓦赤喇但喇呼图克图达赖喇嘛明鉴,大清国汗咨文……为指授正道,切盼大圣喇嘛亲来……”。给班禅呼图克图的咨文中称:“班禅呼图克图明鉴,大清国汗咨文……为利益众生,派遣以席喇布格隆为首之使团遗书邀请达赖喇嘛,敦促前来之事,喇嘛明鉴……”给固始汗文曰:“大清国汗给持教诺门汗书……为利益众生,今遗书邀请达赖喇嘛,敦促并成事吾意,尔其知之……”。清朝此次遣使之目的为邀请达赖喇嘛,这是清朝从皇太极以来给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封邀请信。土鼠年(1648年)十一月下旬,席喇布喇嘛抵达藏区,颁赐邀请信。土牛年(1649年)初三日,达赖喇嘛接受了顺治皇帝的邀请,并上书顺治皇帝陈述不能久留的理由,派噶居喜饶和他的翻译霍尔扎西携带奏章和礼品回京复命。
1652年三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启程赴京。顺治九年孟冬十三日顺治皇帝行文达赖喇嘛,陈述贼匪增多,文书频至,不能弃国务亲迎,由扎萨克克辛格亲王及内大臣等替我往迎,致书陈述不能亲迎的理由。十一月初二日钦差克辛格亲王前往迎接并给救谕。初五日达赖喇嘛的大队人马继续行进。看来达赖喇嘛对顺治皇帝的决定没有表示异议。十一月初六日顺治皇帝收悉达赖喇嘛二十三日于黄河岸边的来文称:正在行进,遣使密奏要事。十一月十六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岱噶。二十一日钦差墨尔根噶居和同行者沙济达喇抵达。根据皇上的旨意,随行者之大部留在岱噶。二十七日起程,十二月初五日经过张家口,渐次行至巴颜苏木即宣府,行至“库里”。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前楼。
(二)、五世达赖喇嘛在京之活动及辞行受封
五世达赖喇嘛第一次会见皇帝是在十二月十六日,达赖喇嘛起程前往皇帝临幸之地。相距四箭之地,达赖喇嘛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迎十步,行握手礼,由通事问安。之后,顺治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达赖喇嘛在离御座一渡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谕令先饮,达赖喇嘛称不敢,遂同饮。达赖喇嘛进献礼品,顺治皇帝询问了卫藏地区的情况,并设盛宴款待。当晚,达赖喇嘛回前楼歇息。十七日移住为其专门修建的黄寺。十九日秉图王布施财物。二十五日,顺治皇帝遣人至黄寺赏赐达赖喇嘛。
第二次会见是在顺治十年即1653年正月十六日,顺治皇帝召达赖喇嘛进宫,在太和殿宴达赖喇嘛。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二十一日顺治皇帝准达赖喇嘛“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请告归”之奏请。
第三次会见是在水蛇年二月十八日,顺治皇帝召请达赖喇嘛,赐宴于太和殿,即为达赖喇嘛饯行。
二月二十日达赖喇嘛从北京德胜门外黄寺起程。达赖喇嘛在返藏途中为前来的大批蒙古香客作了多种法事。三月初十日抵达岱噶。 顺治十年(1653年)季春二十八日顺治皇帝收到达赖喇嘛来文两件。第一件以诗体文歌颂顺治皇帝之功德。第二件中叙说本人的病情未见好转,若于入冬之前不能离开青海,则如所奏将耽误办理吐蕃特之事务,因青海与吐蕃特之间地域寒冷加雪,必致人马疲惫行进缓慢,务于十一月之前越过雪山,奏请于四月底离开此地,并请仍照前来之例供给至青海之旅途照应。另有小事,使臣彼时面奏。 顺治十年孟夏二十二日顺治皇帝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各给金册、金印。第二个五月的初一日达赖喇嘛离开岱噶。顺治十年季秋二十六日顺治帝收到达赖喇嘛七月十四日自黄河岸边的来文,称:我旅途平安,已至青海,本月之内前往吐蕃特,此间亦作各种诵经活动以佑国政。 十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顺治十一年1654年季夏二十日清朝方面收到固始汗于吉日发自呼毕勒罕庙附近之地的来文,称:汗统驭万民至大海之滨,今仍念及并赐给金册金印,我等甚为嘉悦。
三、总结
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帝的会晤是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与清王朝统治者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邂逅”。128年后,六世班禅重见清朝皇帝,亦是藏传佛教东向发展的继续。学者张亚辉在《六世班禅朝觐事件中的空间与礼仪》一文中指出,元代以后汉藏并立的知识格局以及清代多种宇宙观交错并存的状态,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中国的性质。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十分重要。藏传佛教具有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和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内部的科层制,宗教领袖不仅是权力的代表,更是知识(包括宗教知识和世俗知识)权威和卡里斯马的代表。而清政府对五世达赖喇嘛及六世班禅的礼遇虽不排除政治上的各种考虑,但亦拉开了终清一朝寻求妥善对待藏传佛教文化的序幕。
(作者姚婧媛,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现为西藏大学藏族宗教史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