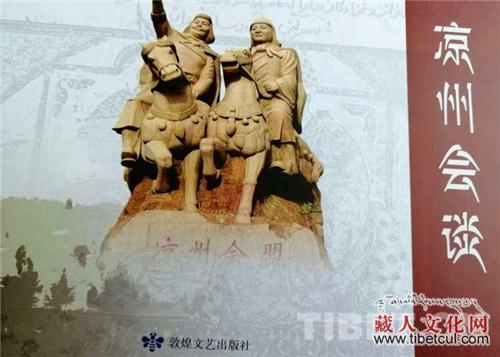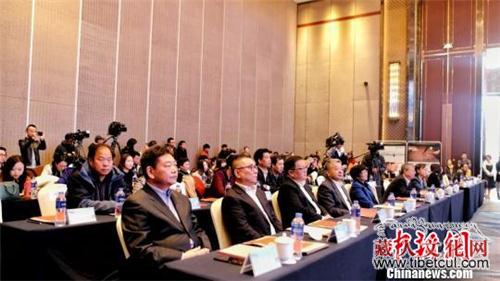图为旧西藏大领主庄园。闻鸣摄
在西藏所有的节日中最为隆重的是“洛萨”(新年),“洛萨”为藏历新年初一。由于藏历历算的特殊,每年的新年与阳历相比较,差距较大。但一般来讲,每逢藏历“新年”几乎是在开春之际。哈勒在他的《西藏七年》中写到:“眼看春色满园。三月已经来了,本月四日起便是新年节庆——所有西藏节日中最大的一个,一闹便是三礼拜”。
尽管藏历“新年”是最为重要和最为隆重的节日,但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不同,西藏后藏地区和一些农区和牧区并不会由于新年的到来而重视这个节日。然而,这种区域性的行为并不会影响藏族对于“新年”的认识。尤其是居住在拉萨的所有的贵族家庭。因为,藏历“新年”对于贵族们来讲是一次完整一致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情趣上等等各个方面的整体表现机会。“新年”会使每个贵族家庭有机会在社交生活上留下一次较为清晰的印记,这种印记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也表现在贵族社会所强调的礼仪上,因此贵族家庭格外重视这个能够展示其贵族阶层的特殊生活方式的机会。
既然“新年”成为西藏贵族家庭展示实力的机会,为“新年”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自然成为贵族家庭的最大的一次重要的竞争活动。
离“新年”还有一个月,每个贵族家庭的庭院都显得格外热闹。女主人似乎显得非常忙碌,她们手里拿着一串钥匙,长呼短唤着身边的仆人,不时地向“强佐”(管家)或者“涅巴”(管理员)询问一些事宜。事实上,所有的贵族妇女为了证明自己的贤良和治家能力,把值钱的和不值钱的物品都进行分类,分别放在“涅仓”(一所空房)或者放在箱子或者放在柜子内并把它们锁上。由于“强佐”或者“涅巴”时不时地需要开锁取物品,因此少不了劳动女主人。而女主人的开锁、上锁的行动,证明了女主人治家之行为。
时近年终,喧嚣和热闹充溢着每个贵族家庭的庭院,每个房子都在仆人们的收拾中不断被改变。每逢“新年”,仆人们都要对主人的房子乃至整个庭院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藏族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拖积”。“拖积”是由牢固的习惯信念支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尽管贵族拥有的每一间房子、每一个庭院都会在仆人的照料下,每天透出光亮的色泽。然而,千百年的心理积淀和习惯使然,每逢新年人们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即使是非贵族家庭也如此。“拖积”是一种规律性很强的烦琐劳动,同样也是一种增加想象力的劳动。毫无疑问,“拖积”是为新年进行的有目的性的劳动,自然就有确定的时间。一般来讲,藏历十二月的任何一天都会是进行“拖积”时间的最佳开端。但是为了不动怒于神灵,需要选择好的日期,当然这种选择并不需要进行打卦问卜,“络托”(藏历年历)自然成为一种依据。“拖积”的分工是比较明显的,除了搬运大物品上需要一些男劳力外,一切清扫工作都由女佣来承担。虽然清扫工作有了明显的分工,但是女主人不会因此而闲松,她们亲临观察并进行指导。无疑,“拖积”给平日无所事事的贵族妇女给予了一次展示治家才能的机会。“拖积”开始到结尾,女主人始终是中心。仆人们在她的指导下,把第一个房间内所有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搬出,并且把没有东西的空房从房顶、房墙、地板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扫除,之后又把原有的东西搬回房内进行摆放。如果这时女主人或者有经验的女仆能够发挥一些想象,会把原有的房间面貌可以焕然一新。等第一个房间收拾妥当,用同样的劳动方式对第二个房间进行相同程序的劳动。没有多少天,第个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
当“拖积”进入尾声时,女主人感觉到非常得疲惫,最后在女仆的搀扶下回到卧室或者客厅内,与男主人或者仆人一道谈论“拖积”的经过。女主人如释重负,女仆不会忘记轻轻捶打女主人的背部或者腰部。就在女主人感觉辛劳的时候,女仆们还在收拾每间厨房和各自的住所。“厨房”对于一个贵族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尤其是“灶”的建设,更是不容忽视的。同样厨房的收拾要由厨师以及帮厨来监督进行其收拾的方式基本一致。只是在收拾完毕,在灶墙上用干面粉画上“卐”图,祈求灶神的护佑,同时在火灶四周撒一点青稞,以求食物丰厚。
“拖积”很快在仆人们的集体劳动中结束,随着“拖积”尾声的到来,“新年”的准备工作也开始就绪。其中“强玛”(酒女)在“强佐”的指令下开始浸泡一点“青稞”种子,并把浸泡的“青稞”种子栽培在精致的花盆中,准备为“新年”培育“青稞”新苗。与此同时,“强玛”还要开始着手酿新年酒。

佛教仪式。张鹰 摄
迎“新年”的准备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炸面果子(卡赛)。“卡赛”的准备对于贵族家庭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其象征意义并不很强烈,但是“卡赛”种类的多少,“卡赛”品种的好坏等等都成为“新年”前后的重要话题。正因为如此,每个贵族家庭都非常看重炸“卡赛”一事。有了炸“卡赛”一事,自然就有机会把每个贵族家庭的厨师的光辉形象得以显露。拥有资历和经验的厨师不仅给自家主人以光辉的门面,同进也会受到其他贵族家庭的热情欢迎。雇佣厨师炸“卡赛”是一件很自然的劳动借换权利,但这种权利被贵族家庭的家长所掌握。在西藏,厨师的身份具有两面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资历和经验的厨师。作为归属于贵族家庭厨师,他们如同所有的仆人一样,言行举止都会受到主人们的制约,但是与其他仆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或多或少地拥有一定的自由和自治力。同样在拉萨,还有一种以厨艺为生计的“自由人”。他们一般为世袭厨师家庭出生,常常被贵族家庭所雇佣,做为“自由人”,他们每年要为政府上交“人头税”。正因为如此,贵族社会和贵族家庭至少在表面上非常尊重厨师。在“新年”准备工作中,厨师们除了大显身手地油炸各种果子外,还要与“强佐”、“涅巴”一起共同准备“新年”的宴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年”到了。大年二十九是“新年”前奏曲,这一天,由于一种公允的意识指导,家庭中的老爷、少爷们开始在仆人的伺候下进行洗浴,洗去旧年的尘埃。与此同时,家庭中所有的男性都会在这一天进行洗浴。临近傍晚,每家每户都在作“古突”(疙瘩面)。“古”为藏话中的“九”之间,“突”为面汤食(面食的混合概念。即面条、面片、面疙瘩、面糊等)。一般来讲主人和仆人一同食用“古突”,因为“古突”的食用不仅仅是一种年庆前必须保持的习俗,同时它还包含着很强的娱乐意义。“古突”面团里要包各种寓意的东西,如:石子、辣椒、木炭、陶片、磁片、羊毛等等。与此同时还用面团来作“太阳”、“月亮”等等一些有说法的形象。当食用“古突”时,厨师会在每个人的碗里放一个面团,等大家食用完毕,由一仆人把面团打开,解释其意思。每个解释都会引起一番热闹,其中孩子们最害怕拿到意思不好的面团。等大家食用完“古突”,紧接着家中有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女仆要进行驱鬼仪式。其仪式既不用借助僧人,也不用借助经书,而是仅靠一种习惯和经验。驱鬼的仆人们,有一人手里拿着点了火的麦秸,有一人端着装满“古突”的陶罐,还有几个是助威者。他们一边奔跑着,由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一边嘴里大喊着“鬼滚出来”。一边喊一边不回头地径直跑出门外,一直跑到十字或丁字路口,把燃着的麦秸和“古突”都端放在地上,这时四面八方的临近驱鬼者都会聚在一起,大家共同欢呼着,跳跃着,火光冉冉升起,一年的鬼气似乎在人们热闹的呼喊和直升的火焰中被驱赶。“古突”和“驱鬼”是迎“新年”的一次重大助兴活动,大家为此非常兴奋、热闹。等到驱鬼者返回,各家庭又要进行一次习惯性极强的严肃活泼的游戏。正当驱鬼者离开家院大门时,有一仆人马上会把大门关上并上栓,以免鬼气徘徊返回。主人和仆人都会回到主客厅内,按主次坐位入座,“强玛”手里捧着新酿的酒敬献主人,与此同时,仆人们也开始饮用主人赐给的酒。等听到驱鬼返回的敲门声,主人和仆人同时来到门口,院内院外隔门进行“问答”。一切就绪,驱鬼者方可进门。驱鬼者的功劳会得到主人的“奖赏”,主人亲自给每个驱鬼者赐一杯青稞酒,即使那些不善饮酒的驱鬼者也要接受这种“奖赏”。
大年三十是迎接“新年”的关键一天。这一天里太太、小姐们在仆人的伺候下开始洗浴,同样家中所有的女性都要在这一天进行洗浴,与此同时,仆人们再一次把各个房间清扫得一尘不染。到了傍晚,开始在几个主要房间(主客厅、主人的经堂、以及供奉佛祖和护法神大经堂)摆设“德嘎”(食物供品,其中“德嘎”是一种面制的具有固定形状的贡物)。除夕到新年之间虽然仅隔一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天里,每个贵族家庭都似乎处于一种连续思想和劳动的观念之中。最终一切会显得新鲜明亮、富丽堂皇。除夕之夜,女人们缺乏一个固定长度的歇息时间,包括女主人。尽管女主人不用劳动,但是连续性的思想活动和治家意识使她们感到非常得疲惫,但是对于新年所付出“劳累”的感觉是愉快的,也是她们乐于表现的行为。尤其是女主人们倚靠着靠背,指点着女仆翻开一个又一个装满服装的大箱子时,她们的感觉不仅是惬意的,而且还有些显得沉溺于其中。所有的贵族妇女,无论是她们长得美丽还是难看,无论她们的等级如何,有一点似乎是相通的,她们都非常喜爱各种各样的服饰,她们也喜欢鼓捣那些不同颜色、不同料子、不同形状的服饰。
“初三日起,三大寺僧人,即相继下山,入拉萨市。自藏历初五至二十六日,为喇嘛传召之期。在此期内,拉萨之行政、司法各权,改由哲蚌寺之铁棒喇嘛负责执行,政府机关一律停止办公,三大寺及拉萨附近各寺僧众,约二万余人,须于初五以前,集中拉萨”(朱少逸《拉萨见闻录》)。新年第四天,“僧院司教工从哲蚌寺来走访外廓(拉萨古城外环),并公布大愿法合(传召)期间要遵守的规定。在大法会前夕,他宣布在这段期间内任何人不得吵闹、不得酗酒、……这一切禁令从新年的第四天开始生效。前一天晚上,所有主要僧院的喇嘛都会来拉萨。大愿法会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节日,这些外来的僧人被安置在拉萨人家的储藏室休息。在法会那天清晨,所有的僧人都会到杰坎,三层楼很快站满了僧人,异常拥挤”(《我子达赖》)。
“新年”传召大法会是西藏拉萨新年的一个特殊的重大宗教活动,在这个宗教活动期间宗教权威广泛地而又无限地被扩大,以至于在这段时间里把拉萨地方政府的司法权力也移交给宗教。《拉萨见闻录》一书较为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活动:“(初三)上午九时,哲蚌寺铁棒喇嘛二人至布达拉宫报道,旋即乘马急驰而下,后随袒背佩剑威武有力之喇嘛十余人,绕拉萨全市行一周,且行且呼曰‘自今日起,全拉萨的官民,除热振(当然包括达赖喇嘛)钦差外,都要归我管理,尚有滋事及不守规律者,不论僧俗,一律严惩’。于是拉萨市之统治权,随铁棒喇嘛之宣言而无形转移。……初四下午,铁棒喇嘛接受浪子厦。浪子厦为管理民事之机关,相当一市政府;自今日始至藏历一月二十六日止,拉萨之政治形态完全消失也”。
关于传召,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一四零九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办大祈愿法会(俗称传召法会)。自始起每年藏历初五日在拉萨举行隆重的传召法会。传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借新年之际而举行的祈福驱邪的宗教活动。有了规则,就自然会有行为。尤其是贵族家庭不会放弃这种求功德获荣誉的行为。传召当天,贵族家庭纷纷给寺庙和僧人发放布施。传召期间朗朗颂经声顿时把藏族对于宗教的信仰提高到无限。尽管如此,贵族家庭之成员不会因此而影响新年的节庆世俗活动。
在年庆的互访活动中,能够凭借高贵的出生来激起贵族阶层强烈的感情有几种现象。首先引入眼帘的是居住建筑外观粉刷,与此相呼应的是宽敞美丽的院子、洁净精致的客厅、阳光灿烂的阳台以及从中透出的暇逸生活之气氛。任何一个贵族家庭都不会放弃想象可能说明的一切行为,追求外在的形式,不外乎是要增加周围的想象。由于贵族阶层统一的认识,对于观察而引起的想象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可以通过可能进行的修饰来获取想象,进而通过想象说明某个贵族家庭可能有的富裕和享乐的图景。正因为如此,家具的布置,以及器具的精致既是用来点缀整个建筑,也是用来说明该家庭的等级品味和财产显现。事实上,某个贵族家庭都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把客厅摆设得古朴典雅,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很少去讨论这种统一的追求,但有一种相应的阶层等级心情,他们会把棕色作为一种古老的典范成为建筑装饰的主色。与这种棕色的主调相一致的自然是贵族家庭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的礼仪社交生活。
由于贵族成员的想象是建立在贵族家庭生活主调的重复出现的基础上,因此年庆互访活动中,很少有家庭受着冲动的支配,把建筑外观和与之相呼应的房屋装置不会进行一些可能超出贵族阶层等级想象的改变。既是新型的达赖喇嘛家庭,他们也会在有经验的仆人指导下,谨慎地接受贵族应具备的审美要求。对于来访者来讲,最能增加强烈的想象力的是美丽而宽敞的院子,无疑它是重复家庭温馨的幕帘,通过这个幕帘揭开了贵族家庭之间极端的生活本质和精神实质。所有展示的形式既然有了这么强烈的感情,自然就会成为每年贵族家庭所极力追求的对象,同样也成为每个贵族来访者所注意和感觉到的对象。
年庆所花费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每个贵族家庭在趣味的高雅上和概念的统一上尽管非常相似,但是在时间的认同上可能缺少某种意义上的和谐。然而,家庭内可能具有的时间模糊之概念,必然会被外面环境的一些象征性表演所提示,年庆也就在这种提示中被结束。

西藏阿里普兰婚礼中的迎宾仪式。加措 摄
在年庆中,拉萨还要举行一些最为古老的奇特的活动。其中最为奇妙和精致的是年庆的某一个晚上能够观赏到的“大昭寺酥油灯展”。“高越十公尺的木架自地面升起,……黄昏过后,这些由僧人用酥油制成的艺术品,就会被带过来,这些五颜六色的酥油花,是由僧院里特具才华的僧人,以艺术家的匠心,慢慢捏揉塑造出来的。由于动用了极大的耐性,这类作品往往做工精致,美轮美奂。酥油花创造大赛某晚举行,政府会颁奖给最优者。这奖多年来都是由密宗学院获得(《西藏七年》)”。酥油花的展出再一次丰富了贵族官僚们的年庆活动,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地来到“噶厦”办公驻地(大昭寺隔壁一墙之隔),等待着达赖喇嘛或者摄政的到来。黄昏临近,月亮当头,这时会出来数目不等的开路藏军,看热闹的人们开始向两边散去,腾出一条空路,这时大昭寺数千盏酥油灯开始被点亮,与此相呼应的是每个贵族在自家窗户上也点燃几十盏酥油灯。整个拉萨被大昭寺被酥油灯和皎洁明亮的月亮辉映得无限光彩。达赖喇嘛和贵族世俗官僚开始缓步走出大昭寺,开始观看“酥油花”。周围的人们双手合十,口颂经文,双眼垂地,接受着可能与宗教符合的一切福气。
“酥油花”的观赏如同幕间插曲一样,随着月亮的西移便结束了。官僚以及他们的家庭,乃至整个拉萨都非常熟悉和习惯这样的庆典活动。当八廓街只剩下一些无主人的狗在毫无顾忌地来回走动时,“酥油花”展示的辉煌活动顿时成为一个难以让人理解的剧目。一年之后,如同烂漫的儿戏,在八廓街再一次会展示“酥油花”的景观。这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涵盖了文化影响和文化传播,但是,西藏人,包括那些曾经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西藏贵族家庭或贵族子弟,似乎对此从未想过进行分类和解释,或者改变。
“新年”是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内容贯串在其中,就在结束“酥油花”的神圣展示活动的时候,大昭寺“广场”立刻成为随意启闭的“竞技场”,具有喜剧色彩的“运动竞赛”便开始了。“运动竞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具世俗特点的娱乐活动,所有的拉萨人都喜欢观看这种游戏。达赖喇嘛或者摄政往往是从大昭寺西厢阁楼内探观该活动,由于棉布窗帘的遮掩,一般人是看不到他们。而噶伦以及官僚成员,他们也会坐在固定的位子上,从上往下地观看节目。
与所有的活动一样,“运动竞技”同样也没有固定时间作为开幕,但是初升的太阳位子成为开幕可能依据的最佳时间。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开场下,两个赤膊的年轻人开始进行摔跤。摔跤“有自己的规则。身体任何部位(除了脚)碰到地面,都算摔倒。既没有参赛者名单,也没有如何比赛开始的宣布。只有一块草席往外一铺,人从人群里走出,彼此一抓就开始比赛。参赛者除腰上一块布外,啥也没穿。……比赛很快结束,又换一对新选手上阵。从没有势均力敌,赢观察家不易的扎实比赛。胜利者也没有如何殊荣,而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共同接受白巾(哈达。实际上哈达的等级不一样)。他们向大人(四大噶伦)鞠躬,大人微笑递上白巾,比赛者当着摄政的面磕上三个响头然后回到人群中的亲朋好友间”(《西藏七年》)。摔跤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尽管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比赛规则,但是赢者会在一片欢呼声中绕着观众围圈炫耀自己的胜利。与此相一致的比赛还有“举重”。“继之进行举重比赛。举一块沉重、平滑的石头,这石头八成已看过数百次新年节庆了。石头必须被举起,绕旗杆一周。殊少有人能表演此等绝技。往往是大踏步充满信心而来,却发现丝毫举它不动,或好容易举起,却一会儿又溜了手,险些砸到脚趾头。每有这等情形发生,总引来满堂笑声”(《西藏七年》)。尽管这些活动并不象现代意义上的运动一样尽善尽美,但是这种随意的展示,有如轻松的戏剧,能给拉萨的蓝天带去一些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