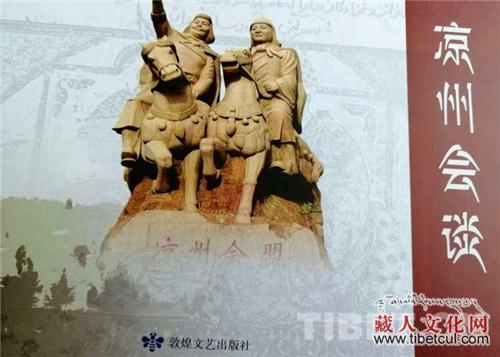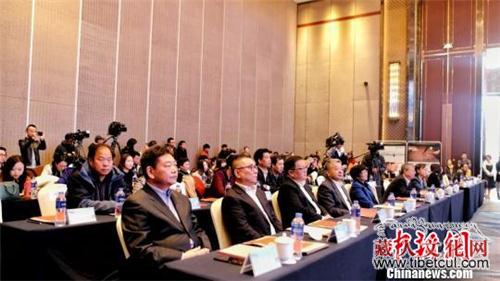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进城之三》 陈丹青画作(图片来自网络)
“毕业作展出后,我曾在文稿中竭力陈述自己为什么以及怎样画出这些画。多年后我才恍然:所谓西藏组画只是1978年‘法国乡村画展’来华展出后的私人效应,而当我在画展中梦游般踯躅不去,中学时代躲在上海阁楼临摹欧洲画片的记忆,倏忽复活了。”
陈丹青1968年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结识了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等上海美专公认的才子。
但那时的上海,并不是艺术的圣地。1974年,陈丹青管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后面全是人挤着,比现在印象派展览的观众多得多了。”(陈丹青自述)
“《西藏组画》有个最最简单的原因,谁都忽略了,连我自己都忽略了,就是在1978年我考上美院以前,文革后第一次请来了法国人的画展。”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
陈丹青曾多次提到这次展览对他的影响。“‘文革’中我希望模仿真正的苏联现实主义,画得像苏里科夫:‘文革’结束后,我立即想要画得像米勒,像真正的法国现实主义,因为法国乡村画展来了中国,那次展览对我影响太大了,所谓影响,我以为就是开眼界,就是模仿的欲望。这时,我的上海‘基因’起作用了:我少年时代的开口奶其实是欧洲的,是民国上海遗留的老派欧洲绘画。但是中山装及汉人的面孔表现不了“苏联”或“法国”,西藏给了我那种可能。”(陈丹青自述)
“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陈丹青说,“我对西藏既不了解,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
在陈丹青的记忆中,“两次西藏行,相隔四年。头一回时在‘文革’终点,《泪水洒满丰收田》与翌年那届全国美展,恐怕是1949年后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最后一次集体展示。那年月,我像所有知青画家一样,竭力模仿国内名家堆叠厚颜料方笔触的苏式画法,瞧着宽袍大袖的西藏人,满脑子苏里柯夫或德加切夫。当我在布达拉宫西南侧劳动人民文化馆一问小屋子里瞧着画布,走近退远,自以为是个‘苏联’革命画家。第二回去西藏,正当改革开放前夜,不但世道大变,我也见识增长,画画时拼命默诵库尔贝、勒帕日、柯罗、米勒的朴素画面,自以为是个‘法国’古典画家。”
“《西藏组画》只是完成了一个美学转换,即无内容、无主题、无情节、无故事的一个小画面,而且由很多小画面组成的生活形态,这是法国乡村画展给我的。而我能够很顺利的从苏联绘画转化到这里又跟我十四岁到十七岁临摹的欧洲绘画有关,当时我还没有画界的朋友,还小到不能进入大人的圈子,我在家里临的都是欧洲的艺术。”
“事实上我一开始学油画从十四五岁开始,最早临的是欧洲的油画,从十四岁到十七岁插队,这三年时间我临过鲁本斯,临过哈尔拉莫夫,是俄罗斯留在意大利的画家,临过他的两张《意大利女孩》。”(《人道主义就是一张脸——陈丹青谈<西藏组画>》)
1980年,陈丹青拿出了七幅画,还在忐忑能有一张展出就不错了,结果没想到不但全部展出,而且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当时是这样,我想老师和同学都没有料到我会拿回来这么一批作品。第一那么小,第二是好几张,第三完全没有主题。四年前我第一次到西藏绝对是苏联画法,我拼命想学苏里柯夫、德加切夫、马伊森科等我们能想得到的苏联画家,而且是准政治题材,这也是没问题的。忽然我拿出七张灰灰的小小的作品,大家会忽然觉得很新很奇怪,我看出来他们不但立刻允许我展出,而且立刻成为那届展览至少油画班被议论的一组画。”(《人道主义就是一张脸——陈丹青谈<西藏组画>》)
陈丹青还记得,当时全国最权威的美术杂志《美术》和《美术家》跟他约稿。“忽然两份杂志都叫我来写,我急死了,不知道怎么写。”《我的七张画》写了将近有一个月都写不出来。后来,两篇文章1981年1月号的两份杂志上同时发表。在《美术研究》作品作为封底,在《美术》杂志上有3页内容,封面是罗中立的作品。
“作品的主题不一定一言道尽,不能说得太清楚,这还不光是个含蓄的问题。我发现所有高乘的作品,特别是诗和绘画,都具有一种你一看就领会,就被打动,但却说不出来的魅力。”(陈丹青《我的七张画》)如今回过头去看30年前的《西藏组画》,无疑已经开始显现出这样的魅力。
隔着几十年的岁月,陈丹青开始回顾那些在西藏写生的日子。“至今我还记得我所画过的若干美丽的男女,那时他(她)们正当青春,今已是中老年人了。这三十幅速写中,还有几篇画于我第一次进藏的1976年,及今想来,仿佛远古的事情。可惜我少梦,即便有,醒来也忘却,倘若想念西藏,兼及自己早年的绘画的情意,这些纸片,准确地说,这批精印的版画,就算是我在高原遗存的梦痕了。”
最怀念的是那时的纯真。“杜尚有言,一件作品之所以著名,并不全在作品本身,而在这件作品被人一再提及的次数。有幸而不幸,我的七件“西藏组画”至今被一再提及,有如重复戳盖的印记……今次回看《进城之三》,我惊异于自己尚未出国前作画的专注与朴实,后来虽则大开眼界,单是米勒的原作就见及不止百幅,然而再也不能寻回彼时的纯真。现在我瞧着画中那位女子朝我看来的眼神,不知作何感想:她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然而如今我也成了她目中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