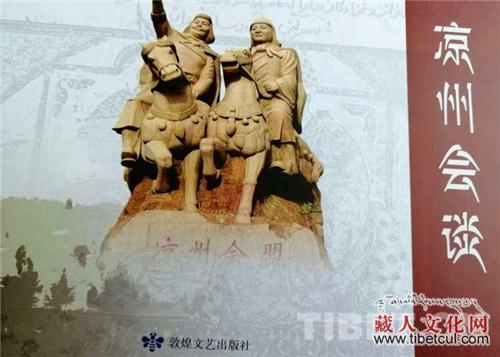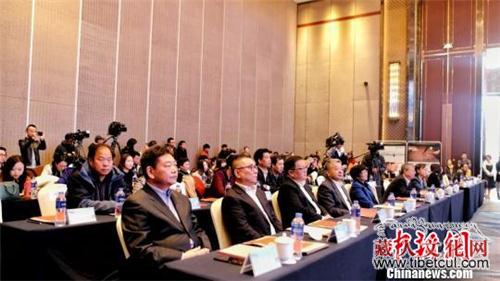《西藏组画》之《进城》(一) 陈丹青画作 布面油画(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
《西藏组画》问世之后,直接掀起了美术界的一股西藏风。青藏高原原始的生存状态、浑朴自然的人情风貌成为一种流行的表现题材。这种趋势后来又被整合进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油画民族化”进程(蒲鸿《被误读的<西藏组画>》)。
“所谓‘西藏组画’,是我七件毕业创作在1980年展出后外间给予的名称。其实,当我在拉萨城创作时并没有幅数的预设,更没有作成‘组画’的意思。为了背离巨型的、单幅的、叙事的、主题性的文革创作模式,我选择了小尺寸的、多幅的、非叙事的、无主题的作法,一幅接一幅画,每幅画题也务求简单:《母与子》、《牧羊人》、《朝圣>》、《进城》……当时,影响我的不再是苏联大型历史画,而是1978年首次来华展览的《法国乡村画展》,其中库尔贝、柯罗,尤其是米勒的小幅油画给予我莫大的启示:有情节,但没有故事,有画面,但未必是主题。我们不能因此将他那些小小的农村生活画面——祈祷、拾穗、播种、收割——叫做《巴比松组画》,他也不过是一幅接一幅地画,用心用意,惟在恳切的描绘、人物的内心、画面的深处……在1980年左右的中国美术界,类似的尝试尚属初见。此前长期形成的创作观,是作者提呈一幅巨大的创作,然后给出意义明确的解释,并据以落实为作品的名称。因此当评家描述我那些小画时,同时面对七幅画,不便一幅幅称引画题,于是统称之为《西藏组画》,沿用至今。”
谈起《西藏组画》的由来,陈丹青这样说。
事实上,陈丹青的西藏系列作品共分两组:一组是1976年在西藏停留四个月创作的三幅作品《泪水洒满丰收田》、《华主席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一起》和《西藏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二组是1980年中央美院毕业创作去西藏创作的七幅作品,被称为西藏组画,包括《母与子》、《进城之一》、《康巴汉子》、《朝圣》、《进城之二》、《牧羊人》和《洗发女》,加上1981年留校后创作的两幅作品《风吹草低》和《荒原呼啸》。
真正令陈丹青蜚声海内外的是这七幅作品:《母与子》、《进城之一》、《康巴汉子》、《朝圣》、《进城之二》、《牧羊人》和《洗发女》。其中有六幅在拉萨完成,《牧羊人》回北京后完成。创作时间为1979年至1980年。
作品《母与子》主要表现的是藏妇女哺乳孩子的画面,她们散坐在地上,默不作声,呆呆出神的面容,在构思上,概括,提炼。构图上,人物组合自然。
《母与子》最初命名为《三个母亲》。翻开破旧的日记,年轻的陈丹青记下了创作这幅画时的心情:
一口气勾出“三个少女”“三个母亲”“三个谈话的女人”,激动不已,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由,我终于学会像说话一样画画。
画“三个母亲”,意思渐渐出来了。这应该算是我过去十年来第一张真正的创作吧!
继续画“三个母亲”,我觉得灵感和技巧一天比一天照顾我。
三个母亲”将近完成,我得意地唱歌,照这样我至少可以带三张精致的画回去了。我好像从来没画过这么好看的,真正像一件作品的画。
来藏后第一张创作,慢慢地润色修改,是慎重而幸福的事。
陈丹青曾经说:“我当年最为迷恋的印象,便是藏人进城互拽衣袖以防走失的淳朴相:《进城之一》,画得是三位彼此牵衣行走的女孩;《进城之二》,画得是怀抱乳儿的妻子拽着丈夫的长袖,也即后来被发表最多的那幅。”
“这纯粹是擦肩而过的印象。结伴出行的姑娘看去经常是亲切有趣的,西藏的牧羊女上街喜欢一个拽一个的袖子,这就更有意思了。她们脸上未见世面的羞怯神色有一种本来的、单纯的魅力。他们都穿着简单缝制的羊皮袄,不像出嫁后的牧女有各种佩戴披挂,结果反而显得和她们的脸一样更本来,更单纯。”(陈丹青《我的七张画》)
作品《进城之一》(最初被称为三个少女,三个姑娘,进城的三个姑娘)在日记中,陈丹青这样写道:
午后画“三个少女”。感谢主,一切证明我进了学院并没有像许多人警告的那样“完了”。相反,我更强了。愿上帝把妙悟与灵感长久赋予我。近来多么幸福。
我欣喜地感到慢慢在成熟,一切是可能达到的。
迟午为“三个姑娘”的背景再次上街画了些窗户,为画中几个窗户,我起码写生了二十个窗户了。
午后继续画“三个少女”。晚上勾出“昌都汉子”,虽然还差些局部素材。创作的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