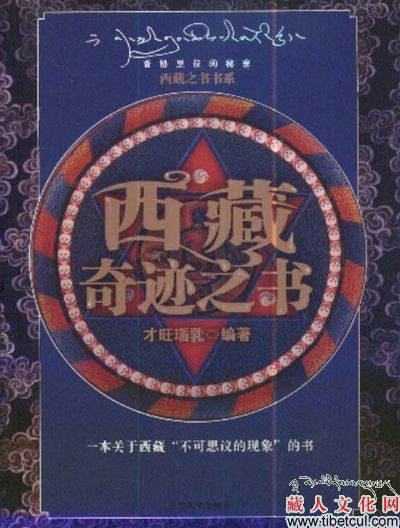гҖҖгҖҖзӣ®еүҚжҲ‘们еҜ№еҸ°ж№ҫжҲҳеүҚеҮә家еҘіжҖ§зҡ„з ”з©¶еҲҡеҲҡиө·жӯҘпјҢжұҹзҒҝи…ҫйҰ–е…ҲжҸҗеҮәд»Һж–Ӣ姑иҪ¬еҸҳеҲ°жҜ”дёҳе°јзҡ„иҜҙжі•пјҢдҪҶжҳҜеҜ№ж–Ӣ姑зҡ„з ”з©¶еҲҷд»ҳд№ӢйҳҷеҰӮгҖӮиҘҝж–Үи‘—дҪңдёӯеҜ№ж–Ӣ姑зҡ„з ”з©¶иҫғеӨҡпјҢMarjorie Tropley еҜ№е№ҝдёңгҖҒж–°еҠ еқЎең°еҢәзҡ„е…ҲеӨ©йҒ“ж–Ӣ姑зҡ„и°ғжҹҘжҳҜз»Ҹе…ёд№ӢдҪңпјҢиҝ‘жқҘдәҰжңүеҸ¶жұүжҳҺгҖҒеҗҙеҮӨд»Әзӯүдәә继з»ӯз ”з©¶е№ҝдёңзҡ„ж–Ӣ姑пјҢиҷҪ然еҪјжӯӨеҲҮе…Ҙзҡ„и§’еәҰдёҚеҗҢгҖӮ
гҖҖгҖҖTropley жҸҗеҮәеҰҷе–„дј иҜҙеҜ№дәҺеҘіжҖ§жҠ•е…Ҙж–Ӣ姑з”ҹжҙ»зҡ„еҗҜеҸ‘пјҢжһ„жҲҗжӢ’е©ҡдёҺдёҚиҗҪе®¶д№ дҝ—зҡ„дҝЎд»°иғҢжҷҜпјӣеҸ¶жұүжҳҺеҲҷд»Һд№Ўй•Үзҡ„е®—ж•ҷзі»з»ҹпјҢжҺўи®ЁзҘ–е…ҲеҙҮжӢңзҡ„зҘӯзҘҖдёҺж–Ӣ姑дҝЎд»°зҡ„е…ізі»пјӣиҖҢеҗҙеҮӨд»ӘеҲҶжһҗеҘіе„ҝеұӢдёҺж–Ӣе ӮеҶ…зҡ„еҘіжҖ§з”ҹжҙ»д»ӘејҸпјҢеҜ№ж–Ӣ姑зҡ„и§ӮйҹідҝЎд»°д»ҘеҸҠжІЎиҗҪжҸҗдҫӣеҫҲеҘҪзҡ„иҜҙжҳҺгҖӮеҸ¶жҢҜиҫүжҠўж•‘е…¶зҘ–зҲ¶жҜҚжүҖеұ…зҡ„й«ҳйӣ„е®қеҚҺе Ӯиў«ејәиЎҢжӢҶжҜҒж—¶п№җеҜ№е…¶ж–Үзү©гҖҒи°ұзі»гҖҒе»әзӯ‘гҖҒжі•еҷЁз•ҷдёӢзӣёеҪ“е®Ңж•ҙзҡ„и®°еҪ•гҖӮе…¶ж•°жҚ®дәҰжҳҫзӨәи§ӮйҹідҝЎд»°дёәжӯӨж–Ӣе ӮжҲҗе‘ҳйҮҚиҰҒзҡ„дҝЎд»°гҖӮиҝҷдәӣз ”з©¶йғҪзӮ№еҮәи§ӮйҹідҝЎд»°жҳҜеҮқиҒҡж–Ӣ姑宗ж•ҷиә«еҲҶе’ҢеӣўдҪ“и®ӨеҗҢзҡ„йҮҚиҰҒж„ҸиҜҶеҹәзЎҖпјҢдҪҶжҳҜеҜ№дҪӣж•ҷе°јдј—е’Ңж–Ӣ姑зҡ„е…ізі»еҲҷзӮ№еҲ°дёәжӯўгҖӮ
гҖҖгҖҖAndrea P. SankarеҜ№дәҺйҰҷжёҜж–Ӣе ӮеҰҮеҘізҡ„з ”з©¶пјҢеҲҷжҢҮеҮәдҪӣж•ҷеҜәйҷўдёҺж–Ӣе ӮйғҪ收容жңүжүҖи°“зҡ„ж–Ӣ姑пјҢеҘ№д»¬еҸҜд»Ҙж №жҚ®иҮӘе·ұзҡ„з»ҸжөҺзҠ¶еҶөе’Ңж –жҒҜзҡ„еҜәйҷўж–Ӣе Ӯи®®е®ҡз”ҹжҙ»жқЎд»¶пјҢдҪңдёәе…»иҖҒйҖҒз»Ҳзҡ„еҪ’е®ҝпјҢе®—ж•ҷеҪ’еұһзҡ„и®Өе®ҡеҜ№еҘ№д»¬е№¶дёҚжһ„жҲҗй—®йўҳгҖӮSankarеңЁйҰҷжёҜеәөе Ӯзҡ„з ”з©¶дәҰжҳҫзӨәпјҢж–Ӣ姑们з”ҡиҮідјҡжҺЁеҮәд»ЈиЎЁеҮә家еүғеәҰдёәе°јпјҢ然еҗҺйӣҶиө„е»әз«ӢдҪӣе ӮпјҢе…ұжёЎжҷҡе№ҙгҖӮ
гҖҖгҖҖ笔иҖ…и®ӨдёәSankar еңЁйҰҷжёҜеҸ‘зҺ°зҡ„ж–Ӣ姑еұ…дҪҸдҪӣж•ҷеҜәйҷўзҡ„жғ…еҶөпјҢдәҰйҖӮз”ЁдәҺи§ЈйҮҠеҸ°ж№ҫзҡ„зҺ°иұЎгҖӮе°ұе®—ж•ҷз”ҹжҖҒиҖҢиЁҖпјҢеҸ°ж№ҫеҰҮеҘізҡ„е®—ж•ҷз”ҹжҙ»пјҢеҹәжң¬дёҠдәҰе’Ңй—ҪеҚ—гҖҒе№ҝдёңзҡ„и§ӮйҹідҝЎд»°зӣёеҪ“зұ»дјјгҖӮеҶҚеҠ дёҠеҘіжҖ§зҡ„еғ§дҫЈиә«еҲҶеҗ‘жқҘдёҺе®—ж•ҷжңәжһ„з»ҙжҢҒиҫғжқҫж•Јзҡ„е…ізі»пјҢеҘіжҖ§еңЁе®¶дҝ®иЎҢжҲ–жҳҜйҡҗеұ…з§ҒдәәдҪӣе ӮпјҢиҖҢдёҚеҗ‘е®ҳж–№жіЁеҶҢжҲ–еҠ е…Ҙе®—жҙҫз»„з»ҮпјҢжҳҜзӣёеҪ“жҷ®йҒҚзҡ„зҺ°иұЎгҖӮж—ҘжҚ®ж—¶жңҹпјҢеҸ°ж№ҫдҪӣж•ҷеҜәйҷўеҗ‘е®ҳж–№жіЁеҶҢзҡ„иҸң姑е’Ңж–ӢеҸӢпјҢеёҰеҸ‘дҝ®иЎҢиҖҢдёҚеҗҢдәҺе°јеёҲпјҢеә”жҳҜSankarжүҖи°“еҜ„еұ…дҪӣеҜәзҡ„ж–Ӣ姑гҖӮжҲҳеҗҺеҲқжңҹеҸ°ж№ҫе°јеҜәгҖҒеІ©д»”д»Қ然收容иҝҷз§ҚеҜ„еұ…дҪӣж•ҷеҜәйҷўзҡ„ж–Ӣ姑пјҢдҪҶжҳҜеӨҡз§°д№Ӣдёәжё…дј—гҖӮеҘ№д»¬еҜ„д»ҳпјҲжҚҗзҢ®пјүдёҖ笔е®үеҚ•иҙ№еҗҺпјҢиҷҪ然еёҰеҸ‘дҝ—жңҚпјҢеҸҜд»ҘеңЁеҜәдёӯдә«жңүе’ҢеҮә家众зӣёеҗҢзҡ„еҫ…йҒҮпјҢдёҚдҪҶжңүиҮӘе·ұдё“еұһзҡ„еҜ®жҲҝпјҲе®ҝиҲҚпјүпјҢиҝҳеҸҜд»ҘиҮӘз”ұеҫҖжқҘеҜәйҷўдёҺдҝ—家пјҢ并且дҫқз»ҸжөҺиғҪеҠӣй«ҳдҪҺеңЁеҜәдёӯжӢ…д»»иҫғжё…й—Ізҡ„е·ҘдҪңпјҢжҲ–иҖ…е…ҚйҷӨдёҖеҲҮжқӮеҪ№гҖӮеҰӮжһңжҲ‘们дёҚе…ҲзҗҶжё…дј з»ҹеҘіжҖ§е®—ж•ҷи®ӨеҗҢзҡ„еј№жҖ§е’ҢеҸҜиҪ¬з§»жҖ§пјҢд»…д»Ҙе®—ж•ҷжҙҫеҲ«е’ҢеүғеәҰдёҺеҗҰжқҘеҢәеҲҶе°јдј—е’Ңж–Ӣ姑пјҢ并且жҺ’йҷӨйҡ¶еұһдәҺдҪӣж•ҷеҜәйҷўзҡ„иҸң姑пјҢеҚіжІҰе…Ҙд»ҘжҲҳеҗҺдёӯеӣҪжӯЈз»ҹж•ҷеӣўдё»д№үзҡ„еҸ—жҲ’ж ҮеҮҶе’ҢеҸІи§ӮжқҘжүӯжӣІж—ҘжҚ®ж—¶жңҹзҡ„еҺҶеҸІжғ…еўғпјҢиҖҢеҝҪз•ҘжҲҳеҗҺдј жҲ’еҜ№дәҺеҘіжҖ§ж•ҷеӣўиә«еҲҶдёҺдҝ®иЎҢж–№ејҸзҡ„еҪұе“ҚгҖӮ
гҖҖгҖҖеҸ°ж№ҫзҡ„жғ…еҶөжҜ”иҫғзү№ж®Ҡзҡ„жҳҜпјҢж—Ҙжң¬ж®–ж°‘ж”ҝеәңзҡ„е®—ж•ҷж”ҝзӯ–йҮҚж–°е®ҡдҪҚж–Ӣж•ҷпјҢеӣ иҖҢйҖ жҲҗж–Ӣ姑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е®ҳж–№жүҝи®ӨгҖҒеҸҜд»ҘдёҺдҪӣж•ҷе°јдј—е№ізӯүзҡ„е®—ж•ҷиә«еҲҶгҖӮдёӯеӣҪжңқе»·дёҖеҗ‘и§Ҷж–Ӣж•ҷдёәз§ҳеҜҶе®—ж•ҷпјҢжӯЈз»ҹзҡ„дҪӣж•ҷе®—жҙҫдәҰи§Ҷж–Ӣж•ҷдёәең°ж–№дёҠдёҖз§ҚеңЁе®¶дҪӣж•ҷзҡ„еҪўејҸгҖӮе®ҳж–№дёҺжӯЈз»ҹзҡ„еғ§еӣўдё»д№үеҜ№дәҺж–Ӣж•ҷжңҖж„ҹиҜҹз—…зҡ„жҳҜе…¶д»ҘвҖңеңЁе®¶дәәвҖқиә«еҲҶжӢ…д»»еғ§дҫЈзҡ„е·ҘдҪңпјҢдёҫеҠһеҗ„з§Қд»ӘејҸгҖӮдҪҶжҳҜж–Ӣж•ҷе…·жңүдёҘеҜҶзҡ„еҚҮиҝҒзӯүзә§е’Ңзӣёеә”зҡ„дҝ®иЎҢж–№ејҸпјҢйҷӨдәҶйҮ‘е№ўжҙҫе’ҢйҫҷеҚҺжҙҫзҡ„з”·жҖ§д»ӘиҪЁеёҲеҸҜд»Ҙз»“е©ҡд№ӢеӨ–пјҢ他们иҮӘе·ұе®ҡдҪҚдёә继жүҝзҰ…е®—е…ӯзҘ–ж…§иғҪд№ӢдҫӢпјҢеңЁдҝ—дё–д№ӢдёӯиҖҢйқһж•ҷеӣўд№ӢеҶ…дҝ®иЎҢпјҢжҜ”еғ§дҫЈпјҲз©әй—ЁпјүжӣҙиғҪе®һи·өзҰ…зҗҶгҖӮе°ұж•ҷд№үгҖҒз»„з»ҮгҖҒдҝ®иЎҢдҪҚйҳ¶еҗ„ж–№йқўиҖҢиЁҖпјҢж–Ӣж•ҷдёҚдҪҶд»ЈиЎЁжҳҺжё…д»ҘжқҘдҪӣж•ҷзҡ„ж–°е…ҙе®—жҙҫпјҢиҖҢдё”жүҖи°“зҡ„вҖңеңЁе®¶дҪӣж•ҷвҖқд№ҹ并йқһжҢҮдҝ—дәәдё»еҜјзҡ„дҪӣж•ҷпјҢиҖҢжҳҜдё–дҝ—зҡ„дҪӣж•ҷгҖӮж—Ҙжң¬ж®–ж°‘ж”ҝеәңиөӢдәҲж–Ӣж•ҷе®ҳж–№и®ӨеҸҜпјҢеҸҜ收дёҖзҹідёӨйёҹд№ӢеҲ©гҖӮдёҖж–№йқўпјҢеҮҖеңҹзңҹе®—зӯүж—Ҙжң¬дҪӣж•ҷе®—жҙҫзҡ„еғ§дҫЈд№ҹжҳҜеёҰзң·пјҢдёҺе…¶еҗҰи®Өж–Ӣж•ҷиҖҢеҮёжҳҫж—Ҙжң¬зҡ„еғ§дҫЈе©ҡ姻зҡ„еҗҲжі•жҖ§еҚҒеҲҶе”җзӘҒпјҢдёҚеҰӮжүҝи®Өж–Ӣж•ҷйўҶиў–зұ»дјјеғ§дҫЈзҡ„иә«еҲҶпјҢжӢүиҝ‘еҪјжӯӨзҡ„е·®и·қпјҢиҝӣиҖҢеҗёж”¶ж–Ӣж•ҷеҫ’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ж—Ҙжң¬е°Ҷж–Ӣж•ҷеҪ’зұ»дёәеҸ°ж№ҫдҪӣж•ҷзҡ„иҢғз•ҙпјҢеҖҫеҗ‘д»Ҙжҡ§жҳ§зҡ„еғ§дҝ—з•ҢйҷҗжқҘиҙ¬дҪҺеҸ°ж№ҫдҪӣж•ҷзҡ„дёҚзәҜзІ№жҖ§гҖӮ
гҖҖгҖҖж—Ҙжң¬е®—ж•ҷж”ҝзӯ–зҡ„ж®–ж°‘еҝғжҖҒпјҢеңЁжЁЎзіҠеҢ–ж–Ӣ姑е’ҢдҪӣж•ҷе°јдј—зҡ„иә«еҲҶи®ӨеҗҢдёҠпјҢжңҖдёәжё…жҘҡгҖӮдёёдә•еңӯжІ»йғҺжӣҫд»Ҙж–°з«№еҮҖдёҡйҷўдёәдҫӢпјҢжҢҮеҮәеҸ°ж№ҫе°јдј—дёҚдјјж—Ҙжң¬е°јеғ§пјҢеҸҚиҖҢиҫғеғҸж–Ӣ姑гҖӮеҮҖдёҡйҷўдёәж–°з«№йғ‘ж°Ҹдё–ж—ҸжүҖе»әд№Ӣ家йҷўпјҢеҺҹжң¬дёәе…¶дё»жҜҚйҷҲж°ҸзҘҲжұӮеӯҗе—ЈиҖҢе»әпјҢеҗҺжқҘ收养дёӨдҪҚе°јдј—жқҘз»ҸиҗҘпјҢйҒӮжҲҗдёәйғ‘家еҘізң·дҝ®иЎҢгҖҒжёЎеҒҮзҡ„ең°ж–№гҖӮ笔иҖ…1997дәҺе№ҙеӨҸеӨ©иө°и®ҝж–°з«№еҮҖдёҡйҷўпјҢи®ҝи°Ҳ第дёүд»ЈпјҲйқһ第дёүдҪҚпјүдҪҸжҢҒж…Ҳеҝғжі•еёҲеҗҺеҸ‘зҺ°пјҢж—ҘжҚ®ж—¶жңҹеҸ°ж№ҫе°јдј—еӨҡж•°дёҚжӣҫеүғеәҰеңҶйЎ¶пјҢжҳҜйҖ жҲҗдёёдә•зҡ„иҜ„д»·зҡ„е…ій”®еӣ зҙ гҖӮж…Ҳеҝғжі•еёҲдёүеІҒеҚідёәеҮҖдёҡйҷўжүҖ收养пјҢиҮӘе№јдәҺеҮҖдёҡйҷўдёҺйғ‘家еӯҗеҘідёҖиө·й•ҝеӨ§гҖӮеҘ№еӣһйЎҫе…¶е№јж—¶з”ҹжҙ»ж—¶жҢҮеҮәпјҢе…¶еёҲзҘ–жҳҜеҪ“ж—¶еҮҖдёҡйҷўеҶ…е”ҜдёҖиҗҪеҸ‘зҡ„е°јдј—пјҢиҝҷжҳҜеӣ дёәеҘ№еҸ—ж—Ҙжң¬дҪӣж•ҷж•ҷиӮІзҡ„зјҳж•…гҖӮ
гҖҖгҖҖж…ҲеҝғеҚҒеҲҶиҒӘйў–ж•ҸжҚ·пјҢеӣ жӯӨе…¶еёҲзҘ–еёҢжңӣеҘ№д№ҹиҗҪеҸ‘пјҢ继жүҝе…¶иЎЈй’өгҖӮ12еІҒзҡ„ж…ҲеҝғеҚҙжҢҮзқҖе ӮдёҠдҫӣеҘүзҡ„и§Ӯдё–йҹіиҸ©иҗЁиҜҙвҖңиҝһеҘ№йғҪжңүеӨҙеҸ‘пјҢжҲ‘дёҚеүғгҖӮвҖқдҪҶжҳҜж…Ҳеҝғе…¬еӯҰж ЎпјҲзӣёеҪ“дәҺзҺ°еңЁзҡ„еӣҪж°‘е°ҸеӯҰпјүжҜ•дёҡеҗҺйўҶжӮҹеҲ°пјҢеҲ°ж—Ҙжң¬иҜ»е°јдј—еӯҰж ЎжҳҜеҘ№е”ҜдёҖ继з»ӯжұӮеӯҰзҡ„жңәдјҡгҖӮиҖҢж №жҚ®ж—Ҙжң¬дҪӣж•ҷеӯҰж Ўзҡ„规е®ҡпјҢж…Ҳеҝғеҝ…йЎ»еүғеәҰгҖӮз»“жһңж…ҲеҝғеңҶйЎ¶пјҢиҖҢз”ұйғ‘家жҸҗдҫӣеҘ№еңЁж—Ҙжң¬зҡ„еӯҰе®ҝиҙ№гҖӮж…Ҳеҝғ并且еҗ‘еҘ№зҡ„еёҲзҘ–з«Ӣеҝ—е°ҶжқҘеӯҰжҲҗеҪ’жқҘпјҢиҰҒеҪ“еёғж•ҷеёҲпјҢе…үиҖҖй—ЁжҘЈгҖӮж…Ҳеҝғ并且жҠұжҖЁпјҢиҷҪ然ж—Ҙжң¬еңЁеҸ°еғ§еҗ‘жқҘдёҺйғ‘家дҝқжҢҒиүҜеҘҪе…ізі»пјҢеҸҜжҳҜ他们йқһеёёеҗқдәҺжҸҗдҫӣеҸ°ж№ҫе°јдј—еҲ°ж—Ҙжң¬иҝӣдҝ®зҡ„иө„ж–ҷпјҢеҮ д№ҺдёҖй—®дёүдёҚзҹҘпјҢзӣҙеҲ°ж…ҲеҝғдёҖеҲҮе°ұз»ӘпјҢзҰ»еҸ°зҡ„еүҚеӨ•жүҚеҸ‘зҺ°пјҢиҝҷдәӣж—Ҙжң¬еғ§дәәе…¶е®һйқһеёёзҶҹиҜҶж—Ҙжң¬дҪӣж•ҷеӯҰж Ўзҡ„жғ…еҪўгҖӮ
гҖҖгҖҖж—Ҙжң¬еңЁеҸ°еғ§дҫЈе№¶дёҚйј“еҠұеҸ°ж№ҫе°јдј—еүғеәҰпјҢдәҰеҸҜд»Ҙд»Һ他们жүҖи®ҫзҡ„еҮә家尼众и®ӯз»ғзҸӯеҫ—зҹҘгҖӮж—ҘжҚ®ж—¶жңҹеҹәйҡҶең°еҢәеҘіжҖ§ж¬ІеҸ–еҫ—еҮә家иә«еҲҶпјҢеҝ…йЎ»еңЁжӯӨи®ӯз»ғзҸӯйҖҡиҝҮдёӨе№ҙиҜҫзЁӢгҖӮдҪҶжҳҜеңЁз»“дёҡе…ёзӨјзҡ„зӣёзүҮдёҠпјҢжқҘиҮӘеҗҢдёҖеҜәйҷўзҡ„еҘіеӯҰз”ҹдёҚдёҖе®ҡйғҪиҗҪеҸ‘гҖӮеҗҢж ·зҡ„жғ…еҪўдәҰеҸ‘з”ҹеңЁдёңжө·е®ңиҜҡе’ҢеӨ§еІ—еұұжҙҫжўҒејҖеҗүдҪҸжҢҒеҗҲдҪңпјҢ1941е№ҙдәҺиҺІеі°еҜәдёҫеҠһвҖңе°јеғ§и®Ід№ дјҡвҖқгҖӮз»“дёҡе…ёзӨјдёҠпјҢеӨҡж•°еҸ°ж№ҫи“„еҸ‘зҡ„еҘіеӯҰе‘ҳе’Ңж—Ҙжң¬е°јж•ҷеёҲзҡ„еңҶйЎ¶жҒ°жҲҗеҜ№жҜ”гҖӮ
гҖҖгҖҖдёңжө·е®ңиҜҡз§°иөһеӨ§еІ—еұұжҙҫзҡ„йҫҷж№–еәөдёәеҸ°ж№ҫжңҖеӨ§гҖҒжңҖжңү规模зҡ„вҖңе°јдј—йҒ“еңәвҖқпјҢеӣ жӯӨиҜ·дёңжө·жҳҢйҒ“гҖҒжіҪжң¬ејҳйҒ“дёӨдҪҚж—Ҙжң¬е°јдј—дёәж•ҷеёҲпјҢе°ұиҺІеі°еҜәпјҲдҪҚдәҺж—§и¶…еі°еҜәе’Ңйҫҷж№–еәөд№Ӣй—ҙпјүй’ҲеҜ№еҸ°ж№ҫеҘіжҖ§жҺЁиЎҢж—Ҙжң¬дҪӣж•ҷж•ҷиӮІгҖӮж №жҚ®жұҹзҒҝи…ҫзҝ»иҜ‘еҮәеҪ“е№ҙгҖҠеҸ°ж№ҫдҪӣж•ҷгҖӢзҡ„ж–°й—»пјҢжӯӨж¬Ўи®Ід№ дјҡзҡ„еӯҰе‘ҳдёәвҖңдё»иҰҒжҳҜеҸ°ж№ҫеҚ—йғЁзҡ„еҘідј—гҖҒеғ§е°јпјҲе°јеғ§пјүгҖҒж–Ӣ姑пјҢе…¬еӯҰж ЎжҜ•дёҡд»ҘдёҠзҡ„зЁӢеәҰпјҢжңүиҝҗз”Ёж—ҘиҜӯзҡ„иғҪеҠӣпјҢз»Ҹз”ұеҪ“ең°еҜәйҷўзҡ„жҺЁиҚҗпјҢеҸӮдёҺи®Ід№ иҖ…дәҢеҚҒеҗҚвҖқгҖӮиҷҪ然笔иҖ…е№¶ж— иҝҷ20еҗҚеӯҰе‘ҳзҡ„ж•°жҚ®пјҢдҪҶжҳҜеҘ№д»¬еҶіеӨҡж•°жҳҜйҫҷж№–еәөзӯүеӨ§еІ—еұұжҙҫзҡ„еҘіжҖ§жҲҗе‘ҳпјҢеӣ дёәж•ҙдёӘжҙ»еҠЁжҳҜз”ұеӨ§еІ—еұұиөһеҠ©пјҢ并且з”ұвҖңеҪ“ең°еҜәйҷўвҖқзӯӣйҖүеӯҰе‘ҳиө„ж јзҡ„гҖӮиҷҪ然ж—Ҙжң¬еғ§е°јзӣӣиӘүйҫҷж№–еәөдёәеҸ°ж№ҫж•°дёҖж•°дәҢзҡ„е°јдј—йҒ“еңәпјҢдҪҶжҳҜдәҰжңӘиҰҒжұӮиҝҷдәӣеҘіеӯҰе‘ҳеүғеҸ‘пјҢиҖҢйҫҷж№–еәөеҶ…зҡ„е°јдј—д№ҹеӨҡж•°еёҰеҸ‘дҝ®иЎҢгҖӮ
гҖҖгҖҖ既然йҫҷж№–еәөдёәжқҘиҮӘеҸ°еҚ—ејҖе…ғеҜәзҡ„ж°ёе®ҡе’Ңе°ҡ(1877-1939)жүҖе»әпјҢ1920е№ҙиҝҳиҒҳиҜ·еӨ§йҷҶеҚ—жҷ®йҷҖеҜәдҪҸжҢҒдјҡжіүе’Ңе°ҡ(1874-1943)жқҘеҸ°жҺҲвҖңеңЁе®¶иҸ©иҗЁжҲ’вҖқпјҢйҫҷж№–еәөзҡ„жҲҗе‘ҳжң¬иә«зҡ„е®ҡдҪҚеә”жҳҜе°јдј—пјҢд»ҘеҸҠзҡҲдҫқдҪӣж•ҷзҡ„иҸң姑пјҢиҖҢйқһж–Ӣж•ҷзҡ„ж–Ӣ姑гҖӮдҪ•еҶөеӨ§йҷҶеғ§дәәжһ—ж…§дә‘дёәйҫҷж№–еәөжүҖж’°зҡ„дёҮе№ҙз°ҝеәҸпјҢз§°д№ӢдёәвҖңе°јдј—жё…дҝ®йҒ“еңәвҖқгҖӮеҗҢе№ҙ(1936)пјҢеҚҸеҠ©дёңжө·е®ңиҜҡжҺЁе№ҝж”№йқ©ж—§жғҜдҪӣж•ҷеҜәйҷўиҝҗеҠЁзҡ„ејҖе…ғеҜәй«ҳжү§еҫ·е’Ңе°ҡ(1986-1955)дәҰи°“йҫҷж№–еәөдёәвҖңи‘—еҗҚе°јеҜәвҖқгҖӮйҫҷж№–еәө并дёҚеӣ е…¶дҪҸдј—еёҰеҸ‘дҝ®иЎҢиҖҢиў«еҪ“ж—¶дҪӣж•ҷз•ҢеҲҶзұ»дёәж–Ӣе ӮгҖӮдҪҶжҳҜж—Ҙжң¬еғ§е°јеҹәдәҺвҖңе°ҠйҮҚвҖқеҸ°ж№ҫж—§жғҜзҡ„з«ӢеңәпјҢ并дёҚиҰҒжұӮеҸ°ж№ҫе°јдј—еүғеҸ‘пјҢеҸӘжңүиғҪеӨҹз•ҷеӯҰж—Ҙжң¬гҖҒзңҹжӯЈиҝӣе…Ҙж—Ҙжң¬дҪӣж•ҷзі»з»ҹзҡ„еҸ°ж№ҫе°јдј—жүҚеңҶйЎ¶пјҢеҫ—еҲ°е°јеғ§зҡ„ең°дҪҚгҖӮеҸҜи§Ғе°јдј—зҡ„еӨҙеҸ‘жҳҜеҰӮдҪ•жҲҗдёәж®–ж°‘иҖ…жҳҫзӨәе…¶е®—ж•ҷдјҳдәҺиў«ж®–ж°‘иҖ…зҡ„иұЎеҫҒгҖӮ
гҖҖгҖҖж•ҙдҪ“иҖҢиЁҖпјҢж—ҘжҚ®ж—¶жңҹеҸ°ж№ҫе°јдј—еҮә家иҗҪеҸ‘并дёҚжҷ®йҒҚпјҢе°ұеғҸеҘ№д»¬еҸ—еӨ§жҲ’дёҖж ·йҡҫеҫ—гҖӮеҸ°ж№ҫз”ұдәҺдҪҚеӨ„иҫ№йҷІең°еҢәпјҢе№¶ж— е®ҳж–№жҲ–еӨ§е®—жҙҫдёӣжһ—зҡ„жҲ’еқӣпјҢеӣ жӯӨеҸ°ж№ҫеғ§е°јж¬ІеҸ—е…·и¶іжҲ’иҖ…пјҢеҝ…йЎ»жёЎиҝҮеҸ°ж№ҫжө·еіЎеҺ»зҰҸе»әзӯүең°еҸ—жҲ’гҖӮйҷӨдәҶиҖғиҷ‘еҘіжҖ§иҝңжёёзҡ„е®үе…Ёй—®йўҳд№ӢеӨ–пјҢеәһеӨ§зҡ„ж—…иҙ№е’ҢжҳӮиҙөзҡ„жҲ’еңәиҙ№з”ЁпјҲйҖҡеёёиҝҳеҢ…еҗ«и°ўеёҲгҖҒеҸӮи®ҝгҖҒжёёеӯҰзӯүиҠұиҙ№пјүпјҢд№ҹдҪҝеҫ—еҸ°ж№ҫеҜәйҷўеҒҸеҗ‘йҖүжҙҫеғ§дј—вҖ”вҖ”зү№еҲ«жҳҜдҪҸжҢҒ继жүҝдәәйҖүвҖ”вҖ”еҺ»еӨ§йҷҶеҸ—жҲ’гҖӮзҺҜеўғжҜ”иҫғдјҳи¶Ҡзҡ„е°јдј—пјҢиҝҳеҸҜд»Ҙд»ҘеҜ„жҲ’зҡ„ж–№ејҸпјҢйӮ®еҜ„иҫғе°‘зҡ„еҸ—жҲ’иҙ№з”ЁеҲ°жҲ’еқӣпјҢд№°еҲ°жҲ’зўҹгҖӮеңЁдәәжңӘеҮәеёӯ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иҝҷдәӣе°јдј—д№ҹдёҚйңҖиҗҪеҸ‘гҖӮеҘ№д»¬жҲ–жҳҜе°ҶеӨҙеҸ‘жүҺжҲҗдёӨжқЎеҸ‘иҫ«пјҢжҳҫзӨәеҘ№д»¬зҡ„еӨ„еҘіиә«еҲҶпјӣжҲ–жҳҜйҪҗиҖіеүӘеҺ»пјҢиЎЁзӨәиҮӘе·ұзҡ„е…ҲиҝӣпјӣжҲ–жҳҜеҰӮж–Ӣ姑дёҖж ·зӣҳжҲҗе·Іе©ҡеҰҮеҘізҡ„еҸ‘й«»пјҢд»ҘжҳҺеҝ—дёҚе«Ғе®ҲиҙһгҖӮж—ҘжҚ®ж—¶жңҹеҸ°ж№ҫе°јдј—еӨҡдәҶеҲ°ж—Ҙжң¬жұӮеӯҰеҸ–еҫ—е°јеғ§иө„ж јзҡ„жңәдјҡпјҢдҪҶжҳҜиҝҷд»…еұҖйҷҗдәҺ少数家еўғдјҳи¶ҠгҖҒжҲҗз»©дјҳз§Җзҡ„е°јдј—гҖӮеӣ жӯӨж—ҘжҚ®ж—¶жңҹиғҪеӨҹеүғеҸ‘зҡ„е°јдј—пјҢд»ҚеңЁе°‘ж•°гҖӮеңЁиҝҷз§Қжғ…еҶөд№ӢдёӢпјҢеҸ°ж№ҫе°јдј—з•ҷеҸ‘пјҢдёҚд»…жҳҫзӨәеҘіжҖ§е’Ңе®ҳж–№д»ҘеҸҠе®—жҙҫжҺҲжҲ’еҲ¶еәҰзҡ„з–Ҹиҝңе…ізі»пјҢд№ҹе‘ҲзҺ°еҘ№д»¬еҰӮдҪ•з”ЁеҸ‘еһӢпјҲиҖҢйқһеүғеҸ‘пјүжқҘиЎЁиҫҫиҮӘе·ұзҡ„е®—ж•ҷиә«еҲҶгҖӮ
гҖҖгҖҖеҚідҪҝ1953е№ҙд»ҘеҗҺпјҢеҸ°ж№ҫеҮ д№Һе№ҙе№ҙејҖжҲ’еқӣпјҢдҪҶжҳҜж—©жңҹд»Қжңүи®ёеӨҡе°јдј—ж— жі•иҙҹжӢ…жҲ’дјҡзҡ„еҝҸж‘©гҖҒи¶…еәҰзҘ–е…ҲгҖҒдҫӣеғ§и°ўеёҲзӯүиҙ№з”ЁгҖӮзҺ°еңЁ70еІҒд»ҘдёҠзҡ„е°јдј—пјҢиҝҳжңүдәәеӣһйЎҫеҲ°еҪ“еҲқжӢҺзқҖе°ҸеҢ…иўұпјҢзһ’зқҖзҲ¶жҜҚд»“дҝғйҖғ家еҺ»еҗғиҸңзҡ„жғ…еҪўгҖӮеҪ“ж—¶еҜәйҷўз»ҸжөҺжғ…еҶөдёҚеғҸзҺ°еңЁеҰӮжӯӨеҜҢиЈ•пјҢеҘ№д»¬еёёеёёиҰҒзӯүдёҠеҘҪеҮ е№ҙпјҢжүҚзӯ№жҺӘеҲ°дёҖеҘ—еғ§иЎЈпјҢжҲ–иҖ…з»ҲдәҺеҫ—еҲ°еҸ—жҲ’зҡ„жңәдјҡпјҢеӣ жӯӨеҮә家并йқһ马дёҠдёҖе®ҡеңҶйЎ¶гҖӮиҝҳжңүдәӣе№ҙиҪ»жңӘе©ҡеҘіжҖ§з»Ҹеёёз»“дјҙеҲ°еҗ„еәөе ӮеҜәйҷўжёёзҺ©пјҢж—¶ж—Ҙй•ҝдәҶпјҢдҫҝеҗ„иҮӘзҡҲдҫқдёҚеҗҢзҡ„еҜәйҷўеәөе ӮпјҢжёҗжёҗеҫ…еңЁеҜәйҷўеәөе ӮйҮҢеё®еҝҷгҖӮз”ұдәҺжқҘеҫҖзҡ„йғҪжҳҜеҘіжҖ§е’Ңе°јдј—пјҢеҘ№д»¬зҡ„зҲ¶жҜҚжҜ”иҫғе®№и®ёеҘ№д»¬еҰӮжӯӨдә«еҸ—дёҖдёӢе№ҙиҪ»зҡ„з”ҹжҙ»гҖӮиҝҷдәӣе№ҙиҪ»еҘіжҖ§йҖҡеёёд№ҹдёҚз«ӢеҲ»иҗҪеҸ‘пјҢжңүзҡ„дәәз”ҡиҮідёҖдҪҸеҜәйҷўеҚҒе№ҙжүҚеңҶйЎ¶пјҢдёәзҡ„д№ҹжҳҜе®үжҠҡзҲ¶жҜҚдәІпјҢеҮҸе°‘жқҘиҮӘ家еәӯзҡ„йҳ»еҠӣгҖӮзӣёеҜ№зҡ„пјҢеӣ дёәжңӘжӣҫиҗҪеҸ‘пјҢдёҮдёҖз”ҹеҫ’ж— жі•йҖӮеә”еҜәйҷўз”ҹжҙ»пјҢиҝҳдҝ—е®№жҳ“пјҢеҜәж–№д№ҹеҸҜд»ҘйҒҝе…Қи®ёеӨҡйә»зғҰгҖӮ
гҖҖгҖҖ笔иҖ…еңЁеұҸдёңд№ҹеҸ‘зҺ°жҲҳеҗҺд»Қжңүе°јеҜә收养еӯӨе„ҝпјҢд»Ҙдҫҝж—ҘеҗҺ继жүҝиЎЈй’өзҡ„жғ…еҶөгҖӮиҝҷдәӣе°јеҜәиҷҪ然дёҚеғҸж—ҘжҚ®ж—¶жңҹйғ‘家зҡ„еҮҖдёҡйҷўдёҖж ·еҜҢжңүпјҢеҸҜд»Ҙж Ҫеҹ№е…»еҘіз•ҷеӯҰпјҢдҪҶжҳҜеҘ№д»¬д№ҹеҖҫеҗ‘дәҺи®©иҝҷдәӣе…»еҘіеёҰеҸ‘дҝ®иЎҢпјҢзӣҙеҲ°жёЎиҝҮйқ’жҳҘжңҹжүҚиҖғиҷ‘и®©еҘ№д»¬жӯЈејҸеңҶйЎ¶гҖӮз”ұдәҺд»ҘеүҚж°‘йЈҺжҜ”иҫғдҝқе®ҲпјҢдёҚеғҸзҺ°еңЁи®ёеӨҡеғ§е°јиҝӣе…ҘеӨ§дё“йҷўж Ўж•ҷд№Ұе’ҢжұӮеӯҰпјҢдҪҸжҢҒиЎЁзӨәи®©иҝҷдәӣе…»еҘіз•ҷеҸ‘д»ҘдҫҝеӨ–еҮәжҺҘеҸ—дёҖиҲ¬ж•ҷиӮІпјҢиҝҳжҳҜжҜ”иҫғж–№дҫҝзҡ„еҒҡжі•гҖӮ
гҖҖгҖҖдёҠиҝ°иҝҷдәӣеҸ°ж№ҫе°јдј—еҜ№еҫ…еӨҙеҸ‘зҡ„жҖҒеәҰжҳҫзӨәпјҢеҘ№д»¬йқһеёёжё…жҘҡеӨҙеҸ‘жүҖд»ЈиЎЁзҡ„жҖ§еҲ«ж„Ҹж¶өпјҢд»ҘеҸҠиҗҪеҸ‘жүҖд»ЈиЎЁејғз»қдё–дҝ—иә«еҲҶзҡ„дёҘйҮҚжҖ§гҖӮдҪҶжҳҜиҮӘд»ҺжҲҳеҗҺдёӯеӣҪдҪӣж•ҷдјҡдәҺеҸ°ж№ҫе»әз«Ӣдј жҲ’еҲ¶еәҰгҖҒйҮҚжҢҜдёӯеӣҪзҰҒж¬Ізҡ„ж•ҷеӣўз”ҹжҙ»ж–№ејҸд»ҘжқҘпјҢеҸ°ж№ҫе°јдј—еңҶйЎ¶дёҺеҗҰпјҢ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еҫҲйҮҚиҰҒзҡ„жҢҮж ҮпјҢиў«з”ЁжқҘиЎЎйҮҸеҸ°ж№ҫдҪӣж•ҷзҡ„жӯЈз»ҹжҖ§е’ҢзҺ°д»ЈеҢ–гҖӮдёҖж–№йқўпјҢдёӯеӣҪдҪӣж•ҷдјҡе®Јз§°ж–Ӣ姑иёҠи·ғеүғеәҰеҸ—жҲ’зҡ„жғ…еҶөпјҢдёәвҖңеҮҖеҢ–вҖқеҸ°ж№ҫдҪӣж•ҷеҸ—ж—Ҙжң¬дҪӣж•ҷеҪұе“Қзҡ„йғЁд»ҪгҖӮиҖҢдёҺдј жҲ’еҲ¶еәҰзӣёиҫ…зӣёжҲҗзҡ„еғ§дҫЈж•ҷиӮІпјҢдёӨиҖ…йғҪејәи°ғз»Ҹе…ёе®һи·өжҲ’еҫӢзҡ„ж–№ејҸпјҢиҝӣиҖҢеј•д»ӢеҸ°ж№ҫеҘіжҖ§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жӯЈз»ҹеҢ–зҡ„е®—ж•ҷиә«еҲҶе’Ңеғ§дҫЈи®ӯз»ғпјҢиөӢдәҲеүғеәҰеҸ—жҲ’ж–°зҡ„еҺҶеҸІж„Ҹж¶ө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йҖҸиҝҮеңҶйЎ¶пјҢдј жҲ’еҲ¶еәҰејәеҢ–еғ§дҝ—з•ҢйҷҗпјҢеҜ№д»ҘеҫҖзӣӣиЎҢзҡ„ж–Ӣ姑е’Ңе…¶е®ғиҝҮжёЎеҪўејҸзҡ„еҘіжҖ§е®—ж•ҷз”ҹжҙ»ж–№ејҸдә§з”ҹжҺ’жҢӨжҖ§гҖӮеҢәеҹҹжҖ§дҪӣж•ҷе®һи·өж–№ејҸзҡ„е·®ејӮпјҢд№ҹйҖҸиҝҮе°ҶеҘіжҖ§зәіе…ҘжӯЈи§„зҡ„ж•ҷеӣўеҗҜи’ҷиҝҮзЁӢпјҢиҖҢйҮҚж–°ж•ҙеҗҲгҖӮж–Ӣж•ҷзҡ„д»ӘејҸ专家е’ҢеҸ°ж№ҫзҡ„ж—ҘејҸеғ§дҫЈеӨұеҺ»е…¶е®—ж•ҷеҗҲжі•жҖ§гҖӮиҝҷз§ҚеӨҚжқӮзҡ„иҝҮзЁӢдә§з”ҹдёҖдёӘй«ҳеәҰеҲ¶еәҰеҢ–е’Ңж ҮеҮҶеҢ–зҡ„еҘіжҖ§еғ§дҫЈз”ҹж¶ҜгҖӮжҲҳеүҚжҲҳеҗҺеҸ°ж№ҫдҪӣж•ҷеҘіжҖ§дҝ®иЎҢиҖ…жүҖжҺҲжҲ’еҲ«зҡ„е·®ејӮпјҢдёҖиҲ¬иҖҢиЁҖпјҢе°јдј—жң¬иә«жҜ”дёҖиҲ¬ж°‘дј—зҡ„ж„ҹеҸ—иҰҒејәгҖӮиҖҢдёҖиҲ¬ж°‘дј—жүҖдҪ“дјҡеҲ°зҡ„пјҢеҸҜиғҪиҝҳдёҚжҳҜе°јдј—еҸ‘еһӢж”№еҸҳзҡ„е®—ж•ҷж„Ҹд№үпјҢиҖҢжҳҜеүғеәҰжүҖеёҰжқҘзҡ„йңҮж’ј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еӣһйЎҫжҲҳеүҚжҲҳеҗҺеҸ°ж№ҫе°јдј—зҡ„еҸ‘еһӢж—¶пјҢеҗҠиҜЎзҡ„жҳҜпјҢе®—ж•ҷеҘіжҖ§и¶Ҡи®ҫжі•дҝқз•ҷеҘ№д»¬зҡ„еӨҙеҸ‘пјҢд»Ҙе…ҚзӣҙжҺҘеҶІеҮ»зҲ¶зі»зҡ„жҖ§еҲ«д»·еҖјзі»з»ҹж—¶пјҢеҘ№д»¬и¶Ҡиў«зӨҫдјҡжҺ’йҷӨеңЁеӨ–гҖӮеӣ дёәеҘ№д»¬зҡ„е®—ж•ҷи§’иүІпјҢеҹәжң¬дёҠжҸҗдҫӣзҲ¶зі»зӨҫдјҡдёҖдёӘе®үзҪ®ж— жі•еҲҶзұ»еҘіжҖ§зҡ„дҫҝе®ңиЎҢдәӢгҖӮиҖҢеҪ“е°јдј—з»ҲдәҺеңҶйЎ¶пјҢжӯЈејҸе®Је‘ҠдёҺдё–дҝ—зҡ„иә«еҲҶеҲҶиЈӮж—¶пјҢеҘ№д»¬еҸҚиҖҢеҖҹйҮҚе®—ж•ҷзҡ„еҲ¶еәҰеҢ–зӢ¬з«ӢпјҢеҫ—д»Ҙе°Ҷе…¶е®—ж•ҷз”ҹжҙ»з”ұз§Ғдәәзҡ„йўҶеҹҹжҸҗеҚҮеҲ°е…¬зҡ„йўҶеҹҹгҖӮ
гҖҖгҖҖз»“и®әпјҡд»ҺеҮәдё–еҲ°е…Ҙдё–
гҖҖгҖҖжҲҳеҗҺеҸ°ж№ҫеҘіеӨ§еӯҰз”ҹйӣҶдҪ“еүғеәҰзҡ„зҺ°иұЎпјҢд»ҘеҸҠеҸ°ж№ҫдҪӣж•ҷдёҫдё–й—»еҗҚзҡ„еӯҰеЈ«е°јзү№еҫҒпјҢйғҪеҸҚжҳ еҘіжҖ§еғ§дҫЈз”ҹж¶Ҝзҡ„еҸҳиҝҒгҖӮдёҖдёӘжӯЈз»ҹзҡ„гҖҒдё“дёҡзҡ„гҖҒзҺ°д»Јзҡ„еҘіжҖ§еғ§дҫЈз”ҹж¶ҜйҡҸзқҖдј жҲ’еҲ¶еәҰдёҺеғ§дҫЈж•ҷиӮІзҡ„жҷ®еҸҠпјҢе·Із»ҸеҪўжҲҗгҖӮиҖҢй«ҳеӯҰеҺҶзҡ„еҘіжҖ§иө°е…ҘдҪӣй—ЁпјҢеҲҷжӣҙеҠ йҖҹжӯӨдёҖжӯЈз»ҹж•ҷеӣўиә«еҲҶзҡ„дё“дёҡеҢ–д»ҘеҸҠзӨҫдјҡеҸӮдёҺзЁӢеәҰгҖӮдёӨиҖ…дә’дёәеӣ жһңгҖӮеңЁзӨҫдјҡеұӮйқўдёҠпјҢиҝҷдәӣе®—ж•ҷеҘіжҖ§зҡ„ж•ҷеӣўиә«еҲҶж”№еҸҳпјҢеӣ дёәж¶үеҸҠдј з»ҹе®—ж•ҷз”ҹжҙ»дёҺ家еәӯд»·еҖјзҡ„еҶІзӘҒпјҢдёҚдҪҶеҸҚжҳ еҘіжҖ§е®—ж•ҷиә«еҲҶзҡ„и®Өе®ҡе’Ңе®—ж•ҷзҡ„з”ҹжҙ»ж–№ејҸеҰӮдҪ•жҒҜжҒҜзӣёе…іпјҢиҖҢдё”д№ҹжҳҫзӨәдёҖиҲ¬зӨҫдјҡеӨ§дј—зҡ„е®—ж•ҷжҰӮеҝөеҰӮдҪ•еңЁжҖҘйҖҹеҸҳиҝҒдёӯпјҢеҰӮдҪ•зүөеҠЁе®¶еәӯдјҰзҗҶгҖҒжҖ§еҲ«з•ҢйҷҗгҖҒе®—ж•ҷе®һи·өзӯүж·ұеұӮзҡ„ж–ҮеҢ–жҰӮеҝөгҖӮ
гҖҖгҖҖ笔иҖ…и®ӨдёәSankar еңЁйҰҷжёҜеҸ‘зҺ°зҡ„ж–Ӣ姑еұ…дҪҸдҪӣж•ҷеҜәйҷўзҡ„жғ…еҶөпјҢдәҰйҖӮз”ЁдәҺи§ЈйҮҠеҸ°ж№ҫзҡ„зҺ°иұЎгҖӮе°ұе®—ж•ҷз”ҹжҖҒиҖҢиЁҖпјҢеҸ°ж№ҫеҰҮеҘізҡ„е®—ж•ҷз”ҹжҙ»пјҢеҹәжң¬дёҠдәҰе’Ңй—ҪеҚ—гҖҒе№ҝдёңзҡ„и§ӮйҹідҝЎд»°зӣёеҪ“зұ»дјјгҖӮеҶҚеҠ дёҠеҘіжҖ§зҡ„еғ§дҫЈиә«еҲҶеҗ‘жқҘдёҺе®—ж•ҷжңәжһ„з»ҙжҢҒиҫғжқҫж•Јзҡ„е…ізі»пјҢеҘіжҖ§еңЁе®¶дҝ®иЎҢжҲ–жҳҜйҡҗеұ…з§ҒдәәдҪӣе ӮпјҢиҖҢдёҚеҗ‘е®ҳж–№жіЁеҶҢжҲ–еҠ е…Ҙе®—жҙҫз»„з»ҮпјҢжҳҜзӣёеҪ“жҷ®йҒҚзҡ„зҺ°иұЎгҖӮж—ҘжҚ®ж—¶жңҹпјҢеҸ°ж№ҫдҪӣж•ҷеҜәйҷўеҗ‘е®ҳж–№жіЁеҶҢзҡ„иҸң姑е’Ңж–ӢеҸӢпјҢеёҰеҸ‘дҝ®иЎҢиҖҢдёҚеҗҢдәҺе°јеёҲпјҢеә”жҳҜSankarжүҖи°“еҜ„еұ…дҪӣеҜәзҡ„ж–Ӣ姑гҖӮжҲҳеҗҺеҲқжңҹеҸ°ж№ҫе°јеҜәгҖҒеІ©д»”д»Қ然收容иҝҷз§ҚеҜ„еұ…дҪӣж•ҷеҜәйҷўзҡ„ж–Ӣ姑пјҢдҪҶжҳҜеӨҡз§°д№Ӣдёәжё…дј—гҖӮеҘ№д»¬еҜ„д»ҳпјҲжҚҗзҢ®пјүдёҖ笔е®үеҚ•иҙ№еҗҺпјҢиҷҪ然еёҰеҸ‘дҝ—жңҚпјҢеҸҜд»ҘеңЁеҜәдёӯдә«жңүе’ҢеҮә家众зӣёеҗҢзҡ„еҫ…йҒҮпјҢдёҚдҪҶжңүиҮӘе·ұдё“еұһзҡ„еҜ®жҲҝпјҲе®ҝиҲҚпјүпјҢиҝҳеҸҜд»ҘиҮӘз”ұеҫҖжқҘеҜәйҷўдёҺдҝ—家пјҢ并且дҫқз»ҸжөҺиғҪеҠӣй«ҳдҪҺеңЁеҜәдёӯжӢ…д»»иҫғжё…й—Ізҡ„е·ҘдҪңпјҢжҲ–иҖ…е…ҚйҷӨдёҖеҲҮжқӮеҪ№гҖӮеҰӮжһңжҲ‘们дёҚе…ҲзҗҶжё…дј з»ҹеҘіжҖ§е®—ж•ҷи®ӨеҗҢзҡ„еј№жҖ§е’ҢеҸҜиҪ¬з§»жҖ§пјҢд»…д»Ҙе®—ж•ҷжҙҫеҲ«е’ҢеүғеәҰдёҺеҗҰжқҘеҢәеҲҶе°јдј—е’Ңж–Ӣ姑пјҢ并且жҺ’йҷӨйҡ¶еұһдәҺдҪӣж•ҷеҜәйҷўзҡ„иҸң姑пјҢеҚіжІҰе…Ҙд»ҘжҲҳеҗҺдёӯеӣҪжӯЈз»ҹж•ҷеӣўдё»д№үзҡ„еҸ—жҲ’ж ҮеҮҶе’ҢеҸІи§ӮжқҘжүӯжӣІж—ҘжҚ®ж—¶жңҹзҡ„еҺҶеҸІжғ…еўғпјҢиҖҢеҝҪз•ҘжҲҳеҗҺдј жҲ’еҜ№дәҺеҘіжҖ§ж•ҷеӣўиә«еҲҶдёҺдҝ®иЎҢж–№ејҸзҡ„еҪұе“ҚгҖӮ
гҖҖгҖҖеҸ°ж№ҫзҡ„жғ…еҶөжҜ”иҫғзү№ж®Ҡзҡ„жҳҜпјҢж—Ҙжң¬ж®–ж°‘ж”ҝеәңзҡ„е®—ж•ҷж”ҝзӯ–йҮҚж–°е®ҡдҪҚж–Ӣж•ҷпјҢеӣ иҖҢйҖ жҲҗж–Ӣ姑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е®ҳж–№жүҝи®ӨгҖҒеҸҜд»ҘдёҺдҪӣж•ҷе°јдј—е№ізӯүзҡ„е®—ж•ҷиә«еҲҶгҖӮдёӯеӣҪжңқе»·дёҖеҗ‘и§Ҷж–Ӣж•ҷдёәз§ҳеҜҶе®—ж•ҷпјҢжӯЈз»ҹзҡ„дҪӣж•ҷе®—жҙҫдәҰи§Ҷж–Ӣж•ҷдёәең°ж–№дёҠдёҖз§ҚеңЁе®¶дҪӣж•ҷзҡ„еҪўејҸгҖӮе®ҳж–№дёҺжӯЈз»ҹзҡ„еғ§еӣўдё»д№үеҜ№дәҺж–Ӣж•ҷжңҖж„ҹиҜҹз—…зҡ„жҳҜе…¶д»ҘвҖңеңЁе®¶дәәвҖқиә«еҲҶжӢ…д»»еғ§дҫЈзҡ„е·ҘдҪңпјҢдёҫеҠһеҗ„з§Қд»ӘејҸгҖӮдҪҶжҳҜж–Ӣж•ҷе…·жңүдёҘеҜҶзҡ„еҚҮиҝҒзӯүзә§е’Ңзӣёеә”зҡ„дҝ®иЎҢж–№ејҸпјҢйҷӨдәҶйҮ‘е№ўжҙҫе’ҢйҫҷеҚҺжҙҫзҡ„з”·жҖ§д»ӘиҪЁеёҲеҸҜд»Ҙз»“е©ҡд№ӢеӨ–пјҢ他们иҮӘе·ұе®ҡдҪҚдёә继жүҝзҰ…е®—е…ӯзҘ–ж…§иғҪд№ӢдҫӢпјҢеңЁдҝ—дё–д№ӢдёӯиҖҢйқһж•ҷеӣўд№ӢеҶ…дҝ®иЎҢпјҢжҜ”еғ§дҫЈпјҲз©әй—ЁпјүжӣҙиғҪе®һи·өзҰ…зҗҶгҖӮе°ұж•ҷд№үгҖҒз»„з»ҮгҖҒдҝ®иЎҢдҪҚйҳ¶еҗ„ж–№йқўиҖҢиЁҖпјҢж–Ӣж•ҷдёҚдҪҶд»ЈиЎЁжҳҺжё…д»ҘжқҘдҪӣж•ҷзҡ„ж–°е…ҙе®—жҙҫпјҢиҖҢдё”жүҖи°“зҡ„вҖңеңЁе®¶дҪӣж•ҷвҖқд№ҹ并йқһжҢҮдҝ—дәәдё»еҜјзҡ„дҪӣж•ҷпјҢиҖҢжҳҜдё–дҝ—зҡ„дҪӣж•ҷгҖӮж—Ҙжң¬ж®–ж°‘ж”ҝеәңиөӢдәҲж–Ӣж•ҷе®ҳж–№и®ӨеҸҜпјҢеҸҜ收дёҖзҹідёӨйёҹд№ӢеҲ©гҖӮдёҖж–№йқўпјҢеҮҖеңҹзңҹе®—зӯүж—Ҙжң¬дҪӣж•ҷе®—жҙҫзҡ„еғ§дҫЈд№ҹжҳҜеёҰзң·пјҢдёҺе…¶еҗҰи®Өж–Ӣж•ҷиҖҢеҮёжҳҫж—Ҙжң¬зҡ„еғ§дҫЈе©ҡ姻зҡ„еҗҲжі•жҖ§еҚҒеҲҶе”җзӘҒпјҢдёҚеҰӮжүҝи®Өж–Ӣж•ҷйўҶиў–зұ»дјјеғ§дҫЈзҡ„иә«еҲҶпјҢжӢүиҝ‘еҪјжӯӨзҡ„е·®и·қпјҢиҝӣиҖҢеҗёж”¶ж–Ӣж•ҷеҫ’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ж—Ҙжң¬е°Ҷж–Ӣж•ҷеҪ’зұ»дёәеҸ°ж№ҫдҪӣж•ҷзҡ„иҢғз•ҙпјҢеҖҫеҗ‘д»Ҙжҡ§жҳ§зҡ„еғ§дҝ—з•ҢйҷҗжқҘиҙ¬дҪҺеҸ°ж№ҫдҪӣж•ҷзҡ„дёҚзәҜзІ№жҖ§гҖӮ
гҖҖгҖҖж—Ҙжң¬е®—ж•ҷж”ҝзӯ–зҡ„ж®–ж°‘еҝғжҖҒпјҢеңЁжЁЎзіҠеҢ–ж–Ӣ姑е’ҢдҪӣж•ҷе°јдј—зҡ„иә«еҲҶи®ӨеҗҢдёҠпјҢжңҖдёәжё…жҘҡгҖӮдёёдә•еңӯжІ»йғҺжӣҫд»Ҙж–°з«№еҮҖдёҡйҷўдёәдҫӢпјҢжҢҮеҮәеҸ°ж№ҫе°јдј—дёҚдјјж—Ҙжң¬е°јеғ§пјҢеҸҚиҖҢиҫғеғҸж–Ӣ姑гҖӮеҮҖдёҡйҷўдёәж–°з«№йғ‘ж°Ҹдё–ж—ҸжүҖе»әд№Ӣ家йҷўпјҢеҺҹжң¬дёәе…¶дё»жҜҚйҷҲж°ҸзҘҲжұӮеӯҗе—ЈиҖҢе»әпјҢеҗҺжқҘ收养дёӨдҪҚе°јдј—жқҘз»ҸиҗҘпјҢйҒӮжҲҗдёәйғ‘家еҘізң·дҝ®иЎҢгҖҒжёЎеҒҮзҡ„ең°ж–№гҖӮ笔иҖ…1997дәҺе№ҙеӨҸеӨ©иө°и®ҝж–°з«№еҮҖдёҡйҷўпјҢи®ҝи°Ҳ第дёүд»ЈпјҲйқһ第дёүдҪҚпјүдҪҸжҢҒж…Ҳеҝғжі•еёҲеҗҺеҸ‘зҺ°пјҢж—ҘжҚ®ж—¶жңҹеҸ°ж№ҫе°јдј—еӨҡж•°дёҚжӣҫеүғеәҰеңҶйЎ¶пјҢжҳҜйҖ жҲҗдёёдә•зҡ„иҜ„д»·зҡ„е…ій”®еӣ зҙ гҖӮж…Ҳеҝғжі•еёҲдёүеІҒеҚідёәеҮҖдёҡйҷўжүҖ收养пјҢиҮӘе№јдәҺеҮҖдёҡйҷўдёҺйғ‘家еӯҗеҘідёҖиө·й•ҝеӨ§гҖӮеҘ№еӣһйЎҫе…¶е№јж—¶з”ҹжҙ»ж—¶жҢҮеҮәпјҢе…¶еёҲзҘ–жҳҜеҪ“ж—¶еҮҖдёҡйҷўеҶ…е”ҜдёҖиҗҪеҸ‘зҡ„е°јдј—пјҢиҝҷжҳҜеӣ дёәеҘ№еҸ—ж—Ҙжң¬дҪӣж•ҷж•ҷиӮІзҡ„зјҳж•…гҖӮ
гҖҖгҖҖж…ҲеҝғеҚҒеҲҶиҒӘйў–ж•ҸжҚ·пјҢеӣ жӯӨе…¶еёҲзҘ–еёҢжңӣеҘ№д№ҹиҗҪеҸ‘пјҢ继жүҝе…¶иЎЈй’өгҖӮ12еІҒзҡ„ж…ҲеҝғеҚҙжҢҮзқҖе ӮдёҠдҫӣеҘүзҡ„и§Ӯдё–йҹіиҸ©иҗЁиҜҙвҖңиҝһеҘ№йғҪжңүеӨҙеҸ‘пјҢжҲ‘дёҚеүғгҖӮвҖқдҪҶжҳҜж…Ҳеҝғе…¬еӯҰж ЎпјҲзӣёеҪ“дәҺзҺ°еңЁзҡ„еӣҪж°‘е°ҸеӯҰпјүжҜ•дёҡеҗҺйўҶжӮҹеҲ°пјҢеҲ°ж—Ҙжң¬иҜ»е°јдј—еӯҰж ЎжҳҜеҘ№е”ҜдёҖ继з»ӯжұӮеӯҰзҡ„жңәдјҡгҖӮиҖҢж №жҚ®ж—Ҙжң¬дҪӣж•ҷеӯҰж Ўзҡ„规е®ҡпјҢж…Ҳеҝғеҝ…йЎ»еүғеәҰгҖӮз»“жһңж…ҲеҝғеңҶйЎ¶пјҢиҖҢз”ұйғ‘家жҸҗдҫӣеҘ№еңЁж—Ҙжң¬зҡ„еӯҰе®ҝиҙ№гҖӮж…Ҳеҝғ并且еҗ‘еҘ№зҡ„еёҲзҘ–з«Ӣеҝ—е°ҶжқҘеӯҰжҲҗеҪ’жқҘпјҢиҰҒеҪ“еёғж•ҷеёҲпјҢе…үиҖҖй—ЁжҘЈгҖӮж…Ҳеҝғ并且жҠұжҖЁпјҢиҷҪ然ж—Ҙжң¬еңЁеҸ°еғ§еҗ‘жқҘдёҺйғ‘家дҝқжҢҒиүҜеҘҪе…ізі»пјҢеҸҜжҳҜ他们йқһеёёеҗқдәҺжҸҗдҫӣеҸ°ж№ҫе°јдј—еҲ°ж—Ҙжң¬иҝӣдҝ®зҡ„иө„ж–ҷпјҢеҮ д№ҺдёҖй—®дёүдёҚзҹҘпјҢзӣҙеҲ°ж…ҲеҝғдёҖеҲҮе°ұз»ӘпјҢзҰ»еҸ°зҡ„еүҚеӨ•жүҚеҸ‘зҺ°пјҢиҝҷдәӣж—Ҙжң¬еғ§дәәе…¶е®һйқһеёёзҶҹиҜҶж—Ҙжң¬дҪӣж•ҷеӯҰж Ўзҡ„жғ…еҪўгҖӮ
гҖҖгҖҖж—Ҙжң¬еңЁеҸ°еғ§дҫЈе№¶дёҚйј“еҠұеҸ°ж№ҫе°јдј—еүғеәҰпјҢдәҰеҸҜд»Ҙд»Һ他们жүҖи®ҫзҡ„еҮә家尼众и®ӯз»ғзҸӯеҫ—зҹҘгҖӮж—ҘжҚ®ж—¶жңҹеҹәйҡҶең°еҢәеҘіжҖ§ж¬ІеҸ–еҫ—еҮә家иә«еҲҶпјҢеҝ…йЎ»еңЁжӯӨи®ӯз»ғзҸӯйҖҡиҝҮдёӨе№ҙиҜҫзЁӢгҖӮдҪҶжҳҜеңЁз»“дёҡе…ёзӨјзҡ„зӣёзүҮдёҠпјҢжқҘиҮӘеҗҢдёҖеҜәйҷўзҡ„еҘіеӯҰз”ҹдёҚдёҖе®ҡйғҪиҗҪеҸ‘гҖӮеҗҢж ·зҡ„жғ…еҪўдәҰеҸ‘з”ҹеңЁдёңжө·е®ңиҜҡе’ҢеӨ§еІ—еұұжҙҫжўҒејҖеҗүдҪҸжҢҒеҗҲдҪңпјҢ1941е№ҙдәҺиҺІеі°еҜәдёҫеҠһвҖңе°јеғ§и®Ід№ дјҡвҖқгҖӮз»“дёҡе…ёзӨјдёҠпјҢеӨҡж•°еҸ°ж№ҫи“„еҸ‘зҡ„еҘіеӯҰе‘ҳе’Ңж—Ҙжң¬е°јж•ҷеёҲзҡ„еңҶйЎ¶жҒ°жҲҗеҜ№жҜ”гҖӮ
гҖҖгҖҖдёңжө·е®ңиҜҡз§°иөһеӨ§еІ—еұұжҙҫзҡ„йҫҷж№–еәөдёәеҸ°ж№ҫжңҖеӨ§гҖҒжңҖжңү规模зҡ„вҖңе°јдј—йҒ“еңәвҖқпјҢеӣ жӯӨиҜ·дёңжө·жҳҢйҒ“гҖҒжіҪжң¬ејҳйҒ“дёӨдҪҚж—Ҙжң¬е°јдј—дёәж•ҷеёҲпјҢе°ұиҺІеі°еҜәпјҲдҪҚдәҺж—§и¶…еі°еҜәе’Ңйҫҷж№–еәөд№Ӣй—ҙпјүй’ҲеҜ№еҸ°ж№ҫеҘіжҖ§жҺЁиЎҢж—Ҙжң¬дҪӣж•ҷж•ҷиӮІгҖӮж №жҚ®жұҹзҒҝи…ҫзҝ»иҜ‘еҮәеҪ“е№ҙгҖҠеҸ°ж№ҫдҪӣж•ҷгҖӢзҡ„ж–°й—»пјҢжӯӨж¬Ўи®Ід№ дјҡзҡ„еӯҰе‘ҳдёәвҖңдё»иҰҒжҳҜеҸ°ж№ҫеҚ—йғЁзҡ„еҘідј—гҖҒеғ§е°јпјҲе°јеғ§пјүгҖҒж–Ӣ姑пјҢе…¬еӯҰж ЎжҜ•дёҡд»ҘдёҠзҡ„зЁӢеәҰпјҢжңүиҝҗз”Ёж—ҘиҜӯзҡ„иғҪеҠӣпјҢз»Ҹз”ұеҪ“ең°еҜәйҷўзҡ„жҺЁиҚҗпјҢеҸӮдёҺи®Ід№ иҖ…дәҢеҚҒеҗҚвҖқгҖӮиҷҪ然笔иҖ…е№¶ж— иҝҷ20еҗҚеӯҰе‘ҳзҡ„ж•°жҚ®пјҢдҪҶжҳҜеҘ№д»¬еҶіеӨҡж•°жҳҜйҫҷж№–еәөзӯүеӨ§еІ—еұұжҙҫзҡ„еҘіжҖ§жҲҗе‘ҳпјҢеӣ дёәж•ҙдёӘжҙ»еҠЁжҳҜз”ұеӨ§еІ—еұұиөһеҠ©пјҢ并且з”ұвҖңеҪ“ең°еҜәйҷўвҖқзӯӣйҖүеӯҰе‘ҳиө„ж јзҡ„гҖӮиҷҪ然ж—Ҙжң¬еғ§е°јзӣӣиӘүйҫҷж№–еәөдёәеҸ°ж№ҫж•°дёҖж•°дәҢзҡ„е°јдј—йҒ“еңәпјҢдҪҶжҳҜдәҰжңӘиҰҒжұӮиҝҷдәӣеҘіеӯҰе‘ҳеүғеҸ‘пјҢиҖҢйҫҷж№–еәөеҶ…зҡ„е°јдј—д№ҹеӨҡж•°еёҰеҸ‘дҝ®иЎҢгҖӮ
гҖҖгҖҖ既然йҫҷж№–еәөдёәжқҘиҮӘеҸ°еҚ—ејҖе…ғеҜәзҡ„ж°ёе®ҡе’Ңе°ҡ(1877-1939)жүҖе»әпјҢ1920е№ҙиҝҳиҒҳиҜ·еӨ§йҷҶеҚ—жҷ®йҷҖеҜәдҪҸжҢҒдјҡжіүе’Ңе°ҡ(1874-1943)жқҘеҸ°жҺҲвҖңеңЁе®¶иҸ©иҗЁжҲ’вҖқпјҢйҫҷж№–еәөзҡ„жҲҗе‘ҳжң¬иә«зҡ„е®ҡдҪҚеә”жҳҜе°јдј—пјҢд»ҘеҸҠзҡҲдҫқдҪӣж•ҷзҡ„иҸң姑пјҢиҖҢйқһж–Ӣж•ҷзҡ„ж–Ӣ姑гҖӮдҪ•еҶөеӨ§йҷҶеғ§дәәжһ—ж…§дә‘дёәйҫҷж№–еәөжүҖж’°зҡ„дёҮе№ҙз°ҝеәҸпјҢз§°д№ӢдёәвҖңе°јдј—жё…дҝ®йҒ“еңәвҖқгҖӮеҗҢе№ҙ(1936)пјҢеҚҸеҠ©дёңжө·е®ңиҜҡжҺЁе№ҝж”№йқ©ж—§жғҜдҪӣж•ҷеҜәйҷўиҝҗеҠЁзҡ„ејҖе…ғеҜәй«ҳжү§еҫ·е’Ңе°ҡ(1986-1955)дәҰи°“йҫҷж№–еәөдёәвҖңи‘—еҗҚе°јеҜәвҖқгҖӮйҫҷж№–еәө并дёҚеӣ е…¶дҪҸдј—еёҰеҸ‘дҝ®иЎҢиҖҢиў«еҪ“ж—¶дҪӣж•ҷз•ҢеҲҶзұ»дёәж–Ӣе ӮгҖӮдҪҶжҳҜж—Ҙжң¬еғ§е°јеҹәдәҺвҖңе°ҠйҮҚвҖқеҸ°ж№ҫж—§жғҜзҡ„з«ӢеңәпјҢ并дёҚиҰҒжұӮеҸ°ж№ҫе°јдј—еүғеҸ‘пјҢеҸӘжңүиғҪеӨҹз•ҷеӯҰж—Ҙжң¬гҖҒзңҹжӯЈиҝӣе…Ҙж—Ҙжң¬дҪӣж•ҷзі»з»ҹзҡ„еҸ°ж№ҫе°јдј—жүҚеңҶйЎ¶пјҢеҫ—еҲ°е°јеғ§зҡ„ең°дҪҚгҖӮеҸҜи§Ғе°јдј—зҡ„еӨҙеҸ‘жҳҜеҰӮдҪ•жҲҗдёәж®–ж°‘иҖ…жҳҫзӨәе…¶е®—ж•ҷдјҳдәҺиў«ж®–ж°‘иҖ…зҡ„иұЎеҫҒгҖӮ
гҖҖгҖҖж•ҙдҪ“иҖҢиЁҖпјҢж—ҘжҚ®ж—¶жңҹеҸ°ж№ҫе°јдј—еҮә家иҗҪеҸ‘并дёҚжҷ®йҒҚпјҢе°ұеғҸеҘ№д»¬еҸ—еӨ§жҲ’дёҖж ·йҡҫеҫ—гҖӮеҸ°ж№ҫз”ұдәҺдҪҚеӨ„иҫ№йҷІең°еҢәпјҢе№¶ж— е®ҳж–№жҲ–еӨ§е®—жҙҫдёӣжһ—зҡ„жҲ’еқӣпјҢеӣ жӯӨеҸ°ж№ҫеғ§е°јж¬ІеҸ—е…·и¶іжҲ’иҖ…пјҢеҝ…йЎ»жёЎиҝҮеҸ°ж№ҫжө·еіЎеҺ»зҰҸе»әзӯүең°еҸ—жҲ’гҖӮйҷӨдәҶиҖғиҷ‘еҘіжҖ§иҝңжёёзҡ„е®үе…Ёй—®йўҳд№ӢеӨ–пјҢеәһеӨ§зҡ„ж—…иҙ№е’ҢжҳӮиҙөзҡ„жҲ’еңәиҙ№з”ЁпјҲйҖҡеёёиҝҳеҢ…еҗ«и°ўеёҲгҖҒеҸӮи®ҝгҖҒжёёеӯҰзӯүиҠұиҙ№пјүпјҢд№ҹдҪҝеҫ—еҸ°ж№ҫеҜәйҷўеҒҸеҗ‘йҖүжҙҫеғ§дј—вҖ”вҖ”зү№еҲ«жҳҜдҪҸжҢҒ继жүҝдәәйҖүвҖ”вҖ”еҺ»еӨ§йҷҶеҸ—жҲ’гҖӮзҺҜеўғжҜ”иҫғдјҳи¶Ҡзҡ„е°јдј—пјҢиҝҳеҸҜд»Ҙд»ҘеҜ„жҲ’зҡ„ж–№ејҸпјҢйӮ®еҜ„иҫғе°‘зҡ„еҸ—жҲ’иҙ№з”ЁеҲ°жҲ’еқӣпјҢд№°еҲ°жҲ’зўҹгҖӮеңЁдәәжңӘеҮәеёӯ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иҝҷдәӣе°јдј—д№ҹдёҚйңҖиҗҪеҸ‘гҖӮеҘ№д»¬жҲ–жҳҜе°ҶеӨҙеҸ‘жүҺжҲҗдёӨжқЎеҸ‘иҫ«пјҢжҳҫзӨәеҘ№д»¬зҡ„еӨ„еҘіиә«еҲҶпјӣжҲ–жҳҜйҪҗиҖіеүӘеҺ»пјҢиЎЁзӨәиҮӘе·ұзҡ„е…ҲиҝӣпјӣжҲ–жҳҜеҰӮж–Ӣ姑дёҖж ·зӣҳжҲҗе·Іе©ҡеҰҮеҘізҡ„еҸ‘й«»пјҢд»ҘжҳҺеҝ—дёҚе«Ғе®ҲиҙһгҖӮж—ҘжҚ®ж—¶жңҹеҸ°ж№ҫе°јдј—еӨҡдәҶеҲ°ж—Ҙжң¬жұӮеӯҰеҸ–еҫ—е°јеғ§иө„ж јзҡ„жңәдјҡпјҢдҪҶжҳҜиҝҷд»…еұҖйҷҗдәҺ少数家еўғдјҳи¶ҠгҖҒжҲҗз»©дјҳз§Җзҡ„е°јдј—гҖӮеӣ жӯӨж—ҘжҚ®ж—¶жңҹиғҪеӨҹеүғеҸ‘зҡ„е°јдј—пјҢд»ҚеңЁе°‘ж•°гҖӮеңЁиҝҷз§Қжғ…еҶөд№ӢдёӢпјҢеҸ°ж№ҫе°јдј—з•ҷеҸ‘пјҢдёҚд»…жҳҫзӨәеҘіжҖ§е’Ңе®ҳж–№д»ҘеҸҠе®—жҙҫжҺҲжҲ’еҲ¶еәҰзҡ„з–Ҹиҝңе…ізі»пјҢд№ҹе‘ҲзҺ°еҘ№д»¬еҰӮдҪ•з”ЁеҸ‘еһӢпјҲиҖҢйқһеүғеҸ‘пјүжқҘиЎЁиҫҫиҮӘе·ұзҡ„е®—ж•ҷиә«еҲҶгҖӮ
гҖҖгҖҖеҚідҪҝ1953е№ҙд»ҘеҗҺпјҢеҸ°ж№ҫеҮ д№Һе№ҙе№ҙејҖжҲ’еқӣпјҢдҪҶжҳҜж—©жңҹд»Қжңүи®ёеӨҡе°јдј—ж— жі•иҙҹжӢ…жҲ’дјҡзҡ„еҝҸж‘©гҖҒи¶…еәҰзҘ–е…ҲгҖҒдҫӣеғ§и°ўеёҲзӯүиҙ№з”ЁгҖӮзҺ°еңЁ70еІҒд»ҘдёҠзҡ„е°јдј—пјҢиҝҳжңүдәәеӣһйЎҫеҲ°еҪ“еҲқжӢҺзқҖе°ҸеҢ…иўұпјҢзһ’зқҖзҲ¶жҜҚд»“дҝғйҖғ家еҺ»еҗғиҸңзҡ„жғ…еҪўгҖӮеҪ“ж—¶еҜәйҷўз»ҸжөҺжғ…еҶөдёҚеғҸзҺ°еңЁеҰӮжӯӨеҜҢиЈ•пјҢеҘ№д»¬еёёеёёиҰҒзӯүдёҠеҘҪеҮ е№ҙпјҢжүҚзӯ№жҺӘеҲ°дёҖеҘ—еғ§иЎЈпјҢжҲ–иҖ…з»ҲдәҺеҫ—еҲ°еҸ—жҲ’зҡ„жңәдјҡпјҢеӣ жӯӨеҮә家并йқһ马дёҠдёҖе®ҡеңҶйЎ¶гҖӮиҝҳжңүдәӣе№ҙиҪ»жңӘе©ҡеҘіжҖ§з»Ҹеёёз»“дјҙеҲ°еҗ„еәөе ӮеҜәйҷўжёёзҺ©пјҢж—¶ж—Ҙй•ҝдәҶпјҢдҫҝеҗ„иҮӘзҡҲдҫқдёҚеҗҢзҡ„еҜәйҷўеәөе ӮпјҢжёҗжёҗеҫ…еңЁеҜәйҷўеәөе ӮйҮҢеё®еҝҷгҖӮз”ұдәҺжқҘеҫҖзҡ„йғҪжҳҜеҘіжҖ§е’Ңе°јдј—пјҢеҘ№д»¬зҡ„зҲ¶жҜҚжҜ”иҫғе®№и®ёеҘ№д»¬еҰӮжӯӨдә«еҸ—дёҖдёӢе№ҙиҪ»зҡ„з”ҹжҙ»гҖӮиҝҷдәӣе№ҙиҪ»еҘіжҖ§йҖҡеёёд№ҹдёҚз«ӢеҲ»иҗҪеҸ‘пјҢжңүзҡ„дәәз”ҡиҮідёҖдҪҸеҜәйҷўеҚҒе№ҙжүҚеңҶйЎ¶пјҢдёәзҡ„д№ҹжҳҜе®үжҠҡзҲ¶жҜҚдәІпјҢеҮҸе°‘жқҘиҮӘ家еәӯзҡ„йҳ»еҠӣгҖӮзӣёеҜ№зҡ„пјҢеӣ дёәжңӘжӣҫиҗҪеҸ‘пјҢдёҮдёҖз”ҹеҫ’ж— жі•йҖӮеә”еҜәйҷўз”ҹжҙ»пјҢиҝҳдҝ—е®№жҳ“пјҢеҜәж–№д№ҹеҸҜд»ҘйҒҝе…Қи®ёеӨҡйә»зғҰгҖӮ
гҖҖгҖҖ笔иҖ…еңЁеұҸдёңд№ҹеҸ‘зҺ°жҲҳеҗҺд»Қжңүе°јеҜә收养еӯӨе„ҝпјҢд»Ҙдҫҝж—ҘеҗҺ继жүҝиЎЈй’өзҡ„жғ…еҶөгҖӮиҝҷдәӣе°јеҜәиҷҪ然дёҚеғҸж—ҘжҚ®ж—¶жңҹйғ‘家зҡ„еҮҖдёҡйҷўдёҖж ·еҜҢжңүпјҢеҸҜд»Ҙж Ҫеҹ№е…»еҘіз•ҷеӯҰпјҢдҪҶжҳҜеҘ№д»¬д№ҹеҖҫеҗ‘дәҺи®©иҝҷдәӣе…»еҘіеёҰеҸ‘дҝ®иЎҢпјҢзӣҙеҲ°жёЎиҝҮйқ’жҳҘжңҹжүҚиҖғиҷ‘и®©еҘ№д»¬жӯЈејҸеңҶйЎ¶гҖӮз”ұдәҺд»ҘеүҚж°‘йЈҺжҜ”иҫғдҝқе®ҲпјҢдёҚеғҸзҺ°еңЁи®ёеӨҡеғ§е°јиҝӣе…ҘеӨ§дё“йҷўж Ўж•ҷд№Ұе’ҢжұӮеӯҰпјҢдҪҸжҢҒиЎЁзӨәи®©иҝҷдәӣе…»еҘіз•ҷеҸ‘д»ҘдҫҝеӨ–еҮәжҺҘеҸ—дёҖиҲ¬ж•ҷиӮІпјҢиҝҳжҳҜжҜ”иҫғж–№дҫҝзҡ„еҒҡжі•гҖӮ
гҖҖгҖҖдёҠиҝ°иҝҷдәӣеҸ°ж№ҫе°јдј—еҜ№еҫ…еӨҙеҸ‘зҡ„жҖҒеәҰжҳҫзӨәпјҢеҘ№д»¬йқһеёёжё…жҘҡеӨҙеҸ‘жүҖд»ЈиЎЁзҡ„жҖ§еҲ«ж„Ҹж¶өпјҢд»ҘеҸҠиҗҪеҸ‘жүҖд»ЈиЎЁејғз»қдё–дҝ—иә«еҲҶзҡ„дёҘйҮҚжҖ§гҖӮдҪҶжҳҜиҮӘд»ҺжҲҳеҗҺдёӯеӣҪдҪӣж•ҷдјҡдәҺеҸ°ж№ҫе»әз«Ӣдј жҲ’еҲ¶еәҰгҖҒйҮҚжҢҜдёӯеӣҪзҰҒж¬Ізҡ„ж•ҷеӣўз”ҹжҙ»ж–№ејҸд»ҘжқҘпјҢеҸ°ж№ҫе°јдј—еңҶйЎ¶дёҺеҗҰпјҢ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еҫҲйҮҚиҰҒзҡ„жҢҮж ҮпјҢиў«з”ЁжқҘиЎЎйҮҸеҸ°ж№ҫдҪӣж•ҷзҡ„жӯЈз»ҹжҖ§е’ҢзҺ°д»ЈеҢ–гҖӮдёҖж–№йқўпјҢдёӯеӣҪдҪӣж•ҷдјҡе®Јз§°ж–Ӣ姑иёҠи·ғеүғеәҰеҸ—жҲ’зҡ„жғ…еҶөпјҢдёәвҖңеҮҖеҢ–вҖқеҸ°ж№ҫдҪӣж•ҷеҸ—ж—Ҙжң¬дҪӣж•ҷеҪұе“Қзҡ„йғЁд»ҪгҖӮиҖҢдёҺдј жҲ’еҲ¶еәҰзӣёиҫ…зӣёжҲҗзҡ„еғ§дҫЈж•ҷиӮІпјҢдёӨиҖ…йғҪејәи°ғз»Ҹе…ёе®һи·өжҲ’еҫӢзҡ„ж–№ејҸпјҢиҝӣиҖҢеј•д»ӢеҸ°ж№ҫеҘіжҖ§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жӯЈз»ҹеҢ–зҡ„е®—ж•ҷиә«еҲҶе’Ңеғ§дҫЈи®ӯз»ғпјҢиөӢдәҲеүғеәҰеҸ—жҲ’ж–°зҡ„еҺҶеҸІж„Ҹж¶ө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йҖҸиҝҮеңҶйЎ¶пјҢдј жҲ’еҲ¶еәҰејәеҢ–еғ§дҝ—з•ҢйҷҗпјҢеҜ№д»ҘеҫҖзӣӣиЎҢзҡ„ж–Ӣ姑е’Ңе…¶е®ғиҝҮжёЎеҪўејҸзҡ„еҘіжҖ§е®—ж•ҷз”ҹжҙ»ж–№ејҸдә§з”ҹжҺ’жҢӨжҖ§гҖӮеҢәеҹҹжҖ§дҪӣж•ҷе®һи·өж–№ејҸзҡ„е·®ејӮпјҢд№ҹйҖҸиҝҮе°ҶеҘіжҖ§зәіе…ҘжӯЈи§„зҡ„ж•ҷеӣўеҗҜи’ҷиҝҮзЁӢпјҢиҖҢйҮҚж–°ж•ҙеҗҲгҖӮж–Ӣж•ҷзҡ„д»ӘејҸ专家е’ҢеҸ°ж№ҫзҡ„ж—ҘејҸеғ§дҫЈеӨұеҺ»е…¶е®—ж•ҷеҗҲжі•жҖ§гҖӮиҝҷз§ҚеӨҚжқӮзҡ„иҝҮзЁӢдә§з”ҹдёҖдёӘй«ҳеәҰеҲ¶еәҰеҢ–е’Ңж ҮеҮҶеҢ–зҡ„еҘіжҖ§еғ§дҫЈз”ҹж¶ҜгҖӮжҲҳеүҚжҲҳеҗҺеҸ°ж№ҫдҪӣж•ҷеҘіжҖ§дҝ®иЎҢиҖ…жүҖжҺҲжҲ’еҲ«зҡ„е·®ејӮпјҢдёҖиҲ¬иҖҢиЁҖпјҢе°јдј—жң¬иә«жҜ”дёҖиҲ¬ж°‘дј—зҡ„ж„ҹеҸ—иҰҒејәгҖӮиҖҢдёҖиҲ¬ж°‘дј—жүҖдҪ“дјҡеҲ°зҡ„пјҢеҸҜиғҪиҝҳдёҚжҳҜе°јдј—еҸ‘еһӢж”№еҸҳзҡ„е®—ж•ҷж„Ҹд№үпјҢиҖҢжҳҜеүғеәҰжүҖеёҰжқҘзҡ„йңҮж’ј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еӣһйЎҫжҲҳеүҚжҲҳеҗҺеҸ°ж№ҫе°јдј—зҡ„еҸ‘еһӢж—¶пјҢеҗҠиҜЎзҡ„жҳҜпјҢе®—ж•ҷеҘіжҖ§и¶Ҡи®ҫжі•дҝқз•ҷеҘ№д»¬зҡ„еӨҙеҸ‘пјҢд»Ҙе…ҚзӣҙжҺҘеҶІеҮ»зҲ¶зі»зҡ„жҖ§еҲ«д»·еҖјзі»з»ҹж—¶пјҢеҘ№д»¬и¶Ҡиў«зӨҫдјҡжҺ’йҷӨеңЁеӨ–гҖӮеӣ дёәеҘ№д»¬зҡ„е®—ж•ҷи§’иүІпјҢеҹәжң¬дёҠжҸҗдҫӣзҲ¶зі»зӨҫдјҡдёҖдёӘе®үзҪ®ж— жі•еҲҶзұ»еҘіжҖ§зҡ„дҫҝе®ңиЎҢдәӢгҖӮиҖҢеҪ“е°јдј—з»ҲдәҺеңҶйЎ¶пјҢжӯЈејҸе®Је‘ҠдёҺдё–дҝ—зҡ„иә«еҲҶеҲҶиЈӮж—¶пјҢеҘ№д»¬еҸҚиҖҢеҖҹйҮҚе®—ж•ҷзҡ„еҲ¶еәҰеҢ–зӢ¬з«ӢпјҢеҫ—д»Ҙе°Ҷе…¶е®—ж•ҷз”ҹжҙ»з”ұз§Ғдәәзҡ„йўҶеҹҹжҸҗеҚҮеҲ°е…¬зҡ„йўҶеҹҹгҖӮ
гҖҖгҖҖз»“и®әпјҡд»ҺеҮәдё–еҲ°е…Ҙдё–
гҖҖгҖҖжҲҳеҗҺеҸ°ж№ҫеҘіеӨ§еӯҰз”ҹйӣҶдҪ“еүғеәҰзҡ„зҺ°иұЎпјҢд»ҘеҸҠеҸ°ж№ҫдҪӣж•ҷдёҫдё–й—»еҗҚзҡ„еӯҰеЈ«е°јзү№еҫҒпјҢйғҪеҸҚжҳ еҘіжҖ§еғ§дҫЈз”ҹж¶Ҝзҡ„еҸҳиҝҒгҖӮдёҖдёӘжӯЈз»ҹзҡ„гҖҒдё“дёҡзҡ„гҖҒзҺ°д»Јзҡ„еҘіжҖ§еғ§дҫЈз”ҹж¶ҜйҡҸзқҖдј жҲ’еҲ¶еәҰдёҺеғ§дҫЈж•ҷиӮІзҡ„жҷ®еҸҠпјҢе·Із»ҸеҪўжҲҗгҖӮиҖҢй«ҳеӯҰеҺҶзҡ„еҘіжҖ§иө°е…ҘдҪӣй—ЁпјҢеҲҷжӣҙеҠ йҖҹжӯӨдёҖжӯЈз»ҹж•ҷеӣўиә«еҲҶзҡ„дё“дёҡеҢ–д»ҘеҸҠзӨҫдјҡеҸӮдёҺзЁӢеәҰгҖӮдёӨиҖ…дә’дёәеӣ жһңгҖӮеңЁзӨҫдјҡеұӮйқўдёҠпјҢиҝҷдәӣе®—ж•ҷеҘіжҖ§зҡ„ж•ҷеӣўиә«еҲҶж”№еҸҳпјҢеӣ дёәж¶үеҸҠдј з»ҹе®—ж•ҷз”ҹжҙ»дёҺ家еәӯд»·еҖјзҡ„еҶІзӘҒпјҢдёҚдҪҶеҸҚжҳ еҘіжҖ§е®—ж•ҷиә«еҲҶзҡ„и®Өе®ҡе’Ңе®—ж•ҷзҡ„з”ҹжҙ»ж–№ејҸеҰӮдҪ•жҒҜжҒҜзӣёе…іпјҢиҖҢдё”д№ҹжҳҫзӨәдёҖиҲ¬зӨҫдјҡеӨ§дј—зҡ„е®—ж•ҷжҰӮеҝөеҰӮдҪ•еңЁжҖҘйҖҹеҸҳиҝҒдёӯпјҢеҰӮдҪ•зүөеҠЁе®¶еәӯдјҰзҗҶгҖҒжҖ§еҲ«з•ҢйҷҗгҖҒе®—ж•ҷе®һи·өзӯүж·ұеұӮзҡ„ж–ҮеҢ–жҰӮеҝө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