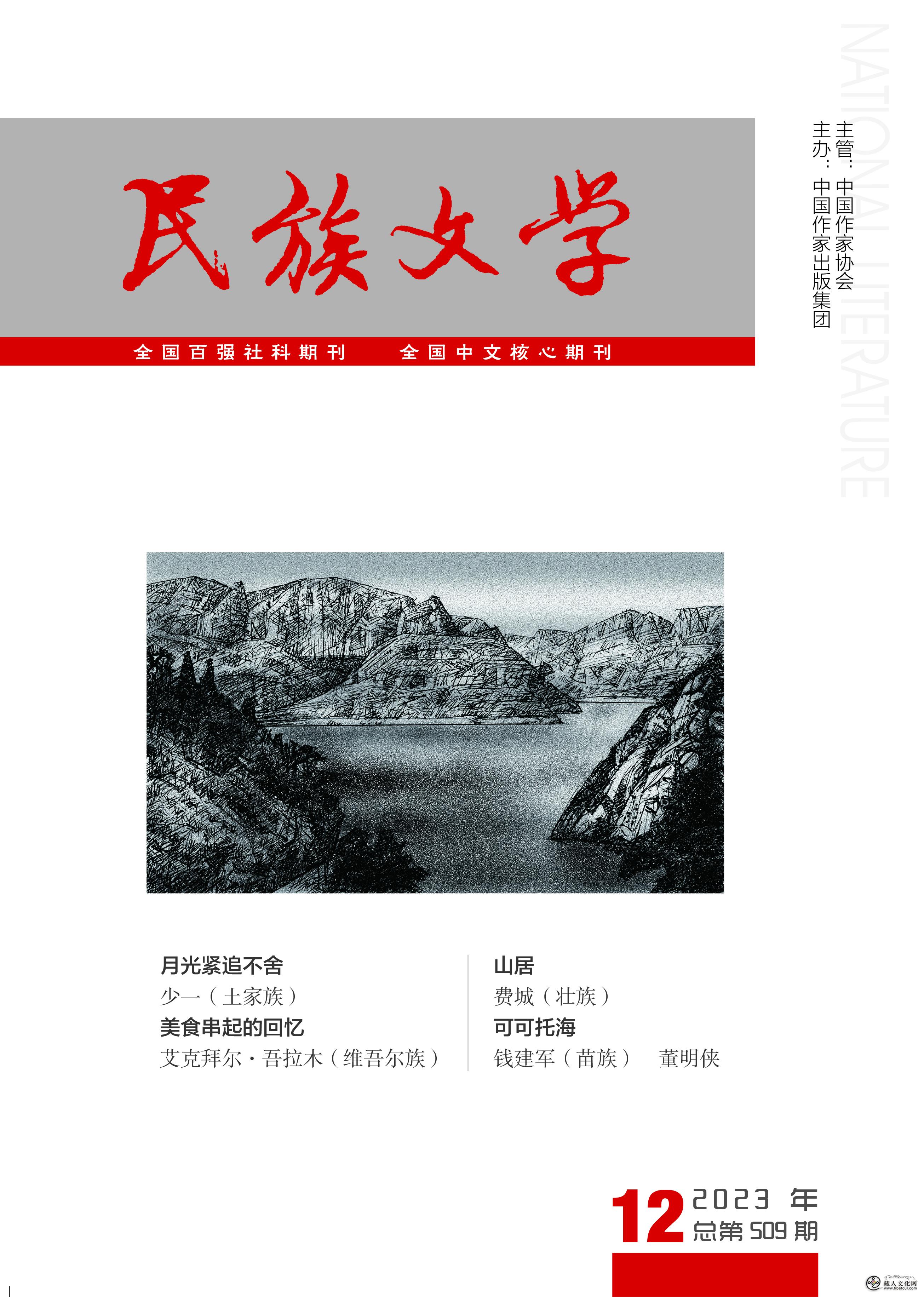
黄昏落下,银灰色的月亮从山尖升起来了。
月光像细雨,慢慢从山尖垂落大地。我沐浴在月光铺就的阴影里,走进一座老旧的村庄。村庄长在荒芜的尽头,像一片荒芜结出的果。一股鲜土的味道朝我袭来,一只喜鹊向我清脆的叫出一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在这座陷在月光中的村庄中行走,我没碰上一条游荡在黄昏中的看家狗,没遇见一个睡不着觉在路上行走的人,每家每户的大门都紧闭着,屋里静悄悄的。我在一座臧房前停下脚步,心想就是它了。我没用手敲门,没问屋里的主人是否同意我进屋,就直接推开了那扇立在黄昏中厚重的木门,门“吱呀”一声响,像给寂静的黄昏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朝里面走进去......
我不认识这座村庄,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是从一个岔路口把自己分叉来到这里的。岔路口不大,两边长满一人多高的白白草。那是个冬天,白白草干巴巴的,一阵野风吹过,草的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仿佛有一百条细流在草丛中流淌。
我被这一百条细流一样的流水声吸引,来到这里。那时我十二岁,正处在一个不畏惧天地,可以把自己随处安放的年龄。
在这之前,我做过几件任性的事,我随意把自己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想不回家就不回家。不可否认,在我的骨子里自始至终潜藏着一种叛逆和探索精神。经过那几次任性的事情之后,我的阿爸阿妈似乎一次比一次适应我的随意消失,即使后来我从自己的随意消失中走回来,心虚地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好像也没察觉到,我已经在和他们共同生活的屋檐下,消失过几天几夜了。
他们见我愣愣地站在空空荡荡的大门口,很久不敢抬脚跨进院坝,他们看我的眼神灰扑扑的,映着大地的颜色,没有责备,也看不出任何异样。他们用平常的口气喊我吃饭,叫我给羊圈里的几只母羊添几把嫩草,然后就没什么话给我说了。我依然站在那里不敢进门,我对他们对我的态度充满怀疑。我知道我做错了事,做错事就该得到惩罚,我在等待他们给我的惩罚,哪怕听他们用凹村土里土气的地脚话骂我几句,哪怕用他们藏在门后面的牛皮绳打我一两下,心里也舒坦些。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什么话也没问,就把我从他们视野里忽视掉了。他们坐在院坝中的青石桌旁,东拉西扯地把话题扯开了。
他们讲昨天自己放一群羊,看见一只秃鹫坠落悬崖的事;他们讲前天洛桑家门口,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大黑洞的事;他们讲两只闭嗓子三年的红嘴乌鸦,突然在晨雾中张嘴叫的事......他们讲得绘声绘色的,讲得彼此的眼珠子也多了几分光亮。我不想傻乎乎地再在门口等他们惩罚我了,我默默地走进院坝,坐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废弃的老木桩上,心里有种被他们抛弃的感觉。我用这种被抛弃的眼神一眼一眼地看他们,我希望在我的看中,能让他们想起他们那几天经历的事情里,少了一个这个家中最小的娃。从我站在门口,就一直在努力地做这件事。但是对于我的看,我的阿爸阿妈无动于衷。
银灰色的圆月跨过远处的一条河流,一片松树林,来到我家院坝的顶上,走累了一般放缓了脚步。院坝中,种着一棵核桃树,和我一般大小的年龄。我坐在老木桩上往天上望,月亮像核桃树结出的一个银灰色的大果子。随着它缓慢的移动,果子一会儿结在这个枝丫上,一会儿结在那个枝丫上,等银灰色的大果子结过十多枝枝丫后,有关我消失过的那几天,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还在继续讲述着。
我陷在自己失落的情绪中,沮丧,无助。他们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有一两次,我故意在他们说某件事的时候去打断他们。我把走向他们的步子踏得重重的,走到他们身旁时,我一改站在门口时的心虚,大声问他们要一碗酥油茶喝。他们对我的举动,显得一点不吃惊。他们停下正讲着的话,不正眼看我一下,顺手从茶壶里倒一碗酥油茶递给我,继续捡着刚才的话讲。我“咕噜咕噜”地一口喝掉酥油茶,站在他们身边不想离开,我的原意并不是想喝一碗夜里的酥油茶。
我站在他们的身边时,他们要讲的新鲜事一件接着一件,讲得嘴角冒出白泡子,舌头打起结来。我气哼哼地又问他们要第二碗酥油茶喝。他们还是不看我,也不问我夜这么深了,还喝这么多酥油茶干什么?他们不关心自己最小的娃,半夜会被一泡大尿胀醒,也不关心酥油茶的咸,会在夜里让自己最小的娃口舌干燥,因为一泡大尿和一口夜里想喝的水,娃要自己在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独自走向夜里撒一泡大尿,独自踮着脚尖从石水缸里舀一瓢冷水喝。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是娃夜里永远喊不答应的人。他们不关心一个自己的娃独自在夜里,面对巨大的黑,心里有没有恐惧和害怕。
我一下泄了气,知道无论自己在他们面前做什么,都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了。
那时的他们,活在那几天我消失的时间里,拔不出自己。
除了那几次的随意消失,我大部分时间待在他们身边。我每天跟在他们身后,看他们拿着一把镰刀或锄头,走到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青稞地收割青稞;看他们到尼达牧场放一群跟了我们一年或七八年的牦牛;看他们起早贪黑地背着背篓,到林子里去捡松茸。那时他们所做的和遇见的事情,都是平常经常要做的和经常遇见的事,所说的话也是平时经常说的话。只要我在他们身边,夜里他们坐在院坝的青石桌旁,板着脸,眼神空空的,嘴巴闭得紧紧的,仿佛一句想要说的话都没有。他们把平缓的呼吸从鼻子里出出来,又平缓地吸进去,他们偶尔看看远处,偶尔用空在夜里好久没动的一只手拍拍身上的灰尘,他们知道夜里谁都看不见他们身上的灰,但是他们还是那样去做了。只要我在他们身边的夜里,他们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寡淡和寂寥。这样的夜里,他们把自己活得孤独而独立,不过在这种孤独中,他们的心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不愿说出口。
月亮缓缓往高处爬,月光照亮了夜的暗的同时,也给大地的某些角落,留下了更深的阴影。
村里有只喜鹊,只有一只,每次月亮走过村头索嘎家时,它就仰着头,硬着脖子,冲天叫一声,无论秋冬,坚持不懈。那一声喜鹊的叫,干脆利落,叫完就再不叫了。那一声叫,有时在人的一次呼吸中很快就划过去了,有时在人的一次眨眼中很快就划过去了,有时在人走出一个步子中很快就划过去了,有时在人的一声咳嗽声中很快就划过去了。人有时被这一声喜鹊的叫声,弄得晕晕乎乎的,他们有时觉得听见了这声喜鹊的叫,有时又觉得没有听见。为了弄清楚这只喜鹊到底叫过没有,常常听见有人在夜里问:那只花鸟刚才叫过了?答的人刚才明明听见了喜鹊的叫,被人这么一问,模棱两可起来。他们在脑海中反复回忆刚才发生的事,越回忆记忆越模糊,越回忆记忆越陷入混沌,最后他们只能无奈地回答问的人,可能已经叫过了,大概已经叫过了的话。问的人“呀呀”地应着,其实人对一只每天都要朝天叫的喜鹊,是没那么在乎它叫与没叫的。人也曾有过被别人问出相同问题的时候,而他们给别人回答出的答案,也类似现在别人回答他的答案。
我的阿爸阿妈和别人不太一样,只要听见那一声喜鹊的叫,就会突然在夜里忙碌起来。他们从正坐着的板凳上一骨碌站起来,互相说着责怪的话,仿佛是他们中的谁,让自己沉默地坐在板凳上那么长时间,仿佛因为刚才的沉默,耽搁了他们干几件重要的事情。那时他们的忙碌,显得平常而毫无意义。忙过一阵之后,他们才突然想到自己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娃,常常和他们坐在夜里,一声不吭。他们不知道那么小的娃,为什么就喜欢独自在夜里待着。他们心里全是疑惑,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他们在夜里一遍遍喊我的名字,四面八方的喊,上上下下的喊。他们说要我赶快回家睡觉,再不睡觉黑就来了。那时在他们口中的黑,像一个鬼怪,会马上吃掉我。那时的他们,生怕自己喊出名字的娃遗落在黑里,再找不到了。在我陪在他们身边的夜里,他们总是轻易忘记我喜欢坐着的那个老木桩,明明昨天他们才在那个老木桩那里找到的我,第二天夜里又被他们忘记了。
我坐在老木桩上,看他们在院坝里急。他们一会儿爬上小楼喊我的名字,一会儿把一个花篮子背篓掀翻了找我。还有的时候,他们把院坝的木门一下关一下开的在门后找我。他们一遍一遍在木门后面找不到我,就站在门口把我的名字朝门外喊出去。我看见我的名字在他们的喊中,不回头看我一眼,悠悠闲闲地溜出了家门,朝门口的那块菜地穿过去了,朝不远处的那棵大树穿过去了,朝一家睡着的人的梦里穿过去了,最后不知了去向。当我的名字一次次丢失在无限大的夜里,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单薄了一些,呼吸细弱了一些,那个丢失在夜里的名字,带走了属于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在夜里,我从来不想答应阿爸阿妈的喊,我喜欢我的名字被他们在夜里一声声唤起。在夜里一个人的名字被唤起,会加深夜的重,会让自己感觉还有一个另外的自己,活在夜里和自己玩着躲猫猫的游戏。
我在老木桩上等他们来找我。他们总是在找完很多地方之后,似乎才想起在院坝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废弃很久的老木桩,此时正陷在月光铺就的阴影里,像一团没有散去的黑,等待被他们发现。我看见他们同时向我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望着他们一步步向我靠近,说不出是开心,还是悲伤。他们站在阴影的边沿,不向前走了,他们高耸耸地立在月光照亮的白里,显得高大、粗壮。他们向一团阴影喊出我的名字,我的名字瞬间被一团阴影染黑,变重,坠落到我的头顶,我忍不住“哎呀”叫出了声。
“你这不听话的娃,原来躲在一片阴影里,害得我们好找。”这是那个我叫阿爸的人说出的话。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在阴影里不叫出声,他们还是不会发现我。如果我不叫出声,那个不被他们发现的我,可能会一直生活在一片月光铺就的阴影里,永远走不出自己。阿妈把一只大手伸进阴影里牵我,她的那只大手在一片阴影里四处摸索,却找不到我。她的手悬在阴影里,停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等我主动去牵她。我在阴影里看阿妈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没有我,一轮圆月装满了她的眼。我从阴影里站起来,想把自己挤进阿妈的眼里,我蹭着身子,脖子伸得长长的,来回在阿妈眼前晃,尝试几次之后还是失败了。在一片月光铺就的阴影里,我离阿妈很远,到达不了她的眼。那个叫阿爸的人,有些不耐烦了,他粗声粗气地对着阴影喊:“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给我出来,快出来。”他的眼睛里也有一轮圆圆的月亮,占据了他的眼。那时我才知道,一旦在夜里,我的阿爸阿妈眼里都没有我。在夜里,唯一让他们牵挂的是一个他们家中最小的娃的名字,那个名字扎根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怎么躲都躲不过。
我从阴影里自己把自己走了出来,没去握那只伸向阴影的手,没抬头望向他们。离开月光铺就的阴影,我的心仿佛空了。
他们看见我,同时往后退了一步,我像一个黑里的怪物,猛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吓坏了他们。他们脸色惨白,上下左右地观察我,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那一刻,我成了他们月光下的陌生人。我还是不想说话,银灰色的月光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融化在了身体里。突然,我的阿爸阿妈像想起什么似地,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的下巴上。我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棕色的大痣,痣是从母体里带出来的,没有什么能取代它。痣,是他们在月光下辨别我是不是他们最小的娃的可靠证据。
“这娃,怎么在月光下长高一大节了,让我差点没认出来。”那个叫阿妈的人说着,把手伸向我。我知道她在说谎,是那颗大痣让他们认出了我,而不是其他的。月光下,我躲不过那只伸向我的手,我把手放进那只大手里,大手掌心硬硬的,冰凉凉的,像冬天折多河边的花石头。
我和他们一起从院坝走向屋子,月光把我们三个人的黑影拖在身后,仿佛还有另外的三个人要跟着我们走进屋子。一进屋,阿妈就松开了我的手,他们说自己这一天累得不行,说着扔下我,朝睡觉的藏床走过去,没过一会儿,呼呼把自己睡过去了。我像一根木讷的竹竿立在屋子中间,不知所措。我又成了一个被他们遗忘的人。伤心难过之后,我走到自己的小床旁,把疲惫的身体肆意躺了上去。在床上,我久久不能像他们一样轻易就把自己睡过去了,我的思想游弋在他们的鼾声里,偶尔听见从他们梦里传出几句不太像样的话,断断续续,朦朦胧胧,带着梦的轻薄:抓住那个逃跑的人,他的头上长出了马尾,河流不会放过他。我把头转过去望向他们,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没做出要去抓住一个人的任何举动。偶尔,我还听见从他们的嘴里突然传出一声喜鹊的叫声,那声音干脆利落,很快被夜淹没了。我想他们的梦,是多么丰富和自由呀,不像我。我从来没有把夜里发生的事情,在白天说给他们听,我想的是,夜里发生的事属于夜,我无权为夜做主。
只要我陪在阿爸阿妈身边的日子,我的家人似乎都生活在旧时间里。在旧时间里,他们所说的话是旧的,所做的事是旧的,他们的眼里和心里都装着几十年来他们经历过的旧。在他们的旧时间里,一阵吹向他们的野风是旧的,一片飘向他们的云朵是旧的,一朵开向他们的花是旧的,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哭声是旧的。他们常常在我耳边说些旧事,那些旧事,有时他们早上已经说过了,下午接着说,下午说过了,晚上还接着说,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一直重复在旧里。我看见他们一次次把旧事当新事来说时,心一阵阵地生疼。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们,说他们正在讲的事情,我已经从他们的嘴里听过无数次了。他们一脸惊讶,脸上满是怀疑,接着似乎觉察到哪儿不对劲儿,连声给我说人老了,很多事情记不住了。他们的自责,让我更加难过。我告诉他们其实也没什么,让他们别太在意。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把我对他们的提醒忘得干干净净,他们继续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把一件件旧事情,当成是一件新鲜事情来说。只有在一天快要被他们过完时,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天又被自己用完了,感觉什么都没做呀,就这样过完了。有时他们还说,回忆自己的这一辈子,跟从来没有过过一样。他们叹息的样子,像一只松鼠忧伤的模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在的时候,他们似乎都被旧时间困着。这种困,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毫无生气,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我隐约觉得,是一个小小的我带给了他们全部陈旧的生活。
于是在十二岁那年,我选择了再次逃离他们。我想用我的逃离,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而事实证明,我的逃离确实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我越来越想在他们面前消失自己,经意的,不经意的。
我背着他们朝远处走。最先我的出走,走得小心翼翼的,走得胆颤心惊的,生怕我踏出去的哪一个步子没走好,吵到他们的耳朵。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当着他们的面随意地朝一个方向走,我把我要走出去的脚步声踏得响响的,偶尔还故意朝一片空天、一棵老树吹出一声响亮的口哨,为的就是要告诉他们,他们最小的一个娃要走了。我走的时候,有时他们眼鼓鼓地看着我走却不喊住我,有时他们看见我右脚已经迈出家门,还回头眼巴巴地看他们,他们立马背过身去,假装忙其他的事情去了。在他们心里,他们希望我消失,只是作为父母,有些话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不怪他们,我一次次把自己的出走和随意消失,当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出走和随意消失也许是一个十二岁的我该活成的样子,出走和随意消失也许也是一个十二岁的我的命。
那天,我越往白白草的深处走,脚下的路被白白草越挤越细,最后没有了。路和人的一辈子有时很像,走着走着就把自己弄丢了。只是路和人的不同是,一条路可以把自己弄丢一会儿,过不了多久又把自己从某处捡回来。人就不同了,人只要在某处弄丢了自己,可能就永远丢掉了自己。那些尝试重新捡起自己的人,往往收获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个不一样的人,或好或坏地站在自己面前,有时让自己都感到陌生和不可信。人那时才由衷感叹,已经回不到从前的自己了。
人的变不像一条路的变,路的变大不了从变的地方多一个深坑,宽一点儿或窄一点儿,土厚一点儿或者薄一点儿,绊脚的石头多一点儿或者少一点儿,路最终的目的不会因为一点变,就把自己彻底改变了,路会想尽办法地延续自己的命,如让一只熟悉自己的鸟叫声,带自己往前走一点儿,让几滴从天空飘落下来的太阳雨,带自己往前走一点儿,让一阵不大不小的野风,带自己往前走一点儿,让自己昨夜没有做完的梦,带自己往前走一点。路的命比人的命硬,路只要想延续自己的命,什么都拦不住它。而人的变往往都是一变就彻底的变了,变得有时自己都惧怕自己,自己都认为那个活在世上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在帮自己活。人一旦变了,是轻易捡不回从前的自己的。
站在一人多高的白白草中,我回头望来时的路,路已被茂密的草封死了。我彻底失去了回头路。我有些茫然,有时我觉得是一条路把我弄丢了,有时我又觉得是我把一条路弄丢了。我不知道这条路的下一个接口在哪里,但我明确的知道这条路会在某个地方重新把自己延续下去。站在茂密的草丛中,我抬头往天上望,天的蓝偶尔在白白草地晃动中小块小块地落进我的眼睛里,天的蓝那一刻是我走出荒芜的光。那时,一百条细流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再次涌向我,我感觉一百条细流正从我的眼睛、耳朵、鼻孔、呼吸流进我十二岁的身体,我的身体在一百条细流地冲刷中,慢慢充盈起来,有种无形的力量在体内推动我,鼓舞我。我告诫自己,如果再不给自己一个方向走,我十二岁的身体就会被一百条细流很快淹没。我随意为自己选了一个方向走,我想无论我走向哪里,对那时的我来说都不重要了。那时的我,只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走出一百条细流追赶的出口。我挥动着十二岁的双手,迈着十二岁的双脚,在茂密的白白草中艰难前行。在我的走中,一人多高的白白草在脚下绊我,枯黄的犀利的枝叶故意伸向我,它们刮乱我的头发,割破我手上的皮肤,它们想用这种方式留住一个十二岁的我,独自在一片荒芜中长大自己。
虽然十二岁的我不在乎把自己再多留在这里几天几夜,我的短暂消失,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只要我愿意在这里留下,我就可以像荒野播种的一粒草种,和白白草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的生长,开出荒芜的花朵,结出荒芜的果子。但可惜的是,我对一望无际的荒芜没有一点兴趣。我不喜欢这里,我不属于荒芜。虽然我的阿妈阿爸对我的突然消失不理不问,虽然只要我在他们身边,就会让他们过上旧生活,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在那座藏房里彻底消失,那个我叫阿妈阿爸的人一定会急坏了,只要我彻底消失,他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了。他们会一个劲儿地到处找我,喊我的名字,寻找每个我留在这个世上的脚印。他们还会在一片空气中四处嗅我的味道,我身上的味道是从那个叫阿妈的人体内带出来的,没法改变。对于他们自己身体的味道,他们比谁都熟悉。如果我待在一片荒芜中独自长大自己,他们最终会花一年、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跟着一阵风的吹找到我,跟着一阵雨的飘找到我,但由于他们找我的时间花费得太久太长,他们中的两个人可能只剩下一个人了,还有一个人找着找着就不见了自己。这样的结局,他们应该早早就能预料到,他们或许提前就商量好了,对于那个找着找着就没有自己的人,可以任由他(她)消失,他们把这种消失当成是他们这个年龄段里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他们说,留下的那个人无论是他们中的谁,都必须找到被自己丢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小的娃,要不即使他们活到下辈子去了,也会因为前辈子未了断的事牵肠挂肚,活得郁郁寡欢。最关键的是,下辈子和这辈子中间有道深深的沟壑,有些事情会因为这道沟壑受到阻拦,让下辈子的人无法记忆。那时,他们的郁郁寡欢来得不明不白,莫名其妙,这样的情绪积累多了,会成为一种没法治愈的病。作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娃,如果是这样,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见的结果。
我加快了在白白草中穿行的速度,头上的蓝天在我的奋力穿行中,一点一点地变多了。有一瞬间,我觉得我像是在剥一片天的壳。因为我的剥,蔚蓝的天在我头上一点一点大起来,更多的光亮从天空洒向我。我知道继续往前走,有一片更大更广阔的天地就快被我遇见。
我终于走出了荒芜,还没等我缓过气来,轻薄的黄昏就到来了。这座叫不出名字的村庄出现在我的眼前,它长在一片荒芜的尽头,像荒芜结出的果实。村庄四周开着黄色、蓝色、白色的花,一条雪白的河流从远处的雪山流经这里,绕过村庄的一片土地,经过几座老旧的磨坊,在一片树林里转了几个大弯之后,不见了踪影。
我向这座村庄走去,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在荒芜中荒了自己多久。冲刷我体内的一百条细流,渐渐从我踏向这座村庄的脚步声中抽走,从我看这座村庄的眼神里抽走,它们要回去了,回到一片养育它们的荒芜中,重新过活自己。我也要回归了,我的回归首先从眼前的这座村庄开始。我不知道这座村庄里到底生活着怎样的一些人,他们说的话我是否能听懂,不过我相信一个人和一座村庄的遇见,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这种注定,隐秘却能让我清晰地感应到它的存在。
一步步靠近这座村庄,我的心安静下来。我用手抚摸路边的树,用鼻子闻那些开得正艳丽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我在快暗下去的小路上,遇见一只尾巴很长的喜鹊,它看见我干脆利落的叫了一声,就再不往下叫了。黄昏,在它的一声叫中更加寂静了。这一切的一切恍如梦境,那么熟悉,又那么亲切。
进了村,穿过两条小路分岔口,我径直向一座藏房走去。我想就是这里了。我心里没任何想用手敲门的想法,直接推开了那扇紧闭在黄昏中的门,木门“吱呀”一声响,像撕碎了黄昏的一道大口子。我从这道大口子中望进去,一个大大的院坝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一棵生长在黄昏中黑黑的核桃树。院坝中有两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忙碌着,院坝的一个角落里有个老木桩,木桩上孤独地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娃,一眼一眼地望着我走向他。
一轮银灰色的圆月挂在夜空,那个坐在老木桩上的娃,在我走进他时,正一点一点陷进月光铺就的阴影里。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12期

雍措,女,藏族,四川康定人。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