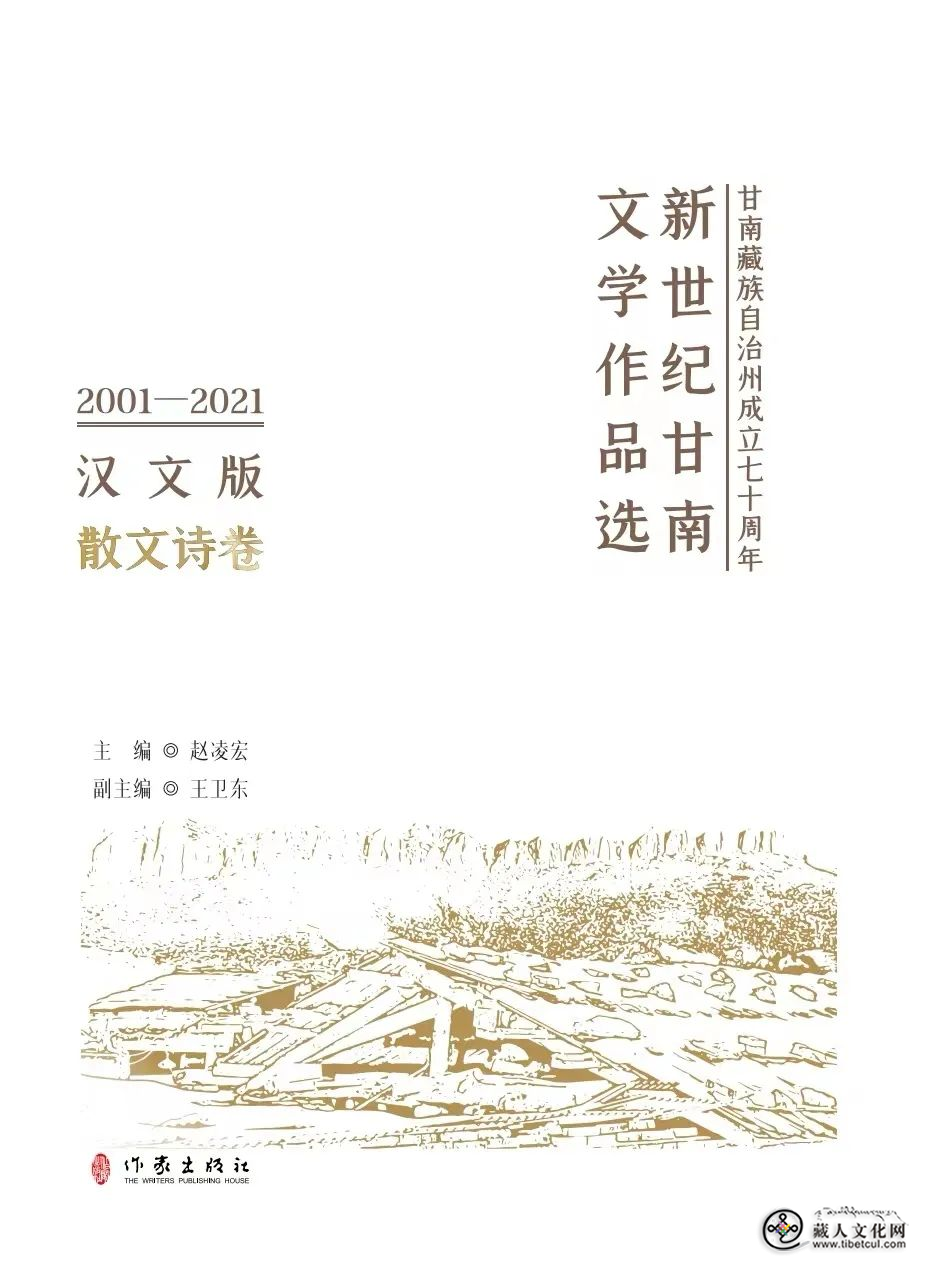
七月尕海
间歇的小雨,留出一个让人匆匆出入的空隙——那空隙如此狭小,仿佛前一滴雨水和后一滴雨水中间,插入的一个小小的休止符。
漫不经心的司雨之神,给一个俗人的闯入,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我的到来惊动了草地叶片上无数刚刚归于安静的钻石。
无疑,尕海是钻石当中最大、最安静的一颗。它奇异的安静,并不拒绝我对它久久的痴望,只是悄悄取走了我眼神中那一丝丝凡人的贪欲,和我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点点可怜的骄傲。
很快,自天而降的水珠,又把它复原成一座大地上沸腾的鼎镬。
斯柔古城堡遗址
——献给李振翼先生
拨开草丛,寻找那条青麻石铺就的大道。
那一度喧嚣、蒸腾尘浊、裹覆红氍毹、迎宾舞乐的大道,充满了刺鼻的草叶腐败的霉味。一堆受惊的蠕虫四下爬动……
法号吹鸣。车马辚辚。昔日的盛大景象确凿是不能与闻的了。
如此缘薄。
斜面。台地。一座想象中巨大光芒的门扉洞开。
——我发现了。他这样说:“一段墙基。然后是另一段……最后,又回到原地——完成了一个循环。”
阳光眩目……羊群四散……时间,九匹快马牵掣的马车,终于来到。
牧羊人和她的妻子,坐望在风雨之夜的甘加草滩,与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堡,有一段宿命的距离。
现在,他躺在文化馆陈旧的木椅中晒着迎窗射来的阳光。他患有严重的风湿。
“这里。还有那里。”向导的声音,渐渐飘近。
我看见荒草中一对对巨大的覆盆式柱础:阴刻的忍冬纹,时间凝固。
寂静敞开无形的建筑:那宴饮。帛书。青铜烛台。壁饰。藻井。鬼面舞。佛龛。吐蕃使者。
月光的蓄水池:一面莲花铜镜。
神秘的回廊:河州女子及其一生。
格萨尔说唱艺人,坐在一株巨柏之下。
一一浮现,又若细数家珍。失意的牧羊人无意间跌进一座宝库。
我曾在不多的时间里翻阅典籍。
那弥漫酥油味的、漫长的赞普时代:雪山之下,遍地城堡。但往往不着一字——“历史湮没了历史。”
一座寂寞无边的村落,被突然唤醒承担了使命。
斯柔:倔强记忆的天空。一段过往历史的见证。角厮罗政权最具诗意的称谓。古丝绸之路南线著名的孔道。
三百商人,卸下盐坨、茶叶、丝绸和青瓷。五百工匠运来了斧斤。而十万西夏叩关的人马倏进倏退,搅起一股股腥臊、狞厉的旋风……太遥远了——那狼烟。泥泞。阳光灿烂的谷地。那琴师。剑客。流寓异地的宋词写作者……太遥远了。
当考古者从一堵夹棍板筑式残垣状若牛眼的孔穴中,透视年代深处;我则从裸露于草棵间的一根根白骨之上听闻最初的美人幽幽的叹息。抑或是荷戟的豹皮武士血脉吟诵的潮汐:
仿佛是如斯的叹喟——如果有火焰,能够在时空的陶具之中保存其记忆,那多好。如果有生命,能够在我们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那多好。
我不禁恍惚。但我确信我于这废墟之上听闻了生命如斯的歌吟。
我仿佛看见:一次不可挽回的日落。一座昔日辉煌的城堡。一种令人无法正视和卒读的伤痛,在荒草间沉浮。
玛曲的街道
玛曲的街道,风是一年四季的常客。街道似乎为它们而建。唯一的十字路口,四通八达,没有任何障碍。风可以呼啸着来,呼啸着去,拍遍所有沿街的门窗,掐疼每一个匆匆出现的姑娘的脸蛋。
在玛曲,不用留意,就可以发现:在一些店铺的门板缝隙,在一家粮站陈旧铁栅的尖顶,甚至在那个迎面走来的藏族男人篷乱卷曲的发丛中,夹着、挑着、贴着或晃荡着一些破碎的
纸片、塑料袋、干枯的杨树叶和令人生疑的动物的毛发——像一艘刚刚打捞上来的沉船,浑身挂满海底的水草——这是风的勋章,它把它佩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地方。
在风经过的街道,沙土久久地沉醉——岗亭、台球桌、电影院门前油漆斑驳的招牌,昏暗光线中的肉案和砧板上忽明忽灭的刀子,一具冒着热气的牛头骨……都像悬浮其中,极不真实。你想在其中脱身、逃跑,已不可能。
你来到玛曲的街道,只能随波逐流。让风裹挟着你、推搡着你、翻遍你的口袋,给你鼻子上狠狠一拳、从一个街口把你带到另一个街口——一座裸露的草原,或一条旱季的大河,硬朗而沉默的北国边地风光,出现在你面前。
大风中晃过的那些面孔当中,没有一个是你熟悉的。他们(或她们)都带着大风部落的徽记——干燥的皮肤、紫红的脸膛、凹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管不顾、憨厚直爽、朴拙天真的眼神,以及袍襟中揣着白酒,为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杀死豢养多年的三只白兔的举动——都是你所不熟悉的。除了那一个唯一的一个——趔趄着身子,顶风在街道上奔跑,袍襟像大鸟一样腾空而起的青年——是你眼前湿漉漉、心中潮乎乎的兄弟。
你是在二十年前来到玛曲。那时,你的心中盛放着爱情——为一只蝴蝶的宛转飞离而痛不欲生,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而彻夜不眠。
谈 话
在玛曲活着的那些人中间,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他经常睡不着觉半夜爬起,看河水洗白岸边的石头。
有一次,露水闪烁。我和他坐在草地中间。他告诉了我一些奇异的事情。
他说:在我的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人。我只是他的役夫和走卒。我经常替他做一些看上去颇为荒唐的事情。比如:去岩石缝隙察看一条风干多年的蛇;在花朵中辩认可使孕妇呕吐不止的药草;用羊皮纸书写一些“年哦”体诗歌;不定时访问附近的几所寺院,等等。我在上班时经常神思恍惚,梦及古代和一只金色大鸟……
这个与我在草地上进行谈话的人是我的学生。几年不见,我感到有些恍惚,甚至怀疑那次谈话是否真实?
就像我常常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真的还生活在玛曲的人群之中,而不是在我自己的体内?
山间寺院
寂静的寺院,甚至比寂静本身还要寂静。阳光打在上面,沉浸在漫长回忆中的时光的大钟,仍旧没有醒来。
对面山坡上一只鸟的啼叫,显得既遥远又空洞。一个空地上缓缓移过的红衣喇嘛,拖曳在地的袍襟,并没有带来半点风声,只是带走了一块抹布大小的生锈的阴影。
简朴的僧舍,传达着原木和褐黑泥土本来的清香。四周花草的嘶叫,被空气层层过滤后,又清晰地进入一只昏昏欲睡的甲壳虫的听觉。辉煌的金顶,就浮在这一片寂静之上。
我和一匹白马,歇在不远处的山坡。坡下是流水环绕的民居,和几顶白色耀眼的帐篷。一条黝黑的公路,从那里向东通向阴晴不定的玛曲草原。
我原本想把马留在坡地,徒步去寺里转转。但起身以后,忽然感到莫名的心虚:寺院的寂静,使它显得那么遥远,仿佛另一个世界,永远地排拒着我。我只好重新坐下坐在自己的怅惘之中。
但不久,那空空的寂静似乎也来到了我的心中,它让我听见了以前从未听见过的响动——是一个世界在寂静时发出的神秘而奇异的声音。
年图乎寺——这是玛曲欧拉乡下一座寺院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我有意义的,只是它阳光下暴露的灿烂的寂静。
鹰
1
鹰,肉体凡胎。在这一点上,与一只鸽子相同。但鹰更多地出现在天空与神界搭边,而与阳台和日常无关。
2
尚黑衣者。孤独艺术家。腐鼠为食。风为马。天空为庭院。
时间:出入之甬道。生死:呼吸之晨昏。
3
东方,两大神秘意象:龙,虚幻的存在;鹰,存在的虚幻。
4
鹰呼吸着与我们大致相同的空气。鹰呼吸过的空气,沾有神的气息。
5
距佛祖最近的不是摩诃迦叶,不是经卷中那只可怜的鸽子,而是敦煌石窟中一只呼之欲出的鹰。
6
一只鹰在它的一生中,遭遇过三个人:佛陀。成吉思汗。希特勒。
7
鹰:一个真正的汉字。一个临风独立的汉字。一个不需要任何修饰的汉字。
雄鹰:一个苍白的词。一种蹩脚的修辞。
秃鹫:鹰的一种。让人想起不毛的山岗,和大风中蹲伏的那头扁毛畜牲。
8
鹰是一部被掐去了首尾的黑白影片。
不明其生,难解其死。只能感知它在时空中无尽的延续。
所有的神秘感由是而生。所有关于鹰的想象,也由是而生。
9
灵魂的对话。在那高处:鹰和无人。
10
那个到过西藏的人,回来后滔滔不绝:苯教。古格王朝。米拉日巴及其密宗修持地。西藏野驴和生殖崇拜。缺氧环境下艰难的一吻。圣湖。山南一隅。等等等等。
但关于鹰,他避而不谈。
敦煌集·鸣沙山
1
黄昏的沙丘起伏着。渐行渐远的驼队起伏着。头驼颈项下节奏徐缓而悠长的铃铛声,起伏着……
沙丘的轮廓线,有一种无法描摹的神韵,让我深深沉醉。
2
鸣沙山的落日,仿若乌孙昆莫西行前最后的眷顾。
青眼赤须的乌孙人,告别故土。那一步三顾的怆恻眼神,不正是鸣沙山脊云层缝隙间粘连不辍的落日吗?
何处寻觅去之已远的人喧、犬吠、马嘶和驼铃?目睹此壮美落日的游人之中,可有乌孙和细君的苗裔?
3
流沙没踝。我提着鞋袜、水、相机,随众人一起攀爬——在光与影角力的沙梁上。
流沙漫漶攀爬者烙下的脚印;渐浓的暮色把攀爬者的侧影,剪贴在蓝宝石的天幕上。
风吹沙响。苍白的大漠之月,如此升起——我感觉有一只白色的大鸟,正在附近振翅掠过。
4
在这旷古的黑夜里,在这静谧、布满陈迹的古道——
我仿佛看见那个负笈西行的僧人,在沙丘,结跏趺坐。
我想,我经历了他的孤独,也经历了日出时分:在他身后的沙丘上,喷薄、涌出的辉煌和圆满。
北美笔记
1、光斑蝴蝶
历史上,每项变革,至少意味着要造成15%的被疏远者。他们与另外85%的人群,会滋生某种敌意。
瑞尔森大学,学术委员会坦白、诚实的征询环节,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们的焦虑。
——伊文斯博士端起咖啡。临窗一侧的脸颊上,正好停着一只光斑蝴蝶。
2、时间之仓
枫叶花园,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多伦多队前主场。
这座拥有80多年历史、无数辉煌时刻的球馆,人去楼空。
2011年,瑞尔森大学收购了它。改造时,在地板下面,发现了一只封存完好的黄铜盒子,里面装有球馆的原始档案:一份协议文本。一册大萧条时期北美冰球职业联赛赛事规则。一张多伦多城市日报……一只玉制的小象。它代表什么?直至今天仍是一个谜。
谢尔顿·琼斯先生见证了改造工程全过程。“我们模仿前人,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所在,重新埋入一只盒子,我们把它称作时间之仓。”那只寓意不明的小象,也一并装入。
或许,再过80年,或者更长时间,人们会再次发现它:一只神秘的玉象。一个谜。
“我们以这种方式,封存时间里面的秘密……没有人会去寻找答案,因为,那是只有傻子才会干的事情。”
3、《新年贺信》
DVG酒店房间阳台,不允许吸烟。但可以坐在躺椅上,欣赏枫树树梢稍纵即逝的夕阳余晖。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刚翻到第220页。“那些是什么山?那些是什么河?”停在这一行,没有再翻过去。
迷人的诗句,出自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新年贺信》。青春期的声音。脱皮的声音。
“无论在《花衣魔笛手》,还是在《黄昏集》中,都未曾出现过这个声音,除了那些谈论离别的诗”(布罗茨基)。
“上帝不止一个,对吗?在他上面,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上帝?”
阳台下的草地,草坡上的枫林,虫鸣的声音,仿佛裹在薄薄的雾气之中……
树林背后,楼宇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楼宇顶上,是北美大陆奇丽、深邃的夜空。梦境一般的夜空。
我离开阳台,发现脊背已经湿透。那是春天的安大略湖潮湿的空气,在椅背上暗暗凝结的夜露。
4、南美肤色的男子
那个在当达斯广场出现的高大男子,神形疲惫。
他带着一只装有四个滑轮的大箱子和他的南美肤色。
他斜穿人群,在广场一角的灯柱下停步。
他铲形帽下深褐色的目光向四周巡视。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没有试图去接近他。
我站在广场另一侧,仿佛隔着大洋,欣赏落日下的另一座大陆,一只充满无限倦意的孤独、黄金的老虎……
5、天体海滩
时值正午。西海岸。巨大的天体海滩。
在这里出现的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国别,侧卧、横躺、行走、嬉闹的人们,他们身下的花毯、手边的书籍、头顶五颜六色的气球,以及彼此之间的友谊、外露的性器,都会一一消失。
我们也不能幸免。
但那些粗大圆木、粗粝礁石、神秘洞穴……还是会留下来。
6、传说
UBC人类学博物馆。
巨大的原住民图腾柱之间,年逾古稀、头发荒草般披覆的古塔博士,告诉我:印第安数百个族群,流传着一个大致相近的传说——
他们的先祖,来自浩瀚宇宙另一片星空。他们分别是鳄鱼、乌鸦、熊和雷鸟……身着羽衣,在一个神秘时刻,借星辰之光,从天空降落。降落过程就是一个幻化人形的过程,当他们的双脚,触到北美的土地,最早的印第安人出现了。
我相信,这是我听闻过的最为庄严和神奇的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
我甚至感觉身边的空气,开始缓缓流动。古塔博士的面孔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根根古老的图腾柱发出幽幽荧光和神秘强大的能量,似乎要带着我们,一同飞离这个星球。
7、印第安女孩
在卡佩兰奴。
我看着这些树木和禽鸟。树木高大,树干上生长着彩色的菌类。禽鸟眼神犀利,辨认来来往往的游客。
它们的主人,是一个长靴细腰的印第安女孩,斜坐在树下铁椅上,左侧肩膀,蹲踞着她的鹰隼。
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草木散发腐烂的气息。
她偶一抬头,瞥向人群的眼神,让我悚然心惊。她的美,令人绝望。她的岑寂、焦渴,呼应着我的万古愁。
她来自我不熟悉的地方,但她似乎知道我的来历,能洞见我隐藏内心、秘不示人的秘密。
8、吹牛杰克的咖啡馆
吹牛小街。每过一刻钟,蒸汽自鸣钟就会奏响古老而优美的旋律,带我们回到:一群伐木者、淘金人、搬运工、轮机长、水手、邮差、面包师和一个来自卑诗省的乡村牧师中间。
这里是西海岸的温哥华。这里有上帝的橡木桶。这里的落日和黄昏比地中海、苏格兰的还要美。这里的酒和大麻味道够冲。这里的美人儿来自墨西哥和遥远神秘的中国。这里是吹牛杰克的咖啡馆。
我们都愿意和他喝上一杯。我们愿意伴着管风琴,在昏暗的煤气灯下听流浪汉杰克讲自己的故事。讲伐木者、淘金人、搬运工、轮机长、水手、邮差、面包师和一个来自卑诗省的乡村牧师与他荞麦肤色的恋人的故事。听他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代人的故事。
有人醉去。有人嚎叫。有人在角落昏睡。有人搂着腰身粗壮的陪酒女去了后厨。有人在满地靴筒中摸自己的那一只。有人来到街上。有人摸黑回到码头。有人死去。伙伴们把他搭上板车,送到维多利亚湾残留积雪的山岗。从这里可以看见巨大的趸船,可以看见:矿石和圆木,随着千帆入海。
来源:《新世纪甘南文学作品选·散文诗卷》(2001—2021)

阿信,男,原名牟吉信,汉族,1964年农历十月初一生人,甘肃临洮人。著有《阿信的诗》《草地诗篇》《那些年,在桑多河边》《惊喜记》《裸原》等多部诗集。曾获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第二届昌耀诗歌奖、2018年度《诗刊》陈子昂年度诗人奖、十二背后•梅尔诗歌奖年度诗人奖、第二届屈原诗歌奖等奖项。现任职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