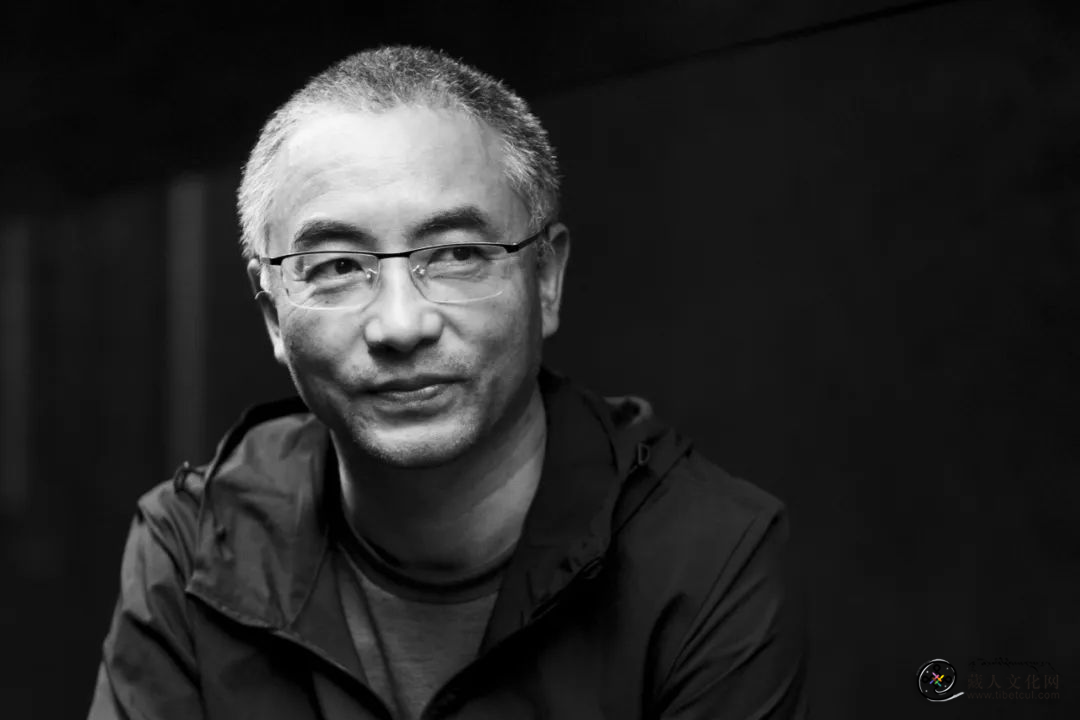在群星璀璨的80后同代作家中,甘肃藏族青年作家何延华的创作产出量并不算大,风格标识也不是特别突出,但她无疑属于那一类默默探索、经得起阅读、需要在阅读中去不断发现的作家。近年来何延华先后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嘉禾的夏天》、中篇小说集《寻找央金拉姆》就有这样的特点,一旦开卷,就放不下来,总想知道她的下一篇小说写的什么故事。的确,何延华是一个注重创新,很少重复自己的作家。尤其是2023年出版的《寻找央金拉姆》收入的六个中篇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新的题材、新的角度、新的写法,使得整部小说集有一种整体的冲击力。
但即使如此,何延华仍然始终保持着自己明晰的方向感,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去书写以自己的家乡为原点的一个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域空间里尚未被现代主流叙事所关注到的人们的生活。这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受过良好的文学人类学知识谱系训练的学者型作家何延华在这里发现了一座题材的富矿。从她已发表的一系列小说来看,一些题材方面的发掘似乎正在展开,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于小说叙事的可能性的探索也才开始。新近完成的中篇小说《河边的秘密》,是集中体现了她的创作变化的作品之一。
何延华以往的题材都集中关注有浓郁多民族地域特征的农村生活,她擅长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呈现重大的现实主题,诸如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底层的生存状况等,通过小说中一个个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去表现社会进程中农牧民的生活状况,或价值伦理的变迁,或揭示人性的善恶冲突及其复杂性,或抒写乡村生活以及大自然中蕴含的无尽诗意等等,并使它们成为带有何延华个人风格的“中国故事”。在这些小说中,何延华的叙事线条是硬朗的,叙述方式是强有力的,带给人的除了观念、情感层面的叩问之外,叙事本身也具有特别的冲击力。她擅长呈现故事冲突,善于刻画人物形神,注重营构戏剧性效果,因而她的叙事有时大开大合,有时曲径通幽,但她对叙事进程和节奏总是有一种力度恰到好处的有效掌控,她的叙事语言有时简洁、充满活力和爆发力,有时铺陈、细腻且富于体察性和寓意。小说集《嘉禾的夏天》《寻找央金拉姆》中的大多数作品属于这类风格。
但在《河边的秘密》中,何延华的叙事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特点,即通过故事的淡化、叙事语言的诗化、小说意境的审美化去营造某种精神境界或理想世界,使小说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诗意氛围和透明、纯净的童话特质。这似乎是一种新的美学追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某种“变化”或“创新”。
一
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在何延华发表于《飞天》2016年第12期的中篇小说《寻找央金拉姆》中就出现了。相对来说,《寻找央金拉姆》的题材比较柔和,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甚至没有任何对抗性冲突。小说的主要叙事线索是一个乡村金匠家的小女孩因幼年的高烧而生理性失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也无法融入正常的儿童世界。在偏远农村,这绝对是一件不幸的遭遇。但小女孩和她的父亲没有放弃希望,他们踏上了寻找传说中的传奇歌手兼神医央金拉姆的旅程。小说的结局是寻访央金拉姆而不遇,但小女孩在旅途中遇到的善良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大自然的启发而学会了发声,重新开口说话。小说突出的是关于信念、信仰的追寻,描写的是一个充满爱与美的童话般的理想境界。由于故事的淡化,这是一个难以展开的题材。但何延华另辟蹊径,在现实之上,强化精神活动的力量和意义,突出爱和信念,勘探生命的内在潜能,去探索对超验性题材的书写,从而在乡土现实主义中找到了另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小说的叙事语言与大自然一样充满诗情画意,小说情节的单纯导致的阅读冲击力的不足,在作者富有激情的叙事中得到了提升,叙事语言也升华了小说的思想境界。这是一种超越性写作,无疑可以称之为一篇成功的诗性小说。但《寻找央金拉姆》在何延华的创作中尚属于为数不多的探索性写作。
《河边的秘密》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了《寻找央金拉姆》的风格和题材探索,这又是一部故事情节被有意识淡化、外在冲突被有意识弱化的“轻软”小说,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一个“内在世界”的小说,但小说主题的意义却不亚于何延华以往的其它重要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试图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深处,去勘探淳朴人性中的本能冲动、破坏欲、错愆意识与乡村伦理中仁爱、向善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并把它上升到对于万物伦理、生命生态书写的高度。
二
《河边的秘密》的情节主线并不复杂,通篇的叙述者“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儿童,小说开场是一个普通农户人家春节前夕的热气腾腾的早餐场面,“爸爸”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闲谈“巴麻村的老木匠病了,听说快不行了”,引出了故事的开端。“爷爷”带着“我”去巴麻村探望他的老朋友、重病中的老木匠。去老木匠的家要经过北藏河,河畔的老柳树上的斑鸠鸟窝引起了“我”的遐想和不可遏止的好奇。“我”从两位老人的交谈中得知了两位老人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知道爷爷曾经做过对不起老木匠的事,最后一面想求得老木匠的原谅。在回家的路上,“我”借机离开爷爷的视线,爬上河边高高的的老柳树掏了斑鸠鸟的鸟窝、鸟蛋。“我”还目睹了经过河边的一些人,在冰封的北藏河上参与了救助落水的傻女人,放生了关在药瓶里的小黑虫……小说结束的时候已是夜晚降临,“我”回到家里,一天的经历让“我”疲惫而兴奋。此时山村寂静,家中炉火正旺,村子里有女婴降生,而邻村的老木匠正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走向人生的结局……结尾作者写道“多么殊胜,吉祥的夜晚啊!马上就是新年了。”
这是一部挑战读者阅读习惯、也考验读者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小说,从看似淡若无骨的叙事中,几乎难以提取一个硬朗的主题。随着少年懵懂而好奇的眼睛,“河边的秘密”薄雾般聚拢而来,那是两位老人的往事秘密?抑或少年与鸟窝的秘密?还是村人、村庄的秘密?还是由这所有的事物共同构成的秘密?
可以说,小说的意境是飘忽、迷蒙的,但文本的叙事是敞开的,如果把小说的各个部分串连起来,就会看到居于中心的主人公是“我”,这是一个关于男孩成长的故事。一天之内,作为叙述者的少年先后遇到了不少人和事,也包括虫子和鸟,从他(它)们的身上他初次认识了衰老、死亡、挣扎、以及新生等许多事物,虽然少不更事的他与这些沉重的人生问题仿佛始终隔着一层“毛玻璃”,但他已经感受到来自这些事物的某种震慑灵魂的气息。少年成长的内驱力来自对于世界与自我的认识,认识自我的契机则是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这是属于成长的“秘密”。
首先是对于“死亡”的认识。在从老木匠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对“死亡”有了朦胧的认识。“我不放心地瞅着爷爷,生怕他突然变成一个怪物。啊,刚才,我已经隐约触摸到了操纵生命与死亡的秘密电流。”……“另一个世界,爷爷说充满了永恒的安详和快乐。他说另一个世界的时候,还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懂,我的聪明有时连我自己也感觉惊讶。于是我带着这个词沉甸甸地行走,我的眼前浮现着一些可怕而瑰丽的景象。”一老一少,达成了对于生死感悟的契合,完成了乡村生死观教育的第一课。同时小说中似乎还并置着另一条若隐若现的叙事线索:对于农村老人的“衰老”及临终状态的某种观察和关怀。
而这一成长中,更重要的还不是勇敢,而是“认错”意识。
小说中的一条主要线索是:老少两代人“河边的错误”。爷爷的过错是“出手伤人”。青年时代,处在恋爱竞争中的爷爷,出于嫉妒,为了“教训一下”情敌,而失手打断了好朋友老木匠的鼻子,使他毁容,并成为终生的残疾人。由此,导致了爷爷的终生悔恨。“唉,年轻时候的感情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冲动,更致命。”“男人间的竞争是多么可怕呀!”“那时的我自私,本想教训一下他,没想到差点失手要了人家的命。”这一事件给两位老人造成了终生的影响:“爷爷”一生背负着负疚与忏悔的精神重荷,老木匠虽然“认命”了,但难免怀着欲罢不能的怨恨。
少年“我”的过错是“掏了鸟蛋”。“我”战胜不了好奇心的冲动,掏了鸟窝,拿了鸟蛋,又不小心造成鸟蛋的破碎和幼鸟的死亡,还打伤了斑鸠的翅膀。“……也许这只是一份儿童兼具偷猎者和喜欢探索未知事物的激情——总之,我对鸟窝和鸟蛋着了迷……”“这乡间小路上走着一个正准备干坏事的小孩。”这是“我”的无心之过,但“我”隐约意识到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内心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忏悔之情。
关于老少两代人“过错”的叙事意义在于:人在一念之差的支使下,往往容易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而微不足道的点滴小事,却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类似的很多事情,具有因果的普遍性。作家把这些都归结为青少年时期不可遏制的激情冲动带来的后果。这似乎与作家对于人类本能、无意识等理论资源的征用有关,其中突出了人的本能中的攻击性和破坏欲。但作家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这种心理:“我觉得我今天遇到的那些人和事,好像都有错,又好像都没错。我不知该怎么和爷爷谈这些。这些话题是那么复杂,那么难于讨论。它们都有一个类似于童话书上‘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头,也许要一直追溯到人类的第一个祖先呢。我不知该怎么描述它们。
“爷爷沉思了一会儿。他答非所问:‘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说真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深藏在人类心中的良知。’”
对爷爷一生的忏悔的体察,对幼鸟过冬问题的担心、对装在小药瓶里的小黑虫子的牵挂和怜悯,则说明“善”的意识已经在“我”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回应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在人性基因中的振荡。这是驱使人类“向上”的力量,既是传统“性善论”的体现,也与乡村古老的自然伦理有关。
小说中,一些与主要情节无关的人和事物的出场,如勤劳的阿妈,落魄和潦倒的返乡中年男人、快活而风流的接骨匠、邻村的傻女人、开着白色小汽车带着全家人来河边放风筝的城里人等,都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个窗口,对“我”的成长十分重要。而傻女人不慎失足落水,“我”下意识地扑到河冰上奋力去救人的场景,升华了“我”对生命的终极认识,完成了“我”从少年到“男人”的成长。
因此,这部小说既可以看做是一部儿童小说、成长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一部意识流小说、心理分析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是成立的。
三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一个地方的生活是一张意义之网,而生活的意义就藏在日常的细节里,它联结着所有的古老观念、深层心理,从而构成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生态。这部小说,就是借助一个独特视角,深入到习焉不察的细节里,去挖掘日常生活的褶皱深处的精神意义。
比如地方性的生命观念的体现。少年“我”的过错在于:掏了鸟蛋,打伤了斑鸠的翅膀、把带翅膀的小黑虫关进了药瓶里等等。在乡下,“鸟蛋”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掏鸟窝、偷鸟蛋不过是儿童的一种淘气行为,往往被看做是诸多童年游戏中的一种乐趣。但作家延伸了“鸟蛋”的生命伦理意义,因为它是孕育一个新生命的容器。作家让“我”在拿了鸟蛋,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同时,感知到了其中的生命意义,于是这就不再是一个游戏行为,而变成了事关一个生命生死的决定。于是接下来对于鸟蛋的处置,就具有了神圣仪式的意味。而我的“过错”感,来自于其中一只鸟蛋不小心被碰碎。在生命的意义上,这过错感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在“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应,甚至出现了幻觉。在“我”的幻觉中,北藏河河神、柳树神、鸟神一一与“我”对话,尤其是“这时河神说话了。他把自己的秘密倾诉给了我。”,河神承认自己也犯过错,并把过错看做是追求自己的目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小说结尾:“爷爷笑了。他把我紧紧搂进他嶙峋但温暖的骨头里。他说:‘格来,世上万物都是有情生命,连蚂蚁,蚊子,苍蝇都不能伤害,因为它们或许是我们前世或来生的父母。’……‘格来,你要善良,慈悲,要有一个好心肠。好心肠,是一个人身上顶好的东西。’”因为身在大自然中,乡村儿童的许多淘气行为都攸关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动物生命,因而这也是一种地方性的生命教育方式。从忏悔到认错,再到对于万物的体恤、悲悯之心,这是一个人的成长中自我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
小说中的这些源自地方传统的古老智慧,比如生死观,善恶观,错愆意识,众生平等、万物有情等观念,呈现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生态观念世界,具有乌托邦气息。
地方性知识的介入,还在于作家调动了民间故事的叙事资源,在有些叙述部分,用一种民间故事的程式化叙述模式,代替了部分事实叙述,比如在爷爷给“我”讲述他和老木匠青年时代的冲突的起源时,在讲到他们俩如何同时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如何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的过程,作家就借用了这类模式化的桥段。这应该是对大量无关紧要的叙事内容所作的一种技术性处理,虽然叙述有些草率、夸张,但也填充了过渡性环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叙事手法。
还有大量的民俗、地理物象介入叙事,小说中的一些饮食起居细节,带有明显的西北藏汉结合地带农牧村的生活特色,增强了叙事的的魅力。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雷帝雪山”,作为人文地理标识,提示读者关注小说中人的生存环境,也作为精神活动的一种空间背景,与信仰、崇高、神圣的观念相关联。
四
小说写了一个儿童的一天。小说所采取的限制叙述视角,是西北藏汉结合地带的农牧村生活环境里的一个懵懂、天真、好奇的孩童视角,它提供了一个纯粹原生态的视阈。在孩子眼中,这一天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早餐、家人的对话、院子里的风、北藏河、河边的柳树、两位又是朋友又是冤家的老人的聊天、一天中见到的所有的人和事……仿佛作家用这个孩子的眼光把所有的事物都擦亮了,召唤出了一个宛如刚刚诞生的新世界。你必须贴着叙述者的体验、认知、思考层面走,才能理解小说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及其意义。逐渐的,你和少年一样,体验到连续不断的与陌生、惊讶、发现,体验到成长的迷惘和世界的坚硬。作家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营构了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诗性充沛的小说时空,由此,在叙事上带来了许多新的特征。
小说中对自然景物乐此不疲的铺陈式描写,表现出无穷无尽的观察热情,甚至给人略显过度之感。但这并非是语言修辞的失控,而是有意识为之:一方面符合叙述者儿童角色特点,另一方面与作家的自然观念有关,体现为对“物”的一种理解和态度:赋予“物”以某种动感,唤醒其生命属性,让“物”的语言加入到叙述语言中来,使“物语”转换为叙事中的某种思想、感情。
首先,让无生命的物质加入进来,赋予其形态、动态、神态,成为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小说的开头部分,写新年的氛围:“大铁锅蒸气升腾,香味快要把房子抬起来了。”整部小说中这样的描写非常多,出现在她笔下的这些事物往往富有精神意义。作家还赋予事物以某种“行动能力”,使其完成许多叙事动作,如:“六七层内衣毛衣和一件厚厚的黑棉衣裹着他的老骨头走了,他的咳嗽和我在后面跟着他。”“她的黑色皮鞋上有一朵白色的小花。当她的脚碰到河沿边的薄冰时白色的小花大吃一惊。我听见那花朵的呼救,微弱而颤抖。”……在作家笔下,一切物象仿佛都活起来了,它们具有自身的行动能力,独自构成一个叙事景观,甚至干预作家的叙事动作。这样的句子除了带给读者语言的新奇体验之外,还有重要的意义:它使物质内在于人之中,物质成为人生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物性成为人性的一部分。进而言之,它也与作家的万物观、世界观有关,即拆除人与自然、与环境的内在藩篱之后的生命的敞亮、自在与惊喜。
特别是在小说第九节,我掏了鸟窝、偷了鸟蛋后,在路上听到口袋里的两只鸟蛋在“交谈”的场景,更是把小说中的叙事声音扩大为万物参与的和声与交响,众生平等、生命珍贵的意味更加强烈。
其次,是在一些关键环节,让物象发挥重要的叙事功能。在老木匠家。这是一个重要场景。这一部分是两位老人之间断断续续的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对话,但二人之间的每句话都有具体所指,也映射出二人当下的心理活动:爷爷虽然长期心安理得,但此刻却处在愧疚、忏悔的煎熬中,坐立不安;老木匠眼中虽然依旧闪烁着仇恨的怒火,但他的内心却是平静的。这部分的叙事充满内在的紧张感,场景的氛围是异常沉重、压抑的,但作家用“一根柳树枝”十分巧妙地打破了这一僵局:
“慢慢地,老木匠的眼里聚拢起两团怒火,像深夜野外来源不明的火光那样明亮,闪烁。……病人的眼里全是仇恨,就连我也感觉到,正是仇恨的日子为他的生命注入了力量。
“他还想说什么,被爷爷打断了。爷爷叫我把那根柳枝拿过来。我把柳枝举到病人脖子边的大红花前。”……“老木匠的眼睛闪过一道光,很快又熄灭了。”……“他接过柳枝,凑到他闻了一辈子木头香的残鼻前闻了一下,又闻了一下,接着手臂倏然滑落。他气喘吁吁,发出几声婴儿般的咳嗽。” ……“‘人生就像这柳枝,到最后,干枯,什么味儿也没有。’老木匠说,……爷爷大声说:“‘怎么没有,老骨头里犟味儿还有。’
“于是他俩都笑了。老木匠的笑在嘴里无声地逛荡了一两下,爷爷被自己逗得几根胡子一翘一翘的。”
在小说前面的情节中爷孙二人走过北藏河畔的老柳树下,淘气的孙子爬上大树顺手摘了一条树枝,这看似闲笔的小细节,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虽然爷孙给病人买了不少慰问品,但这根树枝却是他们无意中带给老木匠的最珍贵的礼品:摘自老柳树的、带着春天气息的新鲜树枝,既是对老木匠一生钟爱的职业的最好安慰,也唤醒了他新旧轮回、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这足以平息他内心结痂的伤疤一样陈旧的仇恨。在这里,“柳树枝”的物性叙事的功能是语言不可替代的。
一些物象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其中,“北藏河”意象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在时间的意义上,它是乡村伦理传统绵延不绝的象征,它像唯一不死的无形长者,代表着终极伦理价值标准(许多终极审判就发生在河边)。但它把沉默作为唯一的语言,让河畔来来去去、世世代代的人们用心去感悟。在空间的意义上,它是许多人性秘密的目击者、见证者、收集者、藏匿者。它的浑浊、沉默既有同谋的性质,也有警示的威严。它是倾听者、也是对话者。它有暴怒、惩罚、毁灭的一面,也具有洗涤、抚慰、疗愈、救赎的功能。
热爱描写和比喻,是自荷马史诗以来的文学所保持的一种古老热情。对万物的好奇心是人类永远的童真天性,它表现为一种叙事的活力和经验的新鲜感。诗意感受的空前释放和铺陈,诗性书写的恣肆狂欢,是这部小说的一种语言特点。小说中大段大段生动的自然描写,带来大量鲜活的物象,它们自动介入叙事,使其具有人类学小说文本的丰富生命质感。
五
《河边的秘密》在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普遍意义之上,探讨了人的动机、行为与后果之间可能性的的错谬。在由行为和习俗累积而成的乡村文化惯性中,这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问题。而小说借用一种童真思维,重新打捞出这个话题,用一老一少的精神活动,来展开言说,似乎有传统和当代对话的意味。作者是否意图探索重建乡土善恶标准、生命伦理观念,从而重构一种全新的自然、文化生态的可能性?在当代乡村文化语境中,这样的思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考察何延华的创作,相对于《狼虎滩》《三月之光》《拉姆措和栓牢》《寂静的雪山》等描写生死疲劳题材的“硬叙事”小说来说,《寻找央金拉姆》《河边的秘密》这类描写爱与理想主题的小说无疑属于“软叙事”了,这类“软叙事”小说在何延华的创作中并不多见,但它似乎预示着她对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是否可以延伸“物性叙事”的边界?是否可以用诗性语言增强叙事效果?无论如何,这些都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创新元素:在现实主义的书写中,依然可以有效开掘主题的超越与叙事的拓展的向度。
原刊于《飞天》2022年第12期

安少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散见于《诗刊》《民族文学》《文艺报》《飞天》等报刊,著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域文本实践:新世纪甘南作家多元创作论》(民族出版社2020年),《甘南乡土文学导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曾获第二、三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第五届格桑花文学奖。现任教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