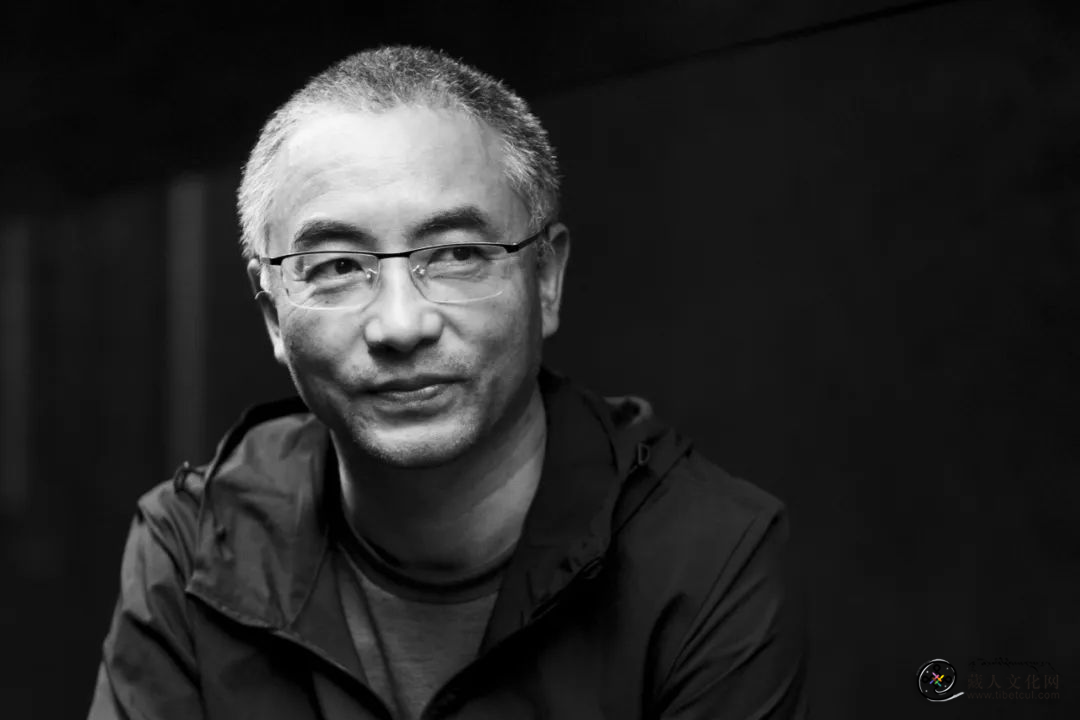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摘 要】严英秀是当代甘肃作家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位作家,作为一位藏族作家,人们似乎在她的作品中很少发现想象中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严英秀创作中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创作风格上与欧·亨利表现出的近似性和她创作中的女性主题,但是不论是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还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都体现了严英秀对爱与美的一种坚守,对良善的道德向度的追寻。这种坚守和追寻恰恰证明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藏族”的严英秀其实文学创作的文化之根依然是她的母文化——藏族文化。
【关键词】 严英秀;小说创作;外来影响;文学之根
严英秀作为一位出身藏族却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女作家,在创作上体现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作为一位藏族作家,人们似乎在她的作品中很少发现想象中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也就是说她似乎是藏族作家中并不那么“藏族”的一位作家。作为大学文学院的老师,她熟悉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通过大量的阅读,她将这些营养融入自己的思想与创作,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她有很多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比如法国作家杜拉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曾说:“我很喜欢杜拉斯,着迷于她的个人魅力。”[1]
严英秀创作中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创作风格上与欧·亨利表现出的近似性和她创作中的女性主题,不论是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还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都体现了严英秀对爱与美的一种坚守,对良善的道德向度的追寻。我们在此讨论严英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想说明,看起来并不那么“藏族”的严英秀其实文学创作的文化之根依然是她的母文化——藏族文化。
一、严英秀与欧·亨利小说
在《面对无穷的可能,和缺陷——作家严英秀访谈录》中,胡沛萍提出严英秀的小说与欧亨利的小说有一些相似之处,“我的第一感觉是,您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这一点上,您的作品与欧·亨利的小说有一些相似之处,非常讲究构思与叙事的曲折变化。接下来的不少作品多是有着同样艺术效果的精细之作。我感觉您非常在意小说结构的营造和设计,喜欢制造悬念。”[1]1此外,暨南大学的教授姚新勇也这样评价严英秀小说:“严英秀较为巧妙地采用了复调的叙事或嵌套式的结构,增加了小说层次的丰富与复杂,也使得一些故事的结局,具有了欧·亨利小说的结尾的魅力:出人意料、戛然而止、又意味深长。但从小说故事叙述的整体感觉来看,又不纯然是欧·亨利男性叙事式的紧凑、干练,而是不无机妙的谋篇布局,与张爱玲式的从容、怅然、隔世之感相契合”。[1]1虽然严英秀本人对于欧·亨利对她的影响并没有明确的认可,但是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确实读到了她和欧·亨利在文学上相近的特点。
(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
欧·亨利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他的作品短小精悍,结构精致紧凑,富有悬念,故事情节简约而富有深意,代入感极强。他的小说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很多小说都抨击了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贫苦大众在生活面前的无奈与爱的挣扎,小说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
欧·亨利的小说往往以出其不意的结局而取胜。他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等作品,更是将这种反转性的结局运用得炉火纯青。《警察与赞美诗》中,主人公苏比为了度过寒冷的冬天,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将过冬的目标选在了监狱。于是他成天惹是生非以引起警察的注意,好让他可以顺理成章地进监狱。然而他做了一系列荒唐可笑的行径之后并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最后当他听到教堂里传出的悠扬的赞美圣歌时,他幡然醒悟,决定重新振作起来,与命运搏斗,堂堂正正做人。可就在这时,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当成不法分子送进了监狱。当读者都以为索彼会痛改前非,暗暗为索彼即将过上好日子而窃喜的时候,警察的出现打碎了索彼的梦,更打碎了读者的心,不禁让我们为之惊愕叹息,而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反而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同时也惊叹于作者构思的独具匠心与叙述的高超技艺。《麦琪的礼物》这部大家都熟悉的小说中的“意料之外”的结局也让读者目瞪口呆,一种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深刻地展现了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境遇以及患难见真情的真挚爱情。
这种反转性结局的在严英秀的小说中也是俯拾皆是。《纸飞机》讲述的是校园爱情故事,小说中,大学生阳子爱上了年轻的老师剑宁,看到老师一家幸福美满之后,她将自己的爱埋在了心底,艰难地守护着自己的初吻,也守护着别人的幸福。可是在十二年之后,阳子得知剑宁背叛了妻子萧波,阳子在自己守护了十几年的初吻中杀死了剑宁。这是一个唯美又残忍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落入“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俗套,故事在阳子的“复仇”这种反转性情节中戛然而止。故事结尾阳子杀了剑宁,乍一看给人一种突兀甚至不真实的感觉,但是认真阅读作家笔下塑造的阳子这个人物,就能理解作家的这个结局安排了,也就是说阳子的性格也只能导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个结尾设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细细品味,就会发现阳子身为一个女人,如何做到十几年不让自己的初吻受到侵犯,别忘了,她已经结婚了。那么,结尾处她杀剑宁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了。极致的叙事、极致的人物,最终导向极致的结局。十几年对爱的坚守原来是一场骗局,这该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在心理上是近乎毁灭性的灾难。而作者设计的这种反转性的结局让人在大跌眼镜之余,也体会到了阳子那种爱之深,恨之切的无限凄凉。
如果说《纸飞机》是一部严英秀自己所说的“特别的作品”的话,《被风吹过的夏天》中以董一莲的一个梦开始,梦中董一莲与何染是宁死也不分开的一对爱人。现实中,董一莲已经结婚,何染是她有一次去南方开学术会议时认识的,这之后,董一莲与何染陷入了异地鸿雁传书式的难以自拔的爱情当中,甚至为此她向丈夫提出离婚,自己也日渐消瘦。当这种彼此不见面的爱情终于盼来了两人见面的美好画面时,何染的到来让董一莲发现她根本无法和何染实现灵与肉的真正结合。小说结尾这样写道:“还好,谢幕的时候,一些花儿还好好地挂在枝头,那最后的谜底里埋着的狰狞,那曲终人散时的真相来不及发生,使一切看上去像极了爱情。”[2]严英秀就是这样敲碎了读者习惯性的大团圆思维,以自己独有的笔法实现了文本之中的情理之中和文本之外的意料之外。可以说,严英秀以这样的结构处理实现了她在爱情书写上的独特性,更多了一份理智的思考和人性复杂性的呈现。
(二)圆圈式的叙述模式
严英秀的小说在叙述上也喜欢采用圆圈式的叙事模式,小说的整体结构曲线呈现一种“圆圈状”。《苦水玫瑰》这部小说,第一章开头就写到了周俪是夏京蕾在巴镇唯一的朋友。“我和夏京蕾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个。”[3]这是夏京蕾第一次来到巴镇饱受欺侮时周俪对她的承诺。在后来十年的时间里,夏京蕾拼命想要离开那个可怕的深渊——巴镇。为了参加成人高考,她受到了非人的遭遇,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人生的那个圈圈,又回到了巴镇。“巴镇——枣沟——巴镇”这十年的兜兜转转,这十年的心酸苦难,这十年的爱恨纠缠,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作品的结尾她和周俪“以十年前的姿势再一次走过巴镇小小的街头。她们飞动飘逸的身影,勾出了小镇深处一串长长的目光”。[3]459就像十年之前一样,周俪还是她唯一的朋友。这种圆圈式的布局不仅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完满,它背后更是揭示了平凡的人在社会的恶面前,就像是在一潭污水中丢入一颗石子一样,泛了几圈涟漪随即又恢复平静,给人一种无以复加的孤独感与深重的绝望感。幸而,作者手下留情,最后并没有让夏京蕾放弃参加成人高考的信念,这也寄予了读者一种斗志,即使现实再不堪,梦想也是要有的。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命运之路》开头就引用了戴维·米尼的诗:
走上许多条路,
我寻找着命运。
忠诚的心,力量,再加上爱,
它们能不能使我
指挥,逃脱,摆布或者改变
我的命运?[4]
在作品中作者这样写道:“路在月光下半明不暗的平原上延伸开来,长九英里,直的像用犁耕出来的,镇上的人都说只是直通巴黎,诗人一路走一路默默念了又念这名字。戴维至今没出弗洛伊远行过巴黎。”小说中的戴维是一位喜欢写诗的放羊人,在与妻子伊凡娜发生争吵后,他便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天下,去实现自己的诗人梦。诗人一边走,一边嘴里还不时念着巴黎这个名字。作者戏剧性地给他安排了三条路:左岔道、右岔道、主干道。在左岔道和右岔道这两条路上,戴维分别遇到了两个女人,并且分别爱上了她们。而在这两条路的这个瞬间,作者都写到“他一定是个诗人没错,伊凡娜已被抛诸脑后”。最终,戴维在这两条路上都因为女人死于侯爵的枪下。
作者给戴维安排的第三条路是让他回归妻子伊凡娜的怀抱。刚开始日子过得不错, 可是有一天,大卫从关了很久的抽屉里抽出纸来,又开始咬起铅笔头来了。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多,羊儿却越来越少。作者又一次写道:“他一定是个诗人没错,伊凡娜已被抛诸脑后”。最终,这条路也没有完美地走下去,在戴维的诗遭人否定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窗,选择了开枪自杀。而结束他生命的那把枪,也是来自侯爵府。
欧·亨利给戴维一共安排了三条人生之路:往左的路——和博贝尔杜依侯爵决斗被枪杀;往右的路——中了博贝尔杜依侯爵的子弹身亡;当中的路——买了印有博贝尔杜依侯爵徽号的枪自杀。作品开头写到:“弗洛伊不是他的久留之地,这儿没一个人与他志同道合。”最后诗人戴维就和严英秀笔下的夏京蕾一样,他下定决心要离开弗洛伊,但是“戴维至今没出弗洛伊远行过巴黎”,他最后依然回到了原点。
由此观之,欧·亨利在这个圆圈式叙述模式的设置上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他在对人物命运的圆圈式叙写上比严英秀更决绝。在他笔下,戴维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一样,无论怎样,最终都无法逃出命运之轮——死亡。但是,他又与俄狄浦斯王不同,俄狄浦斯是试图改变自我,但难以逃脱超自然的命定之运。而他,无论给予多少条人生道路,最终都会走向同一条道路。这种“起点——原点”的圆圈式布局,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叙述技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考量。
(三)小人物的书写
严英秀和欧·亨利小说除了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外,在作品题材的选择上也体现出一定的相通性——他们都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喜欢写小人物的故事。
欧·亨利的作品大多描写社会底层人物,他利用小人物来彰显大社会,揭示了在美国社会的边缘挣扎生存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讽刺了美国当时政治制度的黑暗。在《警察的赞美诗》中,像索彼这种小人物他的生死大权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他在寒冷的街头流浪时的漂泊无依,他走投无路时的痛苦,都给人一种极度的孤独与绝望。再如《麦琪的礼物》中的贫苦夫妻,为了对方卖掉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却发现换来了最无用的东西,作者以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的笔触,既表现了底层人物面对命运时的无奈,同时也体现了底层人们内心的善良和温情,让我们在悲叹他们命运的同时又被他们彼此深沉而又真挚的爱所感动。
在严英秀笔下多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命运。《苦水玫瑰》主要讲了女主人夏京蕾公自小在巴镇非正常人的苦涩生活,因为爸爸的病,全村人表现出的嫌恶,还有老流氓的调戏,好朋友的被迫“背叛”,都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于是家破人亡之后,她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成人高考上,拼命想要逃离这个罪恶的深渊——巴镇。结果造化弄人,兜兜转转十年之后她还是回到了巴镇,这期间她不仅遭受了欺侮,还被冤枉勾引男人,她的苦楚根本无处申诉。在那个封建又封闭的小镇,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她却只能再一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五年之后的成人高考上......她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悲剧,她代表的是底层知识女性的悲剧,作者借助这个故事表达了对男人的厌恶,对这个不公社会的愤慨,更是对底层知识女性没有出路的一种申诉。
《玉碎》围绕在工厂改制中被迫下岗的普通职工郑洁的生活而展开。她和丈夫极力想改变生活现状,为了生活他们勤劳而又努力,但是依然难敌生活猝不及防的打击与灾难。自己生日那天郑洁去商场想去看看一直以来自己喜欢的一只玉镯,却不小心将那个价值不菲的玉镯掉在地上摔碎了。“玉”哗然碎裂时,郑洁一直以来的美好的梦与残酷的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高潮,玉碎的声音既是物质时代对郑洁当下贫困生活的嘲笑,也是残酷的命运对她惨淡人生的嘲弄,更是郑洁对于美的追寻的戏剧性的毁灭。小说以“玉”为核心意象,既写到了郑洁小时候看到的奶奶送给小姑的玉镯和玉镯最后的碎裂,又写到了当下郑洁对玉的执念和商场玉碎的境遇,对于郑洁来说,曾经的“玉”,是美丽善良的小姑的锦绣年华,是郑洁自己的诗意旧梦。而现在的“玉”,则是展柜里遥不可及的昂贵饰品,是直击她生活现实的残酷利器。严英秀以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物质社会中底层社会个体存在的卑微与渺小。
在《一直对美丽妥协》中主要讲了一群在美容院打工的女性。无论是心高气傲的丽英,还是情路坎坷的若若,她们都在那个美容院打拼着,做着出人头地的美梦。可是在现实面前,她们的生活并没有越来越好,有钱的生活依然遥遥无期。最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翠子的妹妹金子——一个保姆,惨死在青天白日之下,翠子上北京伸冤,杀人凶手却告诉她:“你丫的一个乡下小妞,我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你信不信?”[3]185对于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她,拖着自己小小的身体在城市里爬行,“公、检、法、媒体,她所有以为可以信奉可以仰仗的力量,好像在这个世上都不存在了似的,她找不见一点小小的支撑。”[3]186最后她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准备寻死的时候被美容院的姐妹们所救。这么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起眼的打工妹,在自己生活拮据的情况下,大家凑钱救助翠子,有的人甚至将自己的结婚钻戒都拿出来了。就像《麦琪的礼物》中的贫困夫妻一样,她们互帮互助,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彼此。两个作者借此在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又彰显了普通人之间存在的温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严英秀小说与女性主义
严英秀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很明显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影响,但是她又不拘泥于女性主义的拘囿,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思考。
(一)男性批判的主题
严英秀作为女性作家,她曾多次借用戴锦华的话:“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由于我生而为女人,女性主义就不可能不是我内在的组成部分”。[5]而在访谈中她也这样说:“我得承认我的许多篇小说都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立场,我是一个女性,我做不到超越性别,我必然地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对女性的种种不公、挤压、盘剥、展示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弱势境况,揭示男权文化的无处不在。”[1]5由此可见,严英秀作为女性作家,是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她在作品中通过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肯定,隐含了男性批判的主题,尤其是她早期的创作。
写于早期的《1999:无穷思爱》这部作品主要写了发生在校园的爱情故事——师生恋,小说中女学生栗恋上了男老师桑。整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的,“我”作为栗的好友,见证了他们的恋情,见证了栗义无反顾的付出,也见证了桑对栗的伤害与抛弃。正如原文中所说:“我这才知道,关于栗的爱情,其实我比栗更深刻地压抑着,因为站在故事之外,对桑的光华,对桑的爱栗,我也许看得太清。因为爱栗,对她的所有,我感同身受。”[3]226“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讲述了栗的爱情,又将回忆拉回到现实中我的生活——糟糕又充满热情的三十岁。又在其中穿插了漫漫岁月中我的女友在所谓的爱情面前一一失败的故事。于是“我”站在今天的时光中,回首过去的纯情年代不禁感叹。 在谈到这部作品时严英秀曾经这样说:“《1999:无穷思爱》对我来说,更像是对青春年少的最后挥别。那种意味,至今缭绕不已。这篇作品,它不太像小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是我后来很多篇小说的母体,因为,关于女性的友情,爱情,事业,家庭,关于付出,伤害,关于挣扎,妥协,关于破碎,救赎,凡此种种,《1999:无穷思爱》都试图做出自己的思考和表达。”[1]4-5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早期作者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也确立了她早期创作中的女性主题。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这样写道:“我们所找到的男人,也许往往只是我们身体的伙伴,生活的伙伴......他们要我们包揽家务,温柔贤惠,全然献身,无怨无悔。他们男人,永远不懂我们女人的心。我们寻找的同类,永远只在我们女人自己中间。”[3]215-216这段语言深刻揭示了男人在女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俨然一副主人的架势,“塑造”着女人,使之符合自己的要求,之后他们便站在高处享受生活。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过,如果没有男人,女人就是一团散乱的花。是男人将这些花插进花瓶,修剪枝叶,使之符合自己的审美,然后就再也不去理会,直至凋零枯萎,积落尘埃。细读《1999:无穷思爱》整部作品,作者对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对男性的批判随处可见。
“我们想不到,独一无二的爱情最终使我们变成了千篇一律的人。女人,花一样的女人,谜一样的女人,经过婚姻的调教,个个像出自一个模子......我恍若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往事,甚至没有了独立的话语。”[3]225-230这段叙述将女性“他者”的地位凸显得更加清楚,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女性是必须经过男人调教的,调教过后的女人便完全失去了自我和自主的创造意识,成为完全的屈从者。
《1999:无穷思爱》中,不管是“我”还是栗,我们都深深地爱着一个男人,为了他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变得温柔贤惠,甚至全然献身,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卑微的存在,才使得男人的气焰愈加嚣张,他们把自己置于“主人”的地位,对女人颐指气使。作家由此指出了女性的一步步妥协所造成的结果,从“我恍若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往事,甚至没有了独立的话语”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种看似表面和谐、波澜无惊婚姻生活背后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与所忍受的压抑的自觉认知,于是,她借助小说发出呐喊:“我没有了独立的话语——我想要话语!”
《1999:无穷思爱》这部作品诞生在二十世纪末期,第二次女性运动的高潮刚过去不久,这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揭示表面上的男女平等背后所隐藏的不平等的社会真实状况。然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还需要时日,因为男女的不平等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原因外,女性自身的觉醒是最根本的,就像作家笔下的栗和“我”,她们妥协之后的处境更加的不堪,这其实也是作家的一种自省和对广大女性的呼唤。波伏娃曾经说过:“只要社会上未能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只要风俗允许女人作为妻子和情人利用某些男人掌握的特权,她就还会梦想到一种被动的成功阻碍她自身的完善。”[6]而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风俗规定让女人成为男人的妻子或情人,也是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女性注定要依附男人而生活,但是这并不代表女人的能力不如男人,而是这个社会在各个层面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各方面的“设限”决定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
严英秀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不仅细腻地呈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现实境遇,同时笔触也深入到男权文化的肌理,对男性的精神面孔予以了深刻的挖掘。正如在《1999:无穷思爱》中,“我”的丈夫对“我”和栗的评价:“我的丈夫说真是幼稚可笑啊,你们这些人。他这样说时,脸上带着居高临下而又不无同情的神情。思想者特有的复杂面孔。他喜欢自己在我面前有这样的面孔。他是个虚荣心泛滥的男人。可笑啊,你们这些人。”[3]253“我”的丈夫没有批判始乱终弃的男人,反而说两个女人可笑,在自己的女人面前以一个俯视者的态度看待女性种种被他看作是“可笑”的行为,这不仅是他泛滥的虚荣心作祟,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深入骨髓的男权思想。
严英秀作为女性作家,她站在女性的视角审视了男性的自私与狂妄,于是,她的小说中隐含了对男性的批判。她指出在当代社会进程中男性性属文化品格和男性意志力量的普遍衰减,同时也揭示了当代社会中男性精神世界的平庸和空洞。
(二)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严英秀在女性问题的关注上是持续的,也是在这个问题的认知上不断掘进的。如果说早期的创作由于受女性主义的影响,体现了比较单一的女性视角,表达了对男性的批判的话,伴随着她思想的不断成熟,她完成了单一的女性视角到两性视角的转变,她就不单纯只是对男性的批判,还有对男性的期许和关怀,对美好两性关系的向往。她曾说:“我深信将女性写作的目光投注到男性关怀这一层面,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更新的女性观念的表现,是文化多元的标志。和解不是妥协,关怀不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再去重复古老的历史,而是更高意义更深层面上的达成共识,平衡互补,共荣共存。”[7]在严英秀的作品中,更多表现为一种女性和男性的和解与平衡状态,不管是《玉碎》中的卖鱼女郑洁和下岗工人王志强,还是《沦为朋友》中梅沁和于怀杨,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平和的姿态,男人再没有那种“主人”的姿态,甚至在《玉碎》中作者表现出了一种女性对男性的“拯救”情怀。小说中这样说:“她流着泪一遍遍回想起奶奶说过的话: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什么时候都只能靠自己。是的,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她从来不是弱人。只是因为体制的稳定和王志强的呵护,她才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不思进取地滋润着。现在,既然不能躲在谁的背后享清闲了,那么她只能站起来,走出去。” 他们夫妻双双下岗,王志强一蹶不振,整天愁眉苦脸,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努力的方向。相反作为女人的郑洁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起早贪黑的进货卖鱼,还要照顾丈夫与儿子。她身上的这种母性的光辉终于感染力王志强,王志强从一蹶不振中走了出来,两人一起开始承担生活的重担,虽然辛苦,但也幸福。文中表达的这种女性的自立自强,这种对脱离男性依附,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独立女性的歌颂,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肯定。而后来王志强在郑洁的感召下重新振作起来,夫妻两人重新在并不富裕甚至充满困难的生活里“相敬如宾”的这种生活状态也恰好体现了作者所认为的“男女和解”的理想状态。
正如安少龙所说:
“在当代众多的女性小说家中,甘肃藏族作家严英秀无疑是属于有着独特的个性标记的那一类。在她相继出版的《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中,我们看到近年来她在女性成长叙事主题上的某种渐变与掘进,那就是从单一的女性视角逐渐转向双性视角,从单一的性别对立、冲突的视角逐渐转向性别对话、融合的视角。这一内在变化,使她的小说在性别主题上更显示出一种浑厚的文化包容力,构成一个自足的叙事世界,更使她的小说文本带有某种文化建构性。”[8]
严英秀自己也说:“没有人可以否认,男女和平共处、和谐共处的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最终理想 。”[7]92由此可见,严英秀既认识到了在当今社会中女性依旧的弱势地位,从而对男权社会予以一定的批判,但同时,严英秀又看到了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剑拔弩张”式的铿锵昂扬的弊病,因而她的创作中没有女性主义者那样的愤慨嫉世,没有“张爱玲式”的对男性的“赶尽杀绝”,也没有“费尔斯通式”将男人直接推到女性对立面,她只是温和地,细腻地将女性的艰难处境以冷静的笔触剖析开来,她的作品中更多彰显的是两性机会的均等,以及两性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道德上的相似性。
叶淑媛在《爱与美的探寻:论严英秀小说的现代女性书写》一文中也这样写道:“严英秀的小说有真正的女人味,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和立场。但她的女性主义是温和的,是对女性气质和独特的女性经验的表达,她对男性的失望是对男人本身的失望,而不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表达对男权社会的愤慨,或者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和鞭挞。严英秀的小说不以如椽之笔塑造女性的史诗,也不会以愤激之语塑造对男权具有杀伤力的女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往往对男性充满了失望,同时又充满了向往。所以,严英秀的小说是女性生存和生命的真实境遇,是女性那纯情唯美的浪漫之花盛开和衰落的声音。”[9]
严英秀同时看到了两性的不完美,也就是说,要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的和谐共处,两性都是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成长的,只有个体真正完成了“人”的解放,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男女的和谐共处,平衡互补,美好的两性关系才能实现。
三、严英秀的文化之根
表面来看,严英秀虽为藏族作家,几乎很少触及藏族文化,而且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市文学或者校园题材的文学,作家自己也曾在访谈中谈到她在这个圈子里的尴尬地位:一个藏族作家,却几乎没怎么触及藏族文化。细读严英秀的小说,无论是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还是对女性主题的书写,尤其是她对于男女美好关系的认识归根结底其实都来源于藏文化这个母文化给予她的“慈悲善良、纯净美好”之心。
作为藏族作家,她从小在舟曲长大,但是她却几乎回避了故乡的题材,在她的所有作品中,真正意义上写藏族本土文化的小说也就《雨一直下》和《雪候鸟》这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中对汉藏通婚、藏族山寨的封闭以及对生死轮回的信仰都作了相关介绍,在作为干部子弟的旺姆龙珠和作为牧民儿女的索南次任的分手中将两人的理想差距与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深刻感人,甚至承认了“门当户对”这种世俗观念一定的合理性。
作为评论界,首先看到的严英秀的文化身份:藏族作家,藏族女作家。而她在创作的题材选择上却很少标识出自己的民族身份,细细想来,这恰恰是严英秀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借用昆德拉常常讨论的一个词“媚俗”来说,严英秀恰恰是不媚俗的,她没有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她也没有刻意只是用外在描写的异域风情来强化自己的民族身份来迎合,而是写着自己熟悉的题材,自己感同身受的女性主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会因为自己天然的民族身份,不会因为一种外在的期待视野,而去写这种只有外在的文化符号而缺乏内在的文化生命的所谓藏族题材。”而这恰恰是她的母文化给予她的一种美好品质。“母族文化给予我的慈悲善良、纯净美好,就是用手中之笔表达心中的爱和信仰,追求一种有清洁精神的美好人生。”
一个人在母族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中一点点成长,这样的浸染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成就他的个性特质,这种影响或许是无形的,但却是巨大的。总之,我认为藏族文化中的许多共性,与我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追求非常契合。这种东西,用不着外在符号去标示,它在日常的生活中,是自觉的行为规范,在写作中,是天然的血脉渗透,是一种底色,这跟写什么故事什么题材无关。藏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着我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的精神和追求,那就是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和疼惜,对道德良善永远的信仰和追寻。爱美、信美、求美,是我作品中不变的主题。这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致力要完成的抵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个体能为人类文化的建构所做的也就这点了。[1]3
在笔者看来,评论界看到的严英秀创作中极致化的叙事倾向,纯粹干净的语言表现,宽容的态度,理想主义的表达等等,这些恰恰体现了藏文化赋予严英秀的内在本质。藏文化中的纯净、对美和善的追求,对信仰的坚守这些既是严英秀的特质,也是她的文学的底色。她自己也如此说道:“其实我在《走出巴颜喀拉》这篇散文中也曾说‘没有什么关于我的种种,比我是个藏人更抵达我的本质、我的内里。’我认为不管我写什么,从民族文化内涵的角度探析,我的文学都是藏族文学的血脉分支,是藏族文学的有机构成。”[1]7可以说藏文化的特质融入了严英秀的血脉,以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反过来也决定了她的文学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英秀的文学之根依然是自己的母文化。“严英秀的小说不依靠地域和民族题材来支撑和取胜,而是将藏族洁净文化的精神血统赋予她的对爱与美的探寻,融入世间生活常态,从普通的现象和日常中发现爱与美,将它抽绎、凝练、提升并加以艺术升华和审美转化,在当代平常生活中感悟不平常,这是一种创作的功力,也是对于地域和民族的超越。”[9]112
正如她所说自己“想要从这样的生活中提炼出意义,追问出价值,想要找寻出之所以一步步走下去的坚实理由”。[1]3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仰,一种属于严英秀的文学信仰!
【参考文献】
[1]胡沛萍.面对无穷的可能,和缺陷——作家严英秀访谈录[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
[2]严英秀.严英秀的小说[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313.
[3]严英秀.纸飞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73.
[4]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M].张经浩,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8.
[5]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9: 182.
[6]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31.
[7]严英秀.论女性主义文学的男性关怀[J].当代文坛,2007(4):92-93.
[8]安少龙.严英秀作品:用爱撑起两性共同的天空[N].文艺报,2019-11-04.
[9]叶淑媛.爱与美的探寻:论严英秀小说的现代女性书写[J].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4):113.
原刊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马粉英,女,甘肃天水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理事,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出版著作三部,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末民初外国探险家游记中的西域形象建构研究”,完成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教育厅项目、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等各级各类项目10余项。作为课程负责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获评甘肃省高等学校省级线上一流课程,获得西北师范大学孔宪武中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西北师范大学优秀教师、西北师范大学“优秀班主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我最喜爱的老师”,“三创赛”优秀指导教师等多项奖励与荣誉。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舟曲人,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居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走出巴颜喀拉》和文学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