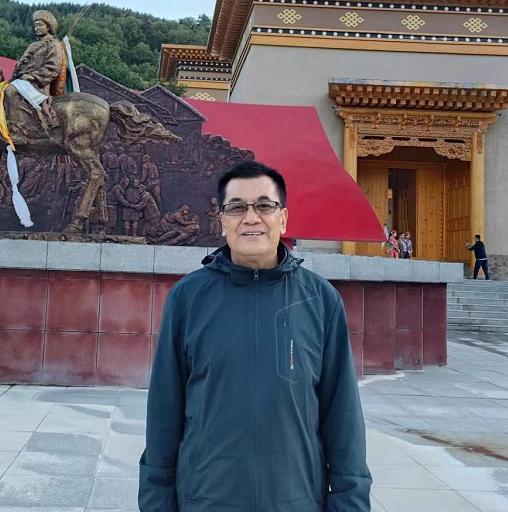гҖҖгҖҖеӢӨеҠіжҷәж…§зҡ„и—Ҹж—Ҹдәәж°‘еңЁеҺҶеҸІеҸ‘еұ•зҡ„й•ҝжІідёӯеҲӣйҖ дәҶзҒҝзғӮзҡ„ж–ҮеҢ–пјҢе…¶и—Ҹж–Үе…ёзұҚжө©еҰӮзғҹжө·пјҢд»…ж¬ЎдәҺжұүж—ҸиҖҢдҪҚеұ…е°‘ж•°ж°‘ж—Ҹд№ӢеҶ пјҢе…ёзұҚиЈ…её§зү№зӮ№жӣҙе…·жңүйІңжҳҺзҡ„ж°‘ж—Ҹзү№иүІпјҢд»Һе…ёзұҚзҡ„иүІеҪ©е‘ҪеҗҚеҲ°дҝ®йҘ°е–»зҡ„иҝҗз”ЁпјҢд»ҺжңЁеҲ»йӣ•зүҲеҚ°еҲ·еҲ°жўөеӨ№иЈ…зҡ„д№ҰзұҚеҪўејҸжҳҺжҳҫеёҰжңүдҪӣж•ҷж–ҮеҢ–зҡ„зғҷеҚ°гҖӮжң¬ж–Үж №жҚ®зҺ°жңүиө„ж–ҷеҜ№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Ү дёӘзү№зӮ№дҪңеҲқжӯҘжҺўи®ЁгҖӮ
гҖҖгҖҖ дёҖ
гҖҖгҖҖд№ҰзұҚзҡ„зү©иҙЁжқҗж–ҷе’Ңе·Ҙиүәжҙ»еҠЁжһ„жҲҗдәҶд№ҰзұҚзҡ„иЈ…её§пјҢдёӯеӣҪд№ҰзұҚзҡ„иЈ…её§еҺҶеҸІжәҗиҝңжөҒй•ҝпјҢе®ғйҡҸзқҖд№ҰзұҚзҡ„еҮәзҺ°йҖҗжёҗдә§з”ҹгҖӮжңҖеҲқзҡ„з®Җзӯ–гҖҒеёӣеҚ·е’ҢеҶҷжң¬зҡ„иЈ…её§е®һз”ЁжҖ§еҠҹиғҪзӘҒеҮәдёҖдәӣпјҢдёәдәҶдҫҝдәҺйҳ…иҜ»жүҚдҪҝеҫ—йЎөж¬ЎжңүеәҸеҢ–пјҢеҗҺжқҘйҡҸзқҖйӣ•зүҲеҚ°еҲ·зҡ„еҸ‘жҳҺе’Ңд№ҰзұҚиЈ…её§жҠҖжңҜзҡ„еҸ‘еұ•гҖҒиҝӣжӯҘпјҢиЈ…её§дҪңдёәдёҖз§ҚиүәжңҜеҲӣйҖ пјҢи¶ҠжқҘи¶ҠжҲҗдёәдҪ“зҺ°д№ҰзұҚзҡ„еӨ–еңЁеҪўиұЎе’ҢйҖҡиҝҮе®ғжқҘиЎЁзҺ°д№ҰзұҚжҖқжғіеҶ…е®№зҡ„еҪўејҸпјҢеҗ„ж°‘ж—ҸеңЁд№ҰзұҚиЈ…её§дёӯзҡ„иүәжңҜеҲӣйҖ пјҢжҲҗдёәзҒҝзғӮж°‘ж—Ҹж–ҮеҢ–дёӯзҡ„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и—Ҹж–Үе…ёзұҚдёӯзҡ„иЈ…её§жүҖиЎЁзҺ°зҡ„йЈҺж је°ұеҫҲжңүзү№иүІгҖӮи—Ҹж–Үе…ёзұҚзҡ„зүҲжң¬еҪўејҸеҫҲзү№еҲ«пјҢе‘Ҳй•ҝжқЎеҪўпјҢжҙ»йЎөзҠ¶еҚ°еҲ·пјҢжўөеӨ№жң¬зҡ„иЈ…её§пјҢиҝҷз§ҚеҪўејҸжҳҜи—Ҹж–Үе…ёзұҚжңҖдё»иҰҒзҡ„зү№еҫҒгҖӮйҡӢжңқжқңе®қгҖҠеӨ§дёҡжқӮи®°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ж–°зҝ»з»Ҹжң¬д»ҺеӨ–еӣҪжқҘпјҢз”ЁиҙқеӨҡж ‘еҸ¶гҖӮеҸ¶еҪўдјјжһҮжқ·пјҢеҸ¶йқўеҺҡеӨ§пјҢжЁӘдҪңиЎҢд№ҰгҖӮзәҰз»ҸеӨҡе°‘пјҢзјҖе…¶дёҖиҫ№пјҢзү’зү’然呼дёәжўөеӨ№гҖӮвҖқжўөеӨ№жң¬зҡ„д№ҰзұҚиЈ…её§жҳҜеҸ—еҚ°еәҰиҙқеҸ¶з»Ҹзҡ„еҪұе“ҚжүҖеҪўжҲҗзҡ„гҖӮиҙқеҸ¶жҳҜиҙқеӨҡзҪ—ж ‘еҸ¶пјҢз”ұдәҺе…·жңүиҖҗзЈЁжҖ§пјҢдәә们е°ұе°Ҷз»Ҹж–ҮеҲ»еҶҷеңЁиҙқеҸ¶дёҠпјҢйҖҡиҝҮжү“еӯ”з©ҝзәҝиЈ…жҲҗвҖңеҶҢйЎөвҖқпјҢдёҚи®әжҗәеёҰгҖҒйҳ…иҜ»еқҮеҫҲж–№дҫҝпјҢиҮід»ҠеңЁж јйІҒжҙҫеҜәйҷўз”ҳиӮғзҡ„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дҝқеӯҳзқҖе Әз§°еҜәе®қзҡ„йҳҝеә•еіЎзҡ„гҖҠиҸ©жҸҗйҒ“зҒҜи®әгҖӢе’ҢжңҲз§°зҡ„жўөж–ҮиҙқеҸ¶и‘—дҪңдёӨйғЁгҖӮз”ұдәҺеҸ—иҙқеҸ¶з»Ҹзҡ„еҪұе“Қе’ҢеҗҜеҸ‘пјҢи—Ҹж–Үе…ёзұҚеҲӣйҖ жҖ§ең°жҠҠиҙқеҸ¶з»ҸеҪўејҸиҝҗз”ЁеҲ°д№ҰзұҚзҡ„иЈ…её§еҚ°еҲ·дёӯ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еҲ«е…·дёҖж јзҡ„й•ҝжқЎеҪўи—Ҹж–Үе…ёзұҚеҪўејҸгҖӮ
гҖҖгҖҖи—Ҹж–Үе…ёзұҚзҡ„й•ҝжқЎеҪўејҖжң¬жңүеҮ з§ҚдёҚеҗҢзҡ„и§„ж јпјҢжңүй•ҝзәҰ 60-70 еҺҳзұізҡ„вҖңз®ӯжқҶжң¬вҖқпјҢдёҺдёҖиҲ¬зҡ„з®ӯжқҶй•ҝеәҰзәҰдёәзӣёзӯүпјӣжңүй•ҝзәҰ 40 еҺҳзұізҡ„вҖңдёҖиӮҳжң¬вҖқпјҢдёҺжҲҗе№ҙдәәзҡ„иӮҳй•ҝзәҰзӣёзӯүпјҢ并еӣ жӯӨиҖҢеҫ—еҗҚпјӣиҝҳжңүзәҰ 25 еҺҳзұій•ҝзҡ„вҖңзҹӯе°Ҹжң¬вҖқпјҢеҪ“然иҝҳжңүе…¶д»–е°әеҜёзҡ„зүҲжң¬еҪўејҸгҖӮиҝҷз§Қй•ҝжқЎеҪўзүҲжң¬зҡ„еҚ°еҲ·жҳҜжңЁеҲ»йӣ•зүҲеҚ°еҲ·еҪўејҸгҖӮеңЁи—ҸеҢәпјҢеҫ·ж јеҚ°з»ҸйҷўгҖҒйӮЈеЎҳеҚ°з»ҸйҷўгҖҒжӢүиҗЁеёғиҫҫжӢүе®«еҚ°з»ҸйҷўгҖҒеЎ”е°”еҜәеҚ°з»ҸйҷўгҖҒеҚ“е°јеҚ°з»ҸйҷўгҖҒ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еҚ°з»ҸйҷўзӯүйғҪжҳҜи‘—еҗҚзҡ„еҮәзүҲеҚ°еҲ·з»„з»Үе’Ңжңәжһ„пјҢжңЁеҲ»йӣ•зүҲеҚ°еҲ·жҳҜдё»иҰҒзҡ„еҚ°еҲ·еҪўејҸпјҢд»Ҙеҫ·ж јеҚ°з»Ҹйҷўе°Өдёәи‘—еҗҚпјҢеҚ°зүҲиҙЁйҮҸй«ҳпјҢеҚ°еҲ·е·Ҙиүә讲究жҳҜеҫҲжңүд»ЈиЎЁжҖ§зҡ„гҖӮиҝҷйҮҢзҡ„д№ҰзүҲеҮәиҮӘзІҫйҖүзҡ„иҙЁең°еқҡзЎ¬зҡ„жЎҰжңЁпјҢз»ҸиҝҮзҶҸгҖҒз…®гҖҒжіЎгҖҒжҷ’зӯүдёҖзі»еҲ—еӨҡйҒ“е·ҘеәҸзҡ„дёҘж јеӨ„зҗҶпјҢжңҖеҗҺе®ҢжҲҗзҡ„з»ҸжқҝдёӨйқўйӣ•еҲ»пјҢеҲҖеҠҹж·ұжІүзЁіеҒҘпјҢж–Үеӯ—жё…жҷ°жҳҺжң—гҖӮ
гҖҖгҖҖжўөеӨ№жң¬е‘Ҳй•ҝжқЎеҪўпјҢжҙ»йЎөзҠ¶пјҢжҜҸйЎөж–Үеӯ—д»Һе·ҰеҲ°еҸіжЁӘеҶҷпјҢжЁӘиЎҢеӯ—ж•°еӨҡпјҢз«–и·қжҜ”иҫғеӨ§пјҢжЁӘеҗ‘зҝ»еҗҜпјҢжңҖеҲқзҡ„иЈ…и®ўеҪўејҸзұ»еҗҢиҙқеҸ¶з»ҸпјҢжҠҠд№ҰйЎөжҢүйЎәеәҸжҺ’еҲ—жү“еӯ”з©ҝиҝһзҡ„еҠһжі•пјҢиЈ…и®ўжҲҗвҖңеҶҢвҖқгҖӮжўөеӨ№жң¬еҲҶдёәдёӨз§ҚеҪўејҸпјҢдёҖз§ҚжҳҜжңүеӨ№жқҝпјҢзӣёеҪ“дәҺд№ҰеҮҪжҖ§иҙЁпјҢеҸҰдёҖз§ҚжҳҜж— еӨ№жқҝгҖӮжўөеӨ№жң¬иҝҷз§Қд№ҰзұҚеҪўејҸзҡ„иЈ…её§йҷӨдәҶеҸ—иҙқеҸ¶з»ҸеҪўејҸеңЁи—ҸеҢәзҡ„жөҒдј еҪұе“ҚеӨ–пјҢд№ҹдёҺи—Ҹж–Үзҡ„еҚ°еҲ·дёҺйҳ…иҜ»д№ жғҜжңүе…ігҖӮи—ҸеҢәеғ§дҝ—д№ жғҜдәҺеёӯең°зӣҳи…ҝиҖҢеқҗпјҢиҝҷз§Қеқҗе§ҝдҫҝдәҺй•ҝжқЎеҪўзҡ„з»Ҹж–ҮжЁӘж”ҫдәҺдёӨи…ҝд№ӢдёҠпјҢйҳ…иҜ»иө·жқҘеҚҒеҲҶж–№дҫҝгҖӮ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Қ°еҲ·жқҝжқҗжүҖз”ЁжңЁжқҗжң¬иә«жҳҜй•ҝжқЎеҪўпјҢеҲ¶дҪңй•ҝжқЎеҪўзҡ„йӣ•зүҲжӣҙжҳҜйЎәеҠҝиҖҢдёә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ҸҜд»ҘиҜҙпјҢи—Ҹж–Үе…ёзұҚй•ҝжқЎеҪўзҡ„иЈ…её§еҪўејҸжҳҜеҗёж”¶е’ҢжҺЁе№ҝдәҶеҚ°еәҰжўөж–ҮдҪӣз»Ҹ并结еҗҲи—ҸеҢәзҡ„е®һйҷ…жүҖеҪўжҲҗзҡ„е…·жңүең°еҹҹзү№иүІзҡ„иЈ…её§еҪўејҸпјҢдҫҝдәҺзҝ»йҳ…иҜөиҜ»гҖӮ
гҖҖгҖҖеҲӣж–°жҳҜдёҖдёӘж°‘ж—ҸиҝӣжӯҘзҡ„зҒөйӯӮгҖӮи—Ҹж°‘ж—ҸжҳҜдёҖдёӘе–„дәҺеҗёж”¶еӨ–жқҘж–ҮеҢ–пјҢ继жүҝдјҳз§Җдј з»ҹж–ҮеҢ–并еңЁз»§жүҝдёӯз§ҜжһҒеҲӣж–°зҡ„ж°‘ж—ҸгҖӮ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Қ°еҲ·еҚҒеҲҶ讲究еңЁз»Ҹд№ҰдёӯжҸ’е…ҘзІҫзҫҺзҡ„дҪӣж•ҷеӣҫеғҸгҖӮе…ёзұҚзҡ„еҶ…е®№еҚҒеҲҶеәһжқӮпјҢеӨ§еӨҡд»ҘдҪӣж•ҷз»ҸгҖҒеҫӢгҖҒи®әдёәдё»иҰҒеҶ…е®№гҖӮи—Ҹж—Ҹзҡ„з»Ҹд№ҰеҚ°еҲ·жңүдёҖдёӘд№ жғҜпјҢе°ұжҳҜеңЁжүҖеҚ°зҡ„з»Ҹд№ҰйҮҢиҰҒеҚ°дёҠдёҖдәӣзҘһзҒөжҲ–дҪӣеЎ”зҡ„еҲ»зүҲеӣҫеғҸпјҢеҮ д№ҺжҜҸеҶҢд№Ұзҡ„ејҖеӨҙе’Ңз»“е°ҫйғҪеҚ°жңүдёҖе№…гҖҒдёӨе№…гҖҒз”ҡиҮідёүе№…дҪӣеғҸгҖӮеҸҰеӨ–дёҖдәӣиЈ…её§зІҫзҫҺзҡ„з»Ҹд№ҰеңЁз»Ҹж–ҮејҖе§Ӣе’Ңз»“жқҹзҡ„еҮ йЎөеҚ°дёҠдҪӣеғҸгҖӮеңЁж•Ұз…ҢеҸ‘зҺ°зҡ„д№ҰзұҚжңүдёҠеӣҫдёӢж–ҮејҸзҡ„жҸ’еӣҫпјҢеғҸдә”д»ЈеҲ»еҚ°зҡ„гҖҠжҷ®иҙӨиҸ©иҗЁеғҸгҖӢгҖҒгҖҠж–Үж®Ҡи§ӮйҹіеғҸгҖӢпјҢиҝҳжңүгҖҠе®қ箧еҚ°йҷҖзҪ—е°јз»ҸгҖӢзӯүйғҪеңЁеҚ·йҰ–и®ҫи®Ўжңүжүүз”»пјҢжҳҫеҫ—зІҫзҫҺиҖҢеҜҢжңүж–°йў–жҖ§пјҢз»ҷдәәдёҖз§ҚиөҸеҝғжӮҰзӣ®д№Ӣж„ҹгҖӮз»Ҹе…ёи‘—дҪңжӣҙ讲究еӣҫж–Ү并иҢӮзҡ„еҪўејҸпјҢжҸ’еӣҫжҳҜж–Үеӯ—еҶ…е®№зҡ„еҶҚзҺ°еҪўејҸпјҢе®ғдҪңдёәеҚ°еҲ·е“Ғзҡ„жңүжңәз»„жҲҗйғЁеҲҶпјҢеҸҜд»ҘеҪўиұЎең°ејҘиЎҘиҜӯиЁҖж–Үеӯ—дёӯйҡҫд»ҘиЎЁиҝ°зҡ„дёңиҘҝгҖӮд»ҺиүәжңҜзҡ„и§’еәҰзңӢпјҢжҸ’еӣҫдҪңдёәдёҖз§ҚиүәжңҜеҪўејҸпјҢдёҚиғҪд»…зңӢеҲ°е®ғеңЁеҚ°еҲ·е“Ғдёӯзҡ„зӮ№зјҖдҪңз”Ёе’ҢиЈ…её§ж•ҲжһңпјҢзј–иҫ‘и®ҫи®Ўдёӯд№ҹе…·жңүйҮҚиҰҒзҡ„и°ғиҠӮе’ҢзҫҺеҢ–зүҲејҸзҡ„дҪңз”ЁгҖӮи—Ҹж–Үе…ёзұҚзҡ„жҸ’еӣҫпјҢиғҪеӨҹеҪўиұЎең°иЎЁиҫҫе’Ңеӣһеә”дҪңиҖ…дёҺиҜ»иҖ…дҝЎд»°дҪӣж•ҷзҡ„еҶ…еҝғдё–з•ҢпјҢдҪҝиҜ»иҖ…дёҖзӣ®дәҶ然пјҢиҜӯиЁҖзҡ„еҶ…ж¶өе’ҢиүәжңҜзҡ„иЎЁиҫҫеңЁиҝҷйҮҢз»“еҗҲеҫ—еҚҒеҲҶе®ҢзҫҺпјҢд»ҺеҸҰдёҖдёӘдҫ§йқўеҸҚжҳ дәҶеҪ“ж—¶еҪ“ең°зҡ„йЈҺеңҹдәәжғ…пјҢе…·жңүжһҒејәзҡ„иүәжңҜе’ҢеҺҶеҸІд»·еҖјгҖӮд№ҹд»ҺеҸҰдёҖдёӘдҫ§йқўеҸҚжҳ и—ҸеҢәзҡ„еҚ°еҲ·жҠҖжңҜж— и®әжҳҜйЈҺж јиҝҳжҳҜеҸ‘еұ•ж°ҙе№ійғҪиҫҫеҲ°дәҶдёҖе®ҡзҡ„й«ҳеәҰпјҢдҪӣж•ҷеҜ№жҺЁеҠЁйӣ•зүҲеҚ°еҲ·жҠҖжңҜиө·дәҶдёҖе®ҡзҡ„з§ҜжһҒдҪңз”ЁгҖӮ
гҖҖгҖҖз»ҸеҚ·зҡ„еӨ№жқҝйҖүжқҗз”ЁиҙөйҮҚзҡ„зҙ«жӘҖжңЁе’Ңж ёжЎғжңЁеҲ¶дҪңпјҢеҒҡе·ҘзІҫе·§гҖҒиЈ…йҘ°еҚҒеҲҶиҖғ究пјҢе°ҒйқўеӨҡдёәеҪ©иүІжјҶжҸҸйҮ‘пјҢ并еңЁеӨ№жқҝдёҠйӣ•еҲ»жңүзІҫзҫҺзҡ„еҪ©иүІеӣҫжЎҲпјҢдҪӣж•ҷзҡ„еҗүзҘҘе…«е®қпјҲжі•иҪ®гҖҒжі•е№ўгҖҒеҸҢйұјгҖҒе®қ瓶гҖҒжі•иһәгҖҒиҺІиҠұгҖҒе®қдјһгҖҒеҗүзҘҘз»“пјүеҫҖеҫҖдёәйҰ–йҖүеӣҫжЎҲпјҢиҝҳжңүдҪӣеғҸгҖҒзҒ«з„°гҖҒе®қзҸ зӯүд№ҹеёёеёёиў«еә”з”ЁгҖӮе…¶ж¬ЎпјҢеңЁдҪӣж•ҷиүәжңҜдёӯиҺІиҠұиў«и§ҶдёәзәҜжҙҒгҖҒй«ҳе°ҡзҡ„иұЎеҫҒпјҢ并еҗ«жңүеҗүзҘҘгҖҒзҘһеңЈзҡ„еҜ“ж„ҸиҖҢеңЁеӨ№жқҝе°ҒйқўиЈ…её§дёӯе№ҝжіӣиҝҗз”ЁгҖӮ
гҖҖгҖҖи—Ҹж–Үе…ёзұҚиЈ…йҘ°дёӯзҡ„иүІеҪ©иҝҗз”ЁжҳҜеёёи§Ғзҡ„гҖӮи—Ҹж–ҮгҖҠеӨ§и—Ҹз»ҸгҖӢжҳҜдҪӣж•ҷе…ёзұҚжұҮзј–иҖҢжҲҗзҡ„дёҖйғЁеӨ§еһӢдёӣд№ҰпјҢз”ұгҖҠз”ҳзҸ е°”гҖӢе’ҢгҖҠдё№зҸ е°”гҖӢдёӨйғЁеҲҶз»„жҲҗгҖӮеҸҜз§°дёәи—Ҹж—Ҹж–ҮеҢ–зҡ„зҷҫ科全д№ҰпјҢеҶ…е®№е№ҝеҚҡпјҢж¶үеҸҠе®—ж•ҷгҖҒе“ІеӯҰгҖҒеҺҶеҸІгҖҒиҜӯиЁҖгҖҒж–ҮеӯҰгҖҒиүәжңҜгҖҒеӨ©ж–ҮгҖҒеҺҶз®—гҖҒеҢ»иҚҜгҖҒе»әзӯ‘зӯүеҗ„дёӘж–№йқўгҖӮе…¶иЈ…её§йқһеёёиҖғ究пјҢзІҫиЈ…гҖҠеӨ§и—Ҹз»ҸгҖӢ镶жңүзҸҚзҸ гҖҒе®қзҹігҖҒжқҫзҹігҖҒиұЎзүҷзӯүпјҢжҳҫеҫ—еҚҒеҲҶеҚҺиҙөгҖӮдёҖиҲ¬зІҫиЈ…гҖҠеӨ§и—Ҹз»ҸгҖӢиҰҒз”Ёй»„иүІз»ёзјҺеҢ…иЈ№пјҢдёҠдёӢз»ҸжқҝйҖүжқҗжңүзҙ«жӘҖжңЁгҖҒж ёжЎғжңЁпјҢ并йӣ•еҲ»жңүиЈ…йҘ°еӣҫжЎҲпјҢеӨ–ж¶ӮйҮ‘жјҶпјҢжҳҫеҫ—еҜҢдёҪе ӮзҡҮгҖӮ 1989 е№ҙжҠ„еҶҷзҡ„е…«е®қгҖҠдё№зҸ е°”гҖӢпјҢз”Ёй»„йҮ‘гҖҒжқҫиҖізҹігҖҒзҷҪ银гҖҒзҸҠз‘ҡгҖҒй”ЎгҖҒзәўй“ңгҖҒзҷҪиһәдёҺзҸҚзҸ зҡ„ж··еҗҲзү©дёәвҖңеўЁжұҒвҖқжүҖеҶҷжҲҗзҡ„з»ҸйЎөе‘ҲдёғиүІе…үеҪ©пјҢиүІеҪ©иЎЁзҺ°еҫҲдё°еҜҢпјҢжүҖеҶҷз»Ҹж–Үзҡ„зәёжҳҜз”ұеҶ…ең°зҡ„зІҫеҲ¶зЎ¬зәёе’Ңи—ҸзәёйҖҡиҝҮеӨҚжқӮзҡ„е·ҘиүәеӨ„зҗҶеҒҡжҲҗзҡ„пјҢе…·жңүжҠ—и…җгҖҒжҠ—иӣҖгҖҒжҠ—ж·ӢгҖҒиҖҗз”Ёзӯүзү№зӮ№гҖӮ
гҖҖгҖҖеҫ·ж јеҚ°з»Ҹйҷўд»Ҙд№ҰзүҲеҚ°еҲ·еҜҢжңүзү№иүІиҖҢи‘—з§°пјҢд№ҰзүҲжңүзәўзүҲе’Ңй»‘зүҲд№ӢеҲҶгҖӮзҸҚиҙөзҡ„дҪӣж•ҷе…ёзұҚз”Ёжңұз Ӯзҡ„зәўзүҲеҚ°еҲ·гҖӮжңұз Ӯдёӯеҗ«жңүзҹҝзү©иҙЁпјҢжңүз»Ҹд№…иҖҗзЈЁе’ҢдёҚжҳ“иӨӘиүІгҖҒеҸҳиүІзҡ„зү№зӮ№гҖӮ 1410 е№ҙпјҲжҳҺж°ёд№җе…«е№ҙпјүпјҢжҳҺжҲҗзҘ–дёәд»–еҺ»дё–зҡ„е® еҰғеҫҗж°ҸиҝҪиҚҗеҶҘзҰҸпјҢжҙҫдәәе…Ҙи—ҸжұӮеҫ—и”Ўе·ҙз”ҳзҸ е°”зүҲжң¬дёәж ҮеҮҶпјҢеҸҲиҜ·з¬¬дә”дё–еҷ¶зҺӣе·ҙжҙ»дҪӣеҫ—银еҚҸе·ҙиөҙеҚ—дә¬зҒөи°·еҜәд»»з”ҳзҸ е°”еҲҠеҚ°жҖ»зәӮпјҢйҰ–ж¬ЎеҲ»зүҲеҚ°еҲ·дәҶи—Ҹж–ҮеӨ§и—Ҹз»ҸгҖҠз”ҳзҸ е°”гҖӢпјҢдәә们称иҝҷеҘ—гҖҠз”ҳзҸ е°”гҖӢзүҲдёәж°ёд№җзүҲгҖӮж°ёд№җзүҲз”ҳзҸ е°”зҡ„еҲҠеҚ°пјҢејҖдәҶи—Ҹж–ҮжңЁеҲ»д№Ӣе…ҲжІіпјҢеҜ№еҗҺжқҘи—Ҹж–Үйӣ•зүҲеҚ°еҲ·жңүзқҖж·ұиҝңзҡ„еҪұе“ҚгҖӮж°ёд№җзүҲжҳҜз”Ёжңұз ӮжұҒеҚ°еҲ·зҡ„гҖӮдёҖиҲ¬зҡ„и‘—дҪңз”Ёзү№еҲ¶зҡ„еўЁдёәйўңж–ҷеҚ°еҲ·пјҢеўЁзҡ„еҲ¶дҪңеҺҹж–ҷйҰ–жҺЁдёәй…ҘжІ№зҒҜзҡ„зҒҜиҠұпјҢиҝҳжңүеғҸжІ№жқҫпјҲжҙӣжүҺгҖҒиҙЎеёғең°жүҖдә§пјүзҮғзғ§ж—¶зҡ„зғҹзө®пјҢеҶҚеҠ дёҠзүӣиғ¶е’Ңе…¶д»–жҲҗеҲҶзҡ„жқҗж–ҷз ”еҲ¶иҖҢжҲҗпјҢз”ЁжүӢе·Ҙж“ҚдҪңе®ҢжҲҗеҚ°еҲ·е·ҘдҪңгҖӮ
гҖҖгҖҖ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Қ°еҲ·дёҖиҲ¬з”Ёи—Ҹең°жүҖдә§зҡ„ вҖңи—ҸзәёвҖқпјҢи—ҸзәёжҳҜз”ұж ‘зҡ®зәӨз»ҙе’ҢдёҖз§Қз‘һйҰҷзӢјжҜ’ж №йғЁзәӨз»ҙдёәеҺҹж–ҷпјҢз»ҸзҹізҒ°е’ҢеңҹзўұеӨ„зҗҶеҗҺиҖҢжҲҗпјҢзәёиүІжҷҰжҡ—пјҢзәӨз»ҙжҖ§еҘҪпјҢдҪҶиҫғдёәзІ—зіҷпјҢеӣ е…¶иҚүиҙЁе…·жңүжҜ’жҖ§пјҢжүҖд»ҘиҜҘзәёе…·жңүдёҚиӣҖиҷ«пјҢиғҪеӨҹй•ҝжңҹдҝқеӯҳзҡ„зү№зӮ№гҖӮ
гҖҖгҖҖ дәҢ
гҖҖгҖҖиүІеҪ©жҳҜдәә们еҜ№е®ўи§Ӯдё–з•Ңзҡ„дёҖз§Қж„ҹзҹҘпјҢе®ғжҳҜжһ„жҲҗдё–з•Ңзҡ„еҹәжң¬иҰҒзҙ д№ӢдёҖгҖӮиүІеҪ©еңЁдәә们зҡ„зңјдёӯйҷӨе…·жңүиҮӘ然еұһжҖ§еӨ–пјҢжӣҙе…·жңүдё°еҜҢзҡ„зӨҫдјҡж–ҮеҢ–еҶ…ж¶өгҖӮ
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и®°еҪ•иүІеҪ©зҡ„з¬ҰеҸ·вҖ”вҖ”йўңиүІиҜҚеңЁдёҚеҗҢзҡ„ж–ҮеҢ–иғҢжҷҜгҖҒдёҚеҗҢзҡ„ж°‘ж—Ҹдёӯеҗ«жңүзҡ„иұЎеҫҒж„Ҹд№үжҳҜжңүе·®ејӮзҡ„пјҢеҙҮе°ҡиүІеҪ©зҡ„иЎЁзҺ°еҪўејҸеёёеёёе…·жңүи§ӮеҝөжҖ§зҡ„иЎЁзҺ°еӣ зҙ гҖӮи—Ҹж°‘ж—ҸжҳҜдёҖдёӘзғӯзҲұиүІеҪ©зҡ„ж°‘ж—ҸпјҢ他们з”ҹжҙ»еңЁжӢҘжңүи“қеӨ©гҖҒзҷҪдә‘гҖҒз»ҝиҚүе’ҢйІңиҠұзҡ„еӨҡеҪ©дё–з•ҢдёӯпјҢйҳіе…үгҖҒи“қеӨ©е’ҢзҷҪдә‘жҳҜиҘҝи—Ҹй«ҳеҺҹжңҖеҜҢжңүиҜ—ж„Ҹзҡ„дәӨе“Қе’Ңдә®дёҪзҡ„иүІеҪ©пјҢ他们еҜ№иүІеҪ©зҡ„ж„ҹзҹҘеҸҚжҳ еҮә他们зҡ„ж„ҹжғ…иүІеҪ©гҖӮи—Ҹж—Ҹиҝҗз”ЁиүІеҪ©е‘ҪеҗҚж–ҮзҢ®е…ёзұҚжҳҜдёҖз§ҚзӢ¬зү№зҡ„ж–ҮеҢ–зҺ°иұЎгҖӮз”ЁйўңиүІиҜҚе‘ҪеҗҚзҡ„и—Ҹж–Үе…ёзұҚжңү гҖҠзҷҪ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йқ’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зәў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ж–°зәў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й»„еҸІгҖӢпјҲеҸҲеҗҚгҖҠй»„зҗүз’ғгҖӢпјүгҖҒгҖҠзҷҪзҗүз’ғи®әзҢ®з–‘дәҢзҷҫйӣ¶е…«жқЎгҖӢпјҢиҝҳжңү第еҸёВ·жЎ‘жқ°еҳүжҺӘзҡ„гҖҠи“қзҗүз’ғгҖӢгҖӮи”Ўе·ҙВ·иҙЎеҷ¶еӨҡжқ°жүҖи‘—зҡ„гҖҠзәўеҸІгҖӢжҳҜиҘҝи—ҸеҺҶеҸІдёҠе…·жңүеӣәе®ҡдҪ“иЈҒзҡ„дёӘдәәж’°еҶҷзҡ„еҸІи‘—пјҢд»–ејҖеҲӣдәҶи—Ҹж—ҸеҸІеӯҰзҡ„ж–°йЈҺпјҢд»–иҝҳи‘—жңүи”Ўе·ҙз”ҳзҸ е°”зҡ„зӣ®еҪ• гҖҠзҷҪеҸІгҖӢе’ҢеҸҚжҳ зҺӢз»ҹеҺҶеҸІзҡ„ гҖҠиҠұеҸІгҖӢпјӣжЎӮиҜ‘еёҲе®ЈеҠӘиҙқжүҖи‘—зҡ„гҖҠйқ’еҸІгҖӢжҳҜеҸІеҶҢзұ»гҖҒж•ҷжі•зұ»и‘—дҪңдәҢиҖ…з»“еҗҲзҡ„д»ЈиЎЁдҪңд№ӢдёҖпјҢд»ЈиЎЁзқҖж–ҮзҢ®еҲӣдҪңзҡ„иҝӣжӯҘи¶ӢеҠҝгҖӮй»„иүІеңЁи—Ҹж—Ҹе®—ж•ҷжҖқжғідёӯиұЎеҫҒе…үжҳҺе’ҢдҪӣжі•ж— иҫ№зҡ„еҶ…ж¶өпјҢжҳҜжһҒдёәзҘһеңЈзҡ„иүІзӣёпјҢд№ҹжҳҜй«ҳеғ§еӨ§еҫ·е’Ңж”ҝж•ҷдёҠеұӮдәәеЈ«зҡ„дё“з”ЁиүІгҖӮ
гҖҖгҖҖиүІеҪ©зҡ„жң¬иҙЁжҳҜжҸҸиҝ°дәӢзү©зҡ„йўңиүІпјҢйўңиүІжҳҜдёҖз§Қи§Ҷи§үзҺ°иұЎпјҢдәә们йҖҡиҝҮеҜ№жүҖйҷ„зқҖзҡ„е…·дҪ“е®һзү©зҡ„йўңиүІжқҘиҺ·еҫ—еҜ№иүІеҪ©зҡ„ж„ҹзҹҘпјҢжӯЈеӣ дёәиүІеҪ©жүҖе…·жңүзҡ„иҝҷз§Қзү№жҖ§пјҢдҪҝеҫ—дәә们иҝҗз”ЁйўңиүІжқҘжҸҸиҝ°иҮӘ然зҺ°иұЎгҖӮи—Ҹж—ҸеҜ№зҷҪиүІеҙҮжӢңе°ұжҳҜеҜ№вҖңзңҹе–„зҫҺвҖқзҡ„иҝҪжұӮпјҢзҷҪиүІжҲҗдёәи—Ҹж°‘ж—Ҹе®ЎзҫҺи§Ӯеҝөдёӯзҡ„дёҖз§ҚиұЎеҫҒе’Ңд»ЈеҗҚиҜҚпјҢзҷҪиүІиЎЁиҫҫдәҶдәә们зҡ„зңҹеҝғиҜҡж„ҸпјҢжҳҜзәҜжҙҒгҖҒеҗүзҘҘгҖҒжӯЈд№үе’Ңз№ҒиҚЈзҡ„иұЎеҫҒпјҢеңЁиҠӮж—ҘйҮҢе’Ңиө°дәІи®ҝеҸӢж—¶зҢ®дёҠзҷҪиүІзҡ„е“ҲиҫҫиЎЁиҫҫеҜ№иҖҒдәәе’Ңй•ҝиҫҲзҡ„е°Ҡ敬пјҢеҜ№еҗҢиҫҲе’ҢжҷҡиҫҲжқҘиҜҙеҸҲиЎЁзӨәзқҖзҫҺеҘҪзҡ„зҘқж„ҝгҖӮеҫҲжҳҫ然пјҢи—Ҹж°‘ж—ҸеҜ№зҷҪиүІзҡ„еҒҸзҲұпјҢдёҚд»…д»…жҳҜеӣ дёәй«ҳеҺҹдёҠз»Ҳе№ҙдёҚеҢ–зҡ„зҷҪйӣӘдёҺе…¶зӣёдјҙпјҢжңүзқҖеҜ№зҷҪиүІзҡ„敬з•Ҹж„ҹпјҢд№ҹдёҺи—Ҹж°‘ж—Ҹзҡ„еӣҫи…ҫеҙҮжӢңгҖҒзҘ–е…ҲеҙҮжӢңжңүзқҖдёҖе®ҡзҡ„ж–ҮеҢ–жёҠжәҗгҖӮ
гҖҖгҖҖиүІеҪ©зҡ„еӨҡз§ҚеӨҡж ·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иЎЁзӨәзқҖиҜӯиЁҖз¬ҰеҸ·зҡ„иҜқиҜӯпјҢжҚ®жңүе…із ”з©¶и—Ҹж—ҸеҺҶеҸІзҡ„еӯҰиҖ…еңЁеҜ№еҗҗи•ғж—¶жңҹзҡ„еҺҶеҸІж–Үд№Ұз ”з©¶дёӯеҸ‘зҺ°пјҢж—©еңЁи—Ҹж—ҸеҺҶеҸІдёҠзҡ„еҗҗи•ғж—¶д»ЈпјҢжңүдёҖдәӣеҺҶеҸІж–Үд№Ұе°ұз”ЁиүІеҪ©е‘ҪеҗҚпјҢзәўеҶҢдё»иҰҒжҳҜжҲ·зұҚзҷ»и®°еҶҢпјӣжё…еҶҢпјҲеӨ§зәўеҶҢпјүжҳҜдёҖз§ҚжӣҙдёәиҜҰз»Ҷзҡ„еҗҚеҶҢпјҢдёҚд»…жңүдәәеҗҚзҷ»и®°гҖҒз»ҹи®ЎпјҢиҖҢдё”иҝҳжңүзӣёе…ізҡ„з”°дә©гҖҒз•ңзү§гҖҒиҙўдә§ж•°йўқд»ҘеҸҠйҖ еҶҢеҗҚжҲ·еә”зјҙзәізҡ„иөӢзЁҺзӯүеҶ…е®№гҖӮзҷҪеҶҢжҳҜеЈ«е…өзҡ„иҠұеҗҚеҶҢпјҢй»„зәёеҶҢжҳҜи®°еҪ•зҺӢе‘Ҫе®ҳд№Ұж–ҮиҜ°зҡ„ж–Үд№ҰгҖӮиҝҷзңҹе®һең°еҸҚжҳ дәҶи—Ҹж—ҸзӨҫдјҡе…ёз« еҲ¶еәҰдёӯзҡ„еҲҶзұ»жғ…еҶөгҖӮ
гҖҖгҖҖ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ҸҰдёҖдёӘзү№зӮ№жҳҜз”Ёеҗ„з§Қеҗ„ж ·зҡ„дҝ®йҘ°е–»жқҘзӮ№зјҖд№ҰеҗҚпјҢд№ҰеҗҚзҡ„дҝ®йҘ°е–»иҫһи—»еҚҺдёҪпјҢдёҺе…ёзұҚеҶ…е®№е·§еҰҷең°жһ„жҲҗеҜ№еә”пјҢиҝҷз§ҚеҪўејҸеңЁдёӯеӣҪд№ҰзұҚиЈ…её§еҸІдёҠеҫҲжңүж°‘ж—Ҹзү№иүІгҖӮжҲ‘们д»ҺеҮ зұ»е‘ҪеҗҚеҸҜд»ҘзңӢеҮәе…¶и—Ҹж–ҮеҢ–зҡ„дё°еҜҢеӨҡеҪ©гҖӮз”ЁзҘһиҜқдәәзү©еҪўиұЎе‘ҪеҗҚзҡ„жңүгҖҠж–Үж®ҠйўӮВ·еӨ§жўөеӨ©йЎ¶йҘ°гҖӢгҖҒгҖҠе№ҝиЎҢзҒҢйЎ¶д»Ә规·жўөеӨ©зҪ‘з»ңгҖӢгҖҒгҖҠз©әиЎҢеЁұд№җд№Ӣзҗөзҗ¶гҖӢгҖҒгҖҠиҜ—жӯҢВ·еҜ»йҰҷд»ҷд№җгҖӢгҖҒгҖҠеҜҶйӣҶж„ҝж–ҮйҮҠВ·з»ҝ马з«ҘеӯҗгҖӢпјӣз”Ёең°зҗҶиҮӘ然зҺ°иұЎдҝ®йҘ°д№ҰеҗҚзҡ„жңүгҖҠ清规еҲ¶зәҰВ·еҸ–иҲҚеҲҶжҳҺд№ӢдёҪж—ҘгҖӢгҖҒгҖҠж…Ҳж°ҸеҲ№еңҹиөһВ·дҝЎж¶Ңж–°жңҲгҖӢгҖҒгҖҠжӯЈжі•жҖ»д№үжҳҺзҜҮВ·з”ҳйңІе…үгҖӢгҖҒгҖҠйҳІйӣ№жі•В·зҒ«йЈҺжј©гҖӢгҖҒгҖҠдҫӣжӣјиҚјзҪ—д»Ә规·дәҢиө„зІ®ж–№йӣҶгҖӢгҖҒгҖҠжҲҗе°ұиҖ…ж•…дәӢВ·еҰӮз§Ӣе”ӨйӣЁгҖӢгҖҒгҖҠзҒ«иҪ®жҳ“иЎҢжі•В·йң№йӣіиҪ°еЈ°гҖӢгҖҒгҖҠеҗүзҘҘиҜҚзұ»В·е…·зјҳеӯ”йӣҖжӮҰж„Ҹд№Ӣйӣ·еЈ°гҖӢгҖҒгҖҠе®—жҙҫе»әз«Ӣи®әВ·йЎ»ејҘеҰҷеә„дёҘгҖӢгҖҒгҖҠдёүеҚҒдә”дҪӣиөһе“ҒВ·жҒ’жІій•ҝжөҒгҖӢгҖҒгҖҠе®үеӨҡж”ҝж•ҷеҸІВ·д№Ұеҝ—д№Ӣжө·гҖӢгҖҒгҖҠиҜ—и®әВ·жө·и—ҸгҖӢзӯүпјӣеҖҹз”ЁжӨҚзү©жқҘе‘ҪеҗҚзҡ„е…ёзұҚжңүгҖҠеҮәдё–жі•иЁҖВ·иҺІиҠұжӯҢиҲһгҖӢгҖҒгҖҠиҜ—й•ңи®әиҝ°В·жқңй№ғд№ӢжӯҢгҖӢгҖҒгҖҠж–°иҜ—В·иңӮд№ӢиҠұиӢ‘гҖӢгҖҒгҖҠж јеҹ№з”ҳдё№еҚҙеҚ“жһ—еҜәеҝ—В·иөЎйғЁйӮЈиҫҫж ‘гҖӢгҖҒгҖҠеҰӮж„Ҹи—ӨгҖӢгҖҒгҖҠе‘Ҳж–ҮжҢҮеҚ—В·йӣӘжңҹйІңиҠұгҖӢгҖҒгҖҠжӣјйҷҖзҪ—д»Ә规·жӮүең°з©—гҖӢгҖҒгҖҠзӨјж•¬дәҢеҚҒдёҖеәҰжҜҚВ·жӮҰж„Ҹйқ’иҺІжқҹгҖӢгҖҒгҖҠзҘҲзҘ·ж–ҮВ·жһңзҶҹзҜҮгҖӢзӯүпјӣиҝҳжңүз”Ёзү©дҪ“е‘ҪеҗҚзҡ„е…ёзұҚжңүгҖҠ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еҝ—В·зҘһд№Ӣе·Ёйј“гҖӢгҖҒгҖҠжӣјйҷҖзҪ—иҜӯж•ҷВ·зҷҪжі•иһәд№ӢеЈ°гҖӢгҖҒгҖҠеңҶ满次第解и„ұВ·е№ҝејҖеӨ§еҜҶй—ЁеҢҷгҖӢгҖҒгҖҠеәҰжҜҚе…«йҡҫж•‘В·йҮ‘еҲҡз”Іиғ„гҖӢгҖҒгҖҠйҡҶжңөе–Үеҳӣж–ҮйӣҶВ·й»„йҮ‘й“ҫгҖӢгҖҒгҖҠи¶…еӨ©з•Ңд№Ӣе®қжўҜгҖӢгҖҒгҖҠеҫҒжңҚдёүз•ҢВ·жҷәж…§й“Ғй’©гҖӢгҖҒгҖҠи§үжі•дҝ®иЎҢВ·ж–ӯжҲ‘жү§д№ӢеҲ©еү‘гҖӢгҖҒгҖҠй•ҮеҺӢжҲҳйӯ”д»Ә规·黑иүІжҜ’з®ӯгҖӢзӯүзӯүгҖӮ
гҖҖгҖҖеҸҜд»ҘиҜҙи—Ҹж–Үе…ёзұҚдёӯеҜ№дҝ®йҘ°жҜ”е–»зҡ„иҝҗз”ЁиҢғеӣҙеҫҲе№ҝпјҢеҶ…е®№дё°еҜҢеӨҡеҪ©гҖӮеӨ§йҮҸзҡ„дҝ®йҘ°е–»еҢ…еҗ«жңүжө“еҺҡзҡ„е®—ж•ҷж–ҮеҢ–иүІеҪ©гҖӮеңЁдҝ®йҘ°е–»зҡ„иҝҗз”Ёдёӯжҡ—еҗ«зқҖдҪңиҖ…еҜ№дҝ®йҘ°еҪўиұЎзҡ„ж„ҹжғ…иүІеҪ©пјҢиЎЁзҺ°дәҶи—Ҹж—Ҹж–ҮеқӣиҝҷдёӘзҷҫиҠұеӣӯдёӯдәүеҘҮж–—иүізҡ„жҷҜиұЎпјҢеғҸдҝ®йҘ°е–»дёӯзҡ„вҖңзҷҪжі•иһәвҖқгҖҒвҖңй»„йҮ‘й“ҫвҖқгҖҒвҖңз»ҝиүІз«ҘеӯҗвҖқгҖҒвҖңй»‘иүІжҜ’з®ӯвҖқзӯүиүІеҪ©иҜҚпјҢеҸҲеҢ…еҗ«зқҖдҪңиҖ…еҜ№иүІеҪ©зҡ„зӢ¬зү№зҗҶи§Је’ҢжҳҺжҳҫзҡ„зҲұжҶҺжғ…ж„ҹпјҢиүІеҪ©еҸҲеҪўиұЎең°иЎЁзҺ°еҮәж–ҮзҢ®зҡ„дё»ж—ЁпјҢиүІеҪ©дёҺж–ҮдҪ“еңЁиҝҷйҮҢиЎЁиҫҫеҫ—еҰӮжӯӨжҒ°еҰӮе…¶еҲҶпјҢз»ҷиҜ»иҖ…з•ҷдёӢдәҶеӣһе‘іж— з©·зҡ„зҫҺж„ҹгҖӮ
гҖҖгҖҖи—Ҹж–Үе…ёзұҚзҡ„зүҲејҸжңүдёҖдёӘзү№зӮ№пјҢжңүдёҖйғЁеҲҶе…ёзұҚзҡ„жӯЈж–ҮеүҚжңүдёҖйҰ–жҲ–дёүдә”йҰ–дёҚзӯүжҲ–иҖ…жӣҙеӨҡйҰ–зҡ„иөһйўӮиҜҚгҖӮдёҖиҲ¬иөһйўӮиҜҚзҡ„ж•°йҮҸжҳҜж №жҚ®еҶ…е®№зҡ„еӨҡе°‘жқҘзЎ®е®ҡзҡ„пјҢеҰӮжһңеҶ…е®№е°‘зҡ„е…ёзұҚпјҢзӣёеҜ№жқҘиҜҙзҜҮйҰ–иөһйўӮиҜҚзҡ„ж–Үеӯ—д№ҹдёҚеӨҡпјҢеҰӮжһңеҶ…е®№еәһжқӮпјҢжӯЈж–Үзҡ„зҜҮе№…еҸҲй•ҝпјҢйӮЈд№ҲпјҢиөһйўӮиҜҚе°ұ жңүеӨҡйҰ–йўӮиҜҚз»„жҲҗпјҢ并且жңүзҡ„иөһйўӮиҜҚиҫһи—»еҚҺдёҪпјҢеғҸгҖҠйўҮзҪ—йјҗдј гҖӢзҡ„иөһйўӮиҜҚе°ұеӨҡиҫҫеҚҒдёғйҰ–гҖӮеҫҖеҫҖдёҖзҜҮиөһйўӮиҜҚд»ЈиЎЁзқҖиҜҘи‘—дҪңзҡ„зІҫеҚҺеҲӣдҪңзҡ„еҶ…е®№д№ӢдёҖпјҢеӣ жӯӨпјҢдҪңиҖ…жҳҜеҫҲжіЁйҮҚиөһйўӮиҜҚзҡ„еҲӣдҪңзҡ„гҖӮ
еңЁ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ҮәзүҲ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 ЎеҜ№д№ҹжҳҜдёҖйЎ№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е·ҘдҪңгҖӮеӨ§иҮҙжңүд»ҘдёӢеҮ дёӘж–№йқўзҡ„ж ЎеҜ№жі•пјҡпјҲ1пјүд№ҰзЁҝж ЎвҖ”вҖ”дё»иҰҒжҳҜе…Ёйқўе®ЎжҹҘд№ҰзЁҝзҡ„еҶ…е®№жҳҜеҗҰз¬ҰеҗҲеҮәзүҲиҰҒжұӮпјҢд»ҺжҖқжғіеҶ…е®№зҡ„еҮҶзЎ®жҖ§гҖҒжңүж— й”ҷеҲ«еӯ—е’Ңж–ӯеҸҘзҡ„жӯЈзЎ®жҖ§зӯүж–№йқўиҝӣиЎҢеҚ°еҲ·еүҚзҡ„еҮҶеӨҮе·ҘдҪңгҖӮпјҲ2пјүдёҠзүҲж ЎвҖ”вҖ”е°ұжҳҜжҠҠиҰҒйӣ•еҲ»зҡ„еҶ…е®№йҖҗдёҖиӘҠеҶҷеңЁе°ҶиҰҒиҙҙеңЁеҲ»зүҲдёҠзҡ„еҚ°еҲ·зәёдёҠпјҢйҖҡиҝҮж ЎеҜ№дҪҝеҫ—й”ҷгҖҒжјҸеӯ—еҫ—еҲ°зә жӯЈеҗҺеҶҚйӣ•еҲ»пјҢиҝҷж ·е°ұжҸҗй«ҳдәҶеҲ»зүҲзҡ„еҮҶзЎ®еәҰгҖӮпјҲ3пјүзүҲйқўж ЎвҖ”вҖ”ж №жҚ®еҲ»еҘҪзҡ„зүҲйқўиҝӣиЎҢи®Өзңҹзҡ„жЈҖжҹҘпјҢжЈҖжҹҘжңүж— й”ҷеӯ—е’Ңй”ҷгҖҒжјҸиЎҢзҡ„зҺ°иұЎгҖӮе…¶е®һпјҢеҲ»зүҲе·ҘдҪңжҳҜдёҖйЎ№еҚҒеҲҶиҫӣиӢҰзҡ„дҪ“еҠӣе’Ңи„‘еҠӣеҠіеҠЁпјҢзЁҚжңүз–ҸеҝҪе’ҢзІ—еҝғеӨ§ж„ҸеҸҜиғҪе°ұдјҡйҖ жҲҗй”ҷиҜҜ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ҝ…йЎ»и®Өзңҹе’Ңз»ҶиҮҙжүҚиғҪеҒҡеҘҪгҖӮпјҲ4пјүеЎ«иЎҘж ЎвҖ”вҖ”еңЁеҲ»зүҲиҝҮзЁӢдёӯеҮәзҺ°й”ҷиҜҜеҗҺпјҢе°ұйҮҮеҸ–жҢ–еҮәй”ҷеӯ—пјҢж·»иЎҘжӯЈзЎ®еӯ—зҡ„еҠһжі•гҖӮи—ҸеҢәйӣ•зүҲеҚ°еҲ·дёӯйҮҮеҸ–зҡ„ж ЎеҜ№ж–№жі•пјҢдёәеҮәзүҲеҗҲж јзҡ„еҚ°еҲ·е“Ғиө·дәҶз§ҜжһҒзҡ„жҠҠе…ідҪңз”ЁгҖӮ еңЁ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ҮәзүҲ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 ЎеҜ№д№ҹжҳҜдёҖйЎ№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е·ҘдҪңгҖӮеӨ§иҮҙжңүд»ҘдёӢеҮ дёӘж–№йқўзҡ„ж ЎеҜ№жі•пјҡпјҲ1пјүд№ҰзЁҝж ЎвҖ”вҖ”дё»иҰҒжҳҜе…Ёйқўе®ЎжҹҘд№ҰзЁҝзҡ„еҶ…е®№жҳҜеҗҰз¬ҰеҗҲеҮәзүҲиҰҒжұӮпјҢд»ҺжҖқжғіеҶ…е®№зҡ„еҮҶзЎ®жҖ§гҖҒжңүж— й”ҷеҲ«еӯ—е’Ңж–ӯеҸҘзҡ„жӯЈзЎ®жҖ§зӯүж–№йқўиҝӣиЎҢеҚ°еҲ·еүҚзҡ„еҮҶеӨҮе·ҘдҪңгҖӮпјҲ2пјүдёҠзүҲж ЎвҖ”вҖ”е°ұжҳҜжҠҠиҰҒйӣ•еҲ»зҡ„еҶ…е®№йҖҗдёҖиӘҠеҶҷеңЁе°ҶиҰҒиҙҙеңЁеҲ»зүҲдёҠзҡ„еҚ°еҲ·зәёдёҠпјҢйҖҡиҝҮж ЎеҜ№дҪҝеҫ—й”ҷгҖҒжјҸеӯ—еҫ—еҲ°зә жӯЈеҗҺеҶҚйӣ•еҲ»пјҢиҝҷж ·е°ұжҸҗй«ҳдәҶеҲ»зүҲзҡ„еҮҶзЎ®еәҰгҖӮпјҲ3пјүзүҲйқўж ЎвҖ”вҖ”ж №жҚ®еҲ»еҘҪзҡ„зүҲйқўиҝӣиЎҢи®Өзңҹзҡ„жЈҖжҹҘпјҢжЈҖжҹҘжңүж— й”ҷеӯ—е’Ңй”ҷгҖҒжјҸиЎҢзҡ„зҺ°иұЎгҖӮе…¶е®һпјҢеҲ»зүҲе·ҘдҪңжҳҜдёҖйЎ№еҚҒеҲҶиҫӣиӢҰзҡ„дҪ“еҠӣе’Ңи„‘еҠӣеҠіеҠЁпјҢзЁҚжңүз–ҸеҝҪе’ҢзІ—еҝғеӨ§ж„ҸеҸҜиғҪе°ұдјҡйҖ жҲҗй”ҷиҜҜ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ҝ…йЎ»и®Өзңҹе’Ңз»ҶиҮҙжүҚиғҪеҒҡеҘҪгҖӮпјҲ4пјүеЎ«иЎҘж ЎвҖ”вҖ”еңЁеҲ»зүҲиҝҮзЁӢдёӯеҮәзҺ°й”ҷиҜҜеҗҺпјҢе°ұйҮҮеҸ–жҢ–еҮәй”ҷеӯ—пјҢж·»иЎҘжӯЈзЎ®еӯ—зҡ„еҠһжі•гҖӮи—ҸеҢәйӣ•зүҲеҚ°еҲ·дёӯйҮҮеҸ–зҡ„ж ЎеҜ№ж–№жі•пјҢдёәеҮәзүҲеҗҲж јзҡ„еҚ°еҲ·е“Ғиө·дәҶз§ҜжһҒзҡ„жҠҠе…ідҪңз”ЁгҖӮ еңЁи—Ҹж–Үе…ёзұҚзҡ„еҮәзүҲ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 ЎеҜ№д№ҹжҳҜдёҖйЎ№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е·ҘдҪңгҖӮеӨ§иҮҙжңүд»ҘдёӢеҮ дёӘж–№йқўзҡ„ж ЎеҜ№жі•пјҡпјҲ1пјүд№ҰзЁҝж ЎвҖ”вҖ”дё»иҰҒжҳҜе…Ёйқўе®ЎжҹҘд№ҰзЁҝзҡ„еҶ…е®№жҳҜеҗҰз¬ҰеҗҲеҮәзүҲиҰҒжұӮпјҢд»ҺжҖқжғіеҶ…е®№зҡ„еҮҶзЎ®жҖ§гҖҒжңүж— й”ҷеҲ«еӯ—е’Ңж–ӯеҸҘзҡ„жӯЈзЎ®жҖ§зӯүж–№йқўиҝӣиЎҢеҚ°еҲ·еүҚзҡ„еҮҶеӨҮе·ҘдҪңгҖӮпјҲ2пјүдёҠзүҲж ЎвҖ”вҖ”е°ұжҳҜжҠҠиҰҒйӣ•еҲ»зҡ„еҶ…е®№йҖҗдёҖиӘҠеҶҷеңЁе°ҶиҰҒиҙҙеңЁеҲ»зүҲдёҠзҡ„еҚ°еҲ·зәёдёҠпјҢйҖҡиҝҮж ЎеҜ№дҪҝеҫ—й”ҷгҖҒжјҸеӯ—еҫ—еҲ°зә жӯЈеҗҺеҶҚйӣ•еҲ»пјҢиҝҷж ·е°ұжҸҗй«ҳдәҶеҲ»зүҲзҡ„еҮҶзЎ®еәҰгҖӮпјҲ3пјүзүҲйқўж ЎвҖ”вҖ”ж №жҚ®еҲ»еҘҪзҡ„зүҲйқўиҝӣиЎҢи®Өзңҹзҡ„жЈҖжҹҘпјҢжЈҖжҹҘжңүж— й”ҷеӯ—е’Ңй”ҷгҖҒжјҸиЎҢзҡ„зҺ°иұЎгҖӮе…¶е®һпјҢеҲ»зүҲе·ҘдҪңжҳҜдёҖйЎ№еҚҒеҲҶиҫӣиӢҰзҡ„дҪ“еҠӣе’Ңи„‘еҠӣеҠіеҠЁпјҢзЁҚжңүз–ҸеҝҪе’ҢзІ—еҝғеӨ§ж„ҸеҸҜиғҪе°ұдјҡйҖ жҲҗй”ҷиҜҜ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ҝ…йЎ»и®Өзңҹе’Ңз»ҶиҮҙжүҚиғҪеҒҡеҘҪгҖӮпјҲ4пјүеЎ«иЎҘж ЎвҖ”вҖ”еңЁеҲ»зүҲиҝҮзЁӢдёӯеҮәзҺ°й”ҷиҜҜеҗҺпјҢе°ұйҮҮеҸ–жҢ–еҮәй”ҷеӯ—пјҢж·»иЎҘжӯЈзЎ®еӯ—зҡ„еҠһжі•гҖӮи—ҸеҢәйӣ•зүҲеҚ°еҲ·дёӯйҮҮеҸ–зҡ„ж ЎеҜ№ж–№жі•пјҢдёәеҮәзүҲеҗҲж јзҡ„еҚ°еҲ·е“Ғиө·дәҶз§ҜжһҒзҡ„жҠҠе…ідҪңз”Ё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