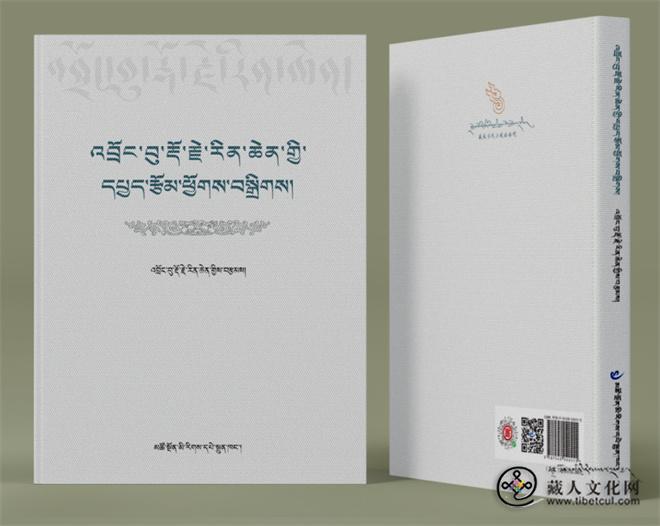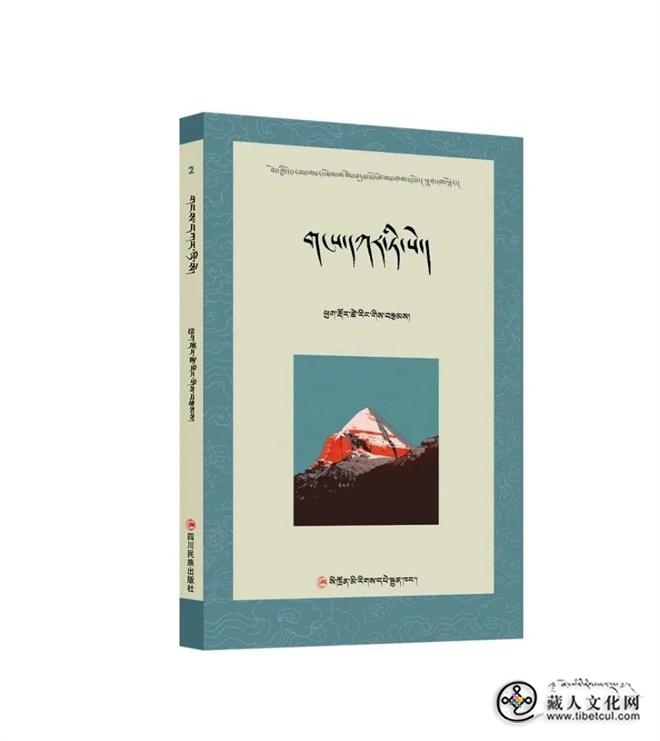ж—ҘеүҚпјҢгҖҠдёӯеӣҪиҜ—дәәгҖӢ2012е№ҙ第5еҚ·жҺЁеҮә“з”ҳеҚ—иҜ—жӯҢ”е°Ҹиҫ‘пјҢйҖүеҸ‘дәҶз”ҳеҚ—е·һиҝ‘е№ҙжқҘеңЁиҜ—жӯҢеҲӣдҪңдёҠйўҮжңүжҲҗз»©зҡ„зҺӢеҠӣзҡ„гҖҠз”ҳеҚ—еӨ§ең°гҖӢпјҲ5йҰ–пјүгҖҒзҺӢе°Ҹеҝ зҡ„гҖҠжҒӘе®ҲгҖӢпјҲ5йҰ–пјүгҖҒжүҺиҘҝжүҚи®©зҡ„гҖҠзҫҡеҹҺжӣІгҖӢпјҲ5йҰ–пјүгҖҒиҠұзӣӣзҡ„гҖҠзғӯзҲұгҖӢпјҲ5йҰ–пјүгҖҒзү§йЈҺзҡ„гҖҠйқ’и—Ҹж—Ҙи®°гҖӢпјҲ5йҰ–пјүгҖҒе”җдәҡзҗјгҖҠеҸҲеҲ°й»„жҳҸгҖӢпјҲ5йҰ–пјүе’ҢеҪӯдё–еҚҺзҡ„гҖҠеӨңиүІгҖӢпјҲ4йҰ–пјүзӯүеҠӣдҪңпјҢ并й…Қжңүи‘—еҗҚиҜ—дәәгҖҒж–ҮеӯҰиҜ„и®ә家黄жҒ©й№Ҹе…Ҳз”ҹдёәжӯӨж Ҹзӣ®еҶҷзҡ„дё“йўҳиҜ„и®әгҖҠз”ҳеҚ—иҜ—жӯҢпјҢзәҜеҮҖеҸҜйҘ®——з”ҳеҚ—дёғдәәз»„иҜ—з®ҖиҜ„гҖӢгҖӮ
з”ҳеҚ—иҜ—жӯҢпјҢзәҜеҮҖеҸҜйҘ®
й»„жҒ©й№Ҹ
жҲ‘дёҺдёҖдҪҚиҜ—жӯҢеҲҠзү©дё»зј–дәӨжөҒж—¶пјҢжӣҫи°Ҳиө·з”ҳеҚ—иҜ—дәәгҖӮжҲ‘иҜҙпјҡ“з”ҳеҚ—иҜ—дәәжһҒеҠӣеҲӣйҖ иҜ—жҖ§зІҫзҘһд№ӢзҫҺпјҢиҝҷжҳҜеҖјеҫ—иӮҜе®ҡзҡ„гҖӮеӣ дёә他们е°ұз”ҹжҙ»еңЁеӨ§зҫҺзҡ„йӣӘеұұиҚүеҺҹж№–жіҠд№Ӣй—ҙпјҢе°ұз”ҹжҙ»еңЁзәҜеҮҖзҡ„иҜ—жҖ§зҡ„жң¬з„¶дё–з•ҢйҮҢгҖӮ”иҝҷиҜқйҒ“еҮәдәҶжҲ‘еҜ№дәҺз”ҳеҚ—иҜ—дәәзҡ„е°ҠеҙҮ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зҫӨжңүзқҖж—әзӣӣз”ҹжңәзҡ„иҜ—дәәзҫӨдҪ“гҖӮ他们зәҜеҮҖгҖҒе®ү然ең°з”ҹжҙ»еңЁиҝҷеқ—е№ІеҮҖеҫ—еҸҜд»ҘйҘұйҘ®зҡ„еӨ©ең°пјҢжҲҗдёәиҜ—жӯҢзҒөжіүзҡ„з§ҜжһҒејҖжӢ“иҖ…гҖӮжҲ‘иҜ»з”ҳеҚ—иҜ—дәәзҡ„иҜ—пјҢжңүеҰӮйҘ®зқҖжё…еҶҪзҡ„жіүж°ҙгҖӮ他们д»ҺзәҜеҮҖзҡ„ең°ж–№жқҘпјҢиҜ—жғ…иҮӘ然д№ҹжҳҜзәҜеҮҖзҡ„гҖӮ
зҺӢеҠӣзҡ„гҖҠз”ҳеҚ—еӨ§ең°гҖӢжҜҸдёҖйҰ–йғҪдјјдёҖе№…з»қеҰҷзҡ„йЈҺжҷҜз”»гҖӮд»–жҸҸиҝ°з”ҳеҚ—еӨ§ең°д№ӢзҫҺеўғпјҢжңүеҰӮйҡҸйЈҺж‘Үжӣізҡ„йқ’иҚүпјҢжҲ–жҳҜд»Һж№–еІёеҗ№иҝҮжқҘзҡ„жңөжңөж¶ҹжјӘиҲ¬зҡ„иҠұйҰҷпјҢжҖ»иғҪз»ҷжҲ‘ж·Ўж·Ўзҡ„ж„ҹжҖҖгҖӮиҝҷж„ҹжҖҖжҳҜйӮЈиҲ¬зҡ„иҝ·дәәпјҢеҰӮжһңжҲ‘иғҪеҺ»иҝҷдәӣең°ж–№пјҢеҗҹиҜөиҜ—дәәз»қзҫҺиҪ»зҒөзҡ„иҜ—еҸҘпјҢдёҖе®ҡжҳҜйқһеёёжғ¬ж„Ҹзҡ„гҖӮжҲ‘еңЁд»–зҡ„иҜ—йҮҢжүҖиҜ»зҡ„дёҖеҲҮйЈҺзү©пјҢзҡҶдёҺе®ЎзҫҺдё»дҪ“зҡ„“жҲ‘”зӣёиҒ”гҖӮжҳҜдәІеҺҶдәҶеұұе·қд№ӢеҗҺзҡ„з”ұиЎ·зҡ„еҝғзҒөиөһеҸ№гҖӮиҝҷдәӣйқҷзҫҺд№Ӣең°жҳҜ“еңЁеұұеҢ…дёҠзҢҺзҢҺзҡ„з»Ҹе№ЎйҮҢпјҸдёҖжіўдёҖжіўпјҢз©ҝйҖҸиҝңиЎҢиҖ…зҡ„еҝғжҲҝ”зҡ„йҳҝдёҮд»“пјҢжҳҜ“еҘ№й»ҳй»ҳж— иЁҖпјҸеҚҙжҠҠдё–й—ҙжүҖжңүеҚ‘еҫ®зҡ„йӘЁеӨҙпјҢдёҖдёҖ收и—Ҹ”зҡ„иҘҝеұұпјҢжҳҜдёҺжҲ‘зҡ„з”ҹе‘Ҫзҡ„иҜёеӨҡ“жңүзҰҸдәҶ”дҪӣзӣёд№Ӣ“еҚҒдёҮдҪӣзҡ„йјҫеЈ°”зҡ„жүҺиҘҝеҘҮпјҢжҳҜ“жҲ‘еҝғжҖҖзҡ„ж¬ІеҝөпјҢиў«ж№–иҫ№зҡ„жё…йЈҺеҗ№ж•Ј”зҡ„е§ңжүҳжҺӘй’ҰпјҢжҳҜ“дҪ иҰҒж•ӣеЈ°еұҸж°”пјҸд»Ҙе…Қиў«жү‘йқўиҖҢжқҘзҡ„йқҷзҫҺдјӨе®і”зҡ„жүҺе°•йӮЈгҖӮзӯүзӯүпјҢд»ҘиҝҷдәӣзҫҺиҪ®зҫҺеҘӮд№Ӣең°дёәиҜ—йўҳпјҢжң¬иә«е°ұиҜҙжҳҺеӨ§иҮӘ然еҺҹжңүд№ӢиҜ—ж„ҸеӯҳеңЁгҖӮиҷҪ然дҪңдёәиҜ»иҖ…зҡ„жҲ‘жІЎжңүеҺ»иҝҮпјҢеҚҙд»ҺиҝҷзҘһжҖ§зҡ„жҸҸиҝ°дёӯж„ҹеҸ—еҲ°дәҶгҖҒзңӢеҲ°дәҶгҖӮйӮЈд№ҲпјҢеҝғзҒөдёҺйЈҺжҷҜзҡ„жҠөиҫҫд№Ӣи°ңпјҢе°ұеңЁзҒөж„ҹзҡ„жҹҗдёҖеӨ„дәӨжұҮдәҶгҖҒзӣёжҸЎзӣёжӢҘдәҶпјҢиҜ—дәәд№ҹе°ұжӯӨжҸӯејҖдәҶе®ғжҳҺдә®иҖҢжё…жҫҲзҡ„е®ЎзҫҺжғ…еўғгҖӮиҝҷжҳҜиҜ—еёҰжқҘзҡ„жё…зәҜпјҢеҰӮеҗҢгҖҠиҜ—з»ҸгҖӢзҡ„еӨ§е°Ҹйӣ…жӯҢпјҢжё…еҶҪзҡ„ж°ҙз•”з…§йүҙзҡ„пјҢжҳҜеӨ§ең°е‘ҲзҺ°зҡ„зҘһжҖ§гҖӮзҘһжҖ§дёҺиҜ—жҖ§з»“еҗҲдәҶпјҢдҫҝжҳҜзҒөйӯӮгҖӮ
зҺӢе°Ҹеҝ дҫқ然жҳҜз«ҷеңЁж•…еңҹдёҖи§’пјҢе®Ўи§Ҷиә«иҫ№зҡ„з”ҹе‘ҪжҷҜзҠ¶гҖӮгҖҠжҒӘе®ҲгҖӢжҳҜеҝғзҒөзҡ„жҒӘе®ҲпјҢз”ҳеҚ—жҳҜжё…иҙ«зҡ„пјҢйҷӨдәҶйӣӘгҖҒиҠҰиӢҮгҖҒиҝҳжңү“йҷҲж—§зҡ„иЎ—йҒ“иҫ№”зҡ„“йӮЈдәӣйЈҳиҗҪзҡ„еҸ¶еӯҗ”зӯүзӯүиҝҷдәӣ“иҪ»”зҡ„дәӢзү©гҖӮйҹ¶е…үжҳ“йҖқпјҢжҲ‘们йҖҗжёҗиӢҚиҖҒпјҢдёҖжғіиө·жңүдёҖдәӣз”ҹе‘Ҫд№ӢиҪ»зҡ„йҷӘдјҙпјҢеҚҙд№ҹжҳҜж— жӮ”зҡ„зғӯзҲұгҖҒе№ёзҰҸ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Ҳ‘们зҡ„жҒӘе®ҲпјҢжҳҜеҝғзҒөзҡ„жҒӘе®ҲпјҢ并дёҚдјҡиў«жө®еҚҺжүҖжү°гҖӮеңЁжҹҗдёҖдёӘжё…жҷЁпјҢд»–еҗ¬еҲ°дәҶдј—йёҹзҡ„жӯҢе”ұгҖӮйёҹе„ҝзҡ„е•Ғе•ҫпјҢи®©д»–зҡ„иҜ—жңүдәҶдә®е…үгҖӮиҝҷдә®е…үйҡҸйёҹеЈ°з’Җз’ЁгҖҒйҳ”иҝңпјҢд№ҹжңүдәҶиҜ—жң¬дҪ“ж„Ҹд№үзҡ„延伸пјҡ“зӣҙеҲ°е®ғ们ејҖеҸЈиҜҙиҜқпјҢзӣҙеҲ°жҲ‘еӣһеҪ’еӨ§ең°ж·ұеұӮ”гҖӮгҖҠз§ҒиҜӯгҖӢ并дёҚжҳҜдҪҺеҫҠзҡ„зӢ¬иҜӯпјҢиҖҢжҳҜеҜ№еҸҳе№»зҡ„дәәз”ҹеҸ‘еҮәдәҶзҡ„иҜҳй—®пјҢйӮЈдәӣжҖҖеҝөдёҺеҸ№жҒҜпјҢжҳ з…§и’ҷе°ҳзҡ„еҶ…еҝғгҖӮжҲ‘пјҢжҲ–жҲ‘们пјҢеҲ°еә•иҜҘжҖҺд№Ҳжҙ»иҝҮиҝҷдёҖз”ҹпјҹд№ҹи®ёпјҢиҝҮеҫҖдәҶзҡ„зҸҚиҙөпјҢжүҚд»Өдәәзј…жҖҖгҖӮ“йҡҗи—ҸеңЁйӣӘиҠұйҮҢеҫ®ејұзҡ„зҒ«е…үжҳҜе°‘е№ҙж—¶д»Јзҡ„жўҰжғіе’ҢзҫҺдёҪ”пјҢд»ҠеӨ©иҝҷдәӣжўҰжғіе’ҢзҫҺдёҪпјҢеңЁе“ӘйҮҢе‘ўпјҹиҝҷз§ҚдјӨж„ҹпјҢж„ҹеҗҢиә«еҸ—пјҒгҖҠе№ҝеңәгҖӢжңүеҲ«ж ·зҡ„е®ЎзҫҺе–»ж„ҸгҖӮе№ҝеңәжҳҜзӣӣиЈ…жғ…з»Әзҡ„е–»жҢҮпјҢд№ҹжҳҜйӣҶз»“е–§е“—з№ҒжқӮзҡ„з©әй—ҙжүҖеңЁгҖӮе®ғжүҖе‘Ҳжҳҫзҡ„пјҢжҳҜдәәзҡ„иҜёеӨҡжғ…ж„ҹгҖӮжё©жҡ–гҖҒеҶ°еҶ·пјҢйғҪжҳҜдәәз”ҹзҡ„ж»Ӣе‘іе„ҝгҖӮжҲ‘гҖҒд»–гҖҒ他们пјҢеңЁе№ҝеңәзҡ„游移йҮҢ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дёӘжЈӢеӯҗпјҢзҺ„з§ҳе’Ңйў„жғіпјҢзҡҶйҷ„зқҖе…¶дёҠдәҶгҖӮз”ҹжҙ»дёӯпјҢдәәдәәйғҪжңүжўҰпјҢгҖҠжўҰеўғгҖӢиҷҪиҜҙжҳҜжўҰеўғпјҢе…¶е®һжҳҜиҜ—дәәжңүж„Ҹи®ҫзҪ®зҡ„дёҖдёӘеҖҫеҗ‘жҖ§йў„и°ӢпјҢиҝҷдёӘйў„и°Ӣе®Ңе…ЁжңҚиҶәдәҺеҶ·жҠ’жғ…зҡ„йңҖиҰҒпјҢиҝҷз§ҚйңҖиҰҒпјҢдёҺзҲ¶дәІзҡ„е‘Ҫиҝҗйҷ…йҒҮзӣёе…іпјҢиҫӣй…ёйҒ“еҮәдәҶзҲ¶дәІиӢҰйҡҫзҡ„дёҖз”ҹгҖӮиҝҷж ·зҡ„йҒ“еҮәпјҢи®©жҲ‘ж„ҹеҲ°дәҶиҜ—дәәзҡ„е·§еҰҷд№Ӣи®ҫгҖӮ“иҖҢдјјд№ҺжҳҜеңЁеҸҰдёҖдёӘдё–з•ҢпјҢжҲ‘еӨҡд№Ҳжғізҙ§зҙ§жҠұдҪҸд»–йӮЈеҶ°еҮүзҡ„иә«дҪ“”гҖӮ“еҶ°еҮүзҡ„иә«дҪ“”е–»жҢҮзҲ¶дәІйҡҫд»ҘеӣһйҰ–зҡ„иӢҰйҡҫгҖӮиҝҷз§ҚжҖҖжғідјјзҡ„жӮІеҮүз»“е°ҫпјҢйңҮиҚЎдәәеҝғгҖӮ
жүҺиҘҝжүҚи®©жҳҜдёҖдҪҚж•Ҹж„ҹиҜ—дәәпјҢжңүж—¶еҖҷпјҢжҲ‘д»Һд»–зҡ„иҜ—дёӯиҜ»еҮәжӢүзҫҺж–ҮеӯҰйӯ”е№»зҺ°е®һдё»д№үе°ҸиҜҙе‘ійҒ“гҖӮжҜ”еҰӮеҚЎеҪӯй“Ғе°”гҖҒеҚҡе°”иө«ж–ҜзӯүиҜӯиЁҖзҡ„е№»жўҰиҲ¬еҸҷиҝ°гҖӮгҖҠзҫҡеҹҺжўҰгҖӢд»Һзҫҡзҡ„иә«дёҠпјҢи®©жҖқжғіи·іжқҘи·іеҺ»пјҢдёҖдјҡе„ҝжҳҜжҳҹжҳҹгҖҒз„°зҒ«гҖҒи—ҸйҮ‘иҺІпјҢдёҖдјҡе„ҝжҳҜеҹҺеёӮзҡ„й«ҳжҘјгҖҒй•ҝиҖ…гҖҒеңЁж–ҮеҢ–е№ҝеңәе’Ңз”өеҪұйҮҢиө°зқҖзҡ„жҲ‘иҮӘе·ұпјҢдёҖдјҡе„ҝеҸҲжҳҜзү§зҫҠдәәе’Ңйҳҝе°јзҺӣеҚҝеұұи„үгҖӮиҜ—зҡ„еӨ§йҮҸж„ҸиұЎзҪ—з»ҮпјҢжңүж„Ҹжһ„жҲҗдәҶиҮӘз”ұдёҺжқҹзјҡзҡ„еҜ№жҜ”гҖӮиҖҢиҝҷдәӣпјҢйғҪжҳҜжўҰзҡ„дёҚеҸҜйў„зҹҘгҖӮгҖҠи…ҫеҝ—иЎ—гҖӢж—ҘеӨҚдёҖж—Ҙең°жңүзқҖдёҺе…¶е®ғең°ж–№зӣёдјјзҡ„з”ҹжҙ»жң¬жҖҒпјҢиҝҷдёӘжң¬жҖҒе…¶е®һд№ҹжҳҜеңЁеҸҳеҢ–зҡ„гҖӮж— и®әзҷҪеӨ©гҖҒеӨңжҷҡпјҢиҝҷеҸҳеҢ–иЎЁиұЎж— жі•зңӢеҮәжқҘгҖӮдәӢе®һдёҠе·Іж”№еҸҳжҲ‘们зҡ„з”ҹе‘ҪгҖӮжҜ”еҰӮпјҢ“жҲ‘жҡ—жҒӢдәҶдёүе№ҙзҡ„еҘіеӯҗпјҢеҶҚд№ҹжІЎжңүеҮәзҺ°”гҖӮдёҚйҡҫиҜ»еҮә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йҰ–е…іж¶ү“ж—¶й—ҙ”жөҒеҸҳзҡ„жҸҸиҝ°пјҢиҝҷж ·жҸҸиҝ°жҳҜйқһеёёе·§еҰҷзҡ„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Қ•зәҜеҶҷдёҖдёӘжҷ®йҖҡиЎ—йӮЈд№Ҳз®ҖеҚ•гҖӮгҖҠ马иҺІж»©гҖӢзҡ„иҜ—ж ёпјҢжҳҜдёҖз§ҚзҫҺзҡ„дәӢзү©пјҢиҝҷдёӘзҫҺжң¬иә«пјҢе…¶е®һжҳҜеҸҜд»ҘжҢҪеӣһзҡ„гҖӮиҖҢдёҚеә”жҳҜиў«еғҸйҳіе…үйӮЈж ·ж”ҫйҖҗзҡ„гҖӮ“йӣЁеҗҺзҡ„з©әж°””“й»„жҳҸ”“еӨңиүІ”иҝҷж ·зҡ„ж—¶е…үйҖ’иҝӣпјҢд№ҹзқҖе®һи®©жҲ‘иҜ»еҲ°дәҶж—¶е…үд№Ӣ马зҡ„иҝ…жғҡгҖӮдёҖз§ҚзҫҺеҰӮдҪ•иғҪз•ҷдҪҸпјҹ“жҲ‘жҳҜдёҚжҳҜеә”иҜҘеғҸдёӘз”·дәәпјҢжҠҠеҘ№ж…ўж…ўең°жҗӮеңЁжҖҖйҮҢ”пјҢиҝҷж ·зҡ„еҸҚй—®пјҢи®©иҜ—еўһеҠ дәҶеҺҡйҮҚгҖӮжЎ‘еӨҡжІі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жқЎд»ӨиҜ—дәәдә§з”ҹйҒҗжғізҡ„жІігҖӮеңЁиҝҷжқЎжІіиҫ№пјҢиҜ—дәәдёҺдј—з”ҹдёҖж ·пјҢд№ҹжҳҜеҗҢж ·зҡ„жІҗжөҙгҖҒеһӮжіЈгҖҒжҳҸзқЎпјҢж°ҙеЈ°йҷӘзқҖиҜ—дәәдёүеҚҒеӨҡе№ҙпјҢдҪҶеҶөе‘ідёҚе°ҪзӣёеҗҢгҖӮдёҖдәӣеЈ°йҹіиў«зЁҖйҮҠе°ҪдәҶпјҢдёҖдәӣд»ҚеҰӮдј иҜҙиҲ¬з•ҷеңЁдәҶеҝғзҒөж·ұеӨ„еј•еҸ‘е№»жғі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іЁйҮҚзІҫзҘһд»·еҖјзҡ„иҝҮзЁӢгҖӮжңүдәҶиҝҷдёӘзІҫзҘһд»·еҖјпјҢдәәз”ҹе°ұжІЎжңүзҷҪиҝҮгҖӮеңЁгҖҠиҫҫеЁІи°ЈгҖӢдёӯпјҢд»Ҙ“еҺҹеҲқзҡ„”ж„ҸиұЎдҪ“йӘҢпјҢжқҘжұӮиҜҒй•ңеғҸејҸзҡ„ж„ҹжӮҹгҖӮи®©и¶…йӘҢе’ҢдәІеҺҶжҲҗдёәзҹҘжҖ§пјҢе№»еҸҳдёҖз§Қзұ»дјјзңҹе®һзҡ„жғ…еўғгҖӮиҝҷжҳҜиҜ—зҡ„дё»и§ӮеҢ–иүІеҪ©зҡ„зӘҒжҳҫпјҢе®ғдёҺиҮӘиә«з”ҹе‘ҪдҪ“жӮҹе…іиҒ”гҖӮдёҖз§ҚдҪӣ家зҡ„иҪ®еӣһж„ҹпјҢе……зӣҲеңЁиҜ—зҡ„ж„Ҹи•ҙдёӯгҖӮжүҺиҘҝжүҚи®©еҲӣдҪңи®©жҲ‘зңӢеҲ°зҡ„дёҚеҸӘжҳҜиҜӯиЁҖзҡ„йҷҢз”ҹеҢ–ж•ҲжһңпјҢд№ҹеҗҢж—¶зңӢеҲ°дәҶд»–зҡ„йқһеҮЎзҡ„ж–ҮеӯҰеҠҹеҠӣпјҢд»–жңүж—¶еҮәе…¶дёҚж„Ҹзҡ„иҜӯеўғпјҢи®©жҲ‘жғҠеҸ№гҖӮ
иҠұзӣӣзҡ„гҖҠзғӯзҲұгҖӢпј•йҰ–пјҢд№ҹжҳҜеҜ„жүҳжғ…ж„ҹдәҺз”ҳеҚ—еӨ§ең°пјҢеҫҲеӨ§зҡ„жҲҗеҲҶпјҢжқҘиҮӘдәҺзҗҶжғіеҢ–пјҢд№ҢжүҳйӮҰж„Ҹе‘іжө“еҺҡгҖӮиҝҷз§Қж„Ҹе‘іжҳҜеҺҶеҸІз§Ҝж·Җзҡ„еӣһеҝҶпјҢжҳҜз”ҹе‘Ҫзҡ„еҝғеўғеҜ№дәҺеҺҶеҸІжғ…еўғзҡ„еӨҚзҺ°гҖӮз»ҸйӘҢдҪңдёәдёҖз§Қе®ЎзҫҺеҲӣйҖ пјҢеңЁд»–зҡ„иҜ—дёӯе‘ҲзҺ°еҮәз«ӢдҪ“гҖӮгҖҠзј“ж…ўиЎҢиө°гҖӢдёүж®өејҸзҡ„е’ҸеҸ№и°ғпјҢеҸҷеҶҷеІҒжңҲзҡ„жІ§жЎ‘д№ӢеҸҳгҖӮд»Һж—¶й—ҙзҡ„з»ҙеәҰдёҠзңӢпјҢеҢ…и•ҙиҝҮеҺ»зҺ°еңЁе’ҢжңӘжқҘгҖӮиҜ—дәәеңЁдҪ“йӘҢжңҖж·ұзҡ„“жғ…еўғ”йҮҢдјёзј©дёҖз§ҚжҖқиҖғпјҢжҙ»и„ұдәҶиЎҢиө°иҝҷдёӘиЎҢдёәпјҢиҜ—ж„Ҹжө“йҶҮгҖӮгҖҠеӨңе®ҝз”ҳеҚ—гҖӢпјҢзқҖйҮҚжҳҜеӯӨзӢ¬зҡ„жӯҢеҗҹпјҢеҚҠдёӘжңҲдә®гҖҒдёҖеҢ№й©¬гҖҒдёҖдёӘйҒҘиҝңзҡ„ж•…д№ЎгҖҒдёҖдёӘиҜ—дәәпјҢйғҪеҢ–дҪңдәҶдёҖеҸҘиҪ»зҒөзҡ„жӯҢеЈ°пјҢйқҷйқҷйЈҳеқ жҖқеҝөйҮҢгҖӮгҖҠзӘ—еӨ–гҖӢйҖҸи§ҶеҮә“еҝҪйҡҗеҝҪзҺ°зҡ„дә‘йӣҫ”жңүеҰӮз”ҹжҙ»зҡ„йҡҗз—ӣпјҢиў«ж—¶ж—¶и§Ұзў°гҖҒи®°жҖҖгҖӮгҖҠзғӯзҲұгҖӢдёӯзҡ„“жҲ‘”пјҢиҷҪ然“йҡ”зқҖжӢҘжҢӨзҡ„дәәзҫӨе’ҢеҳҲжқӮзҡ„еЈ°йҹі”пјҢеҚҙдёҚиғҪеҝҳжҖҖйӮЈе®Ғйқҷзҡ„йӣӘеұұпјҢйӮЈйҮҢиҷҪ然иҙ«зҳ пјҢеҚҙжңүзқҖжё©жҡ–зҡ„зҲұе’Ңж…°и—үгҖӮгҖҠйҮҺиҠұгҖӢжҳҜжҲ‘е–ңж¬ўзҡ„дёҖйҰ–пјҢеҚ‘еҫ®зҡ„йҮҺиҠұпјҢдёәдҪ•иғҪеј•иө·иҜ—дәәжіЁж„Ҹпјҹд№ҹи®ёпјҢеңЁиҮӘжҖңдёӯзӣёдә’жҳ з…§еҮәз”ҹе‘Ҫжң¬зӣёзҡ„иҒ”зі»жқҘгҖӮиҝҷз§ҚиҒ”зі»еҸҲжҳҜеҚҡеӨ§зҡ„гҖҒж…ҲжӮҜзҡ„гҖӮйҮҺиҠұпјҢиҮӘз”ҹиҮӘзҒӯпјҢж— дәәй—®жҙҘпјҢеҸӘжңүеӨ©ең°зҡ„еҜ’жҡ–пјҢи®©е®ғ们жҲҗдёәйЎ·еҲ»д№ӢзҫҺзҡ„еӯҳеңЁгҖӮдҪҶе®ғ们еқҡе®ҡ“еҘҪеҘҪжҙ»зқҖ”пјҢжӯЈжҳҜиҝҷз§Қз”ҹе‘Ҫзҡ„д»·еҖји®ӨеҗҢпјҢи®©жҲ‘们жүҫеҲ°дәҶжҹҗз§ҚеҸҜиҙөзҡ„еӯҳеңЁгҖӮеңЁиҝңиЎҢи·ҜдёҠпјҢжҲ–иҖ…иҜҙжҳҜеңЁдәәз”ҹзҡ„иЎҢзЁӢдёӯпјҢеҰӮдҪ•зңӢеҫ…з”ҹе‘Ҫд»·еҖјгҖӮиҜ»йҮҺиҠұеҚіиғҪжүҫеҲ°зӯ”жЎҲгҖӮ
зү§йЈҺгҖҠйқ’и—Ҹж—Ҙи®°гҖӢзқҖйҮҚеҶҷж„ҹеҸ—гҖӮеңЁгҖҠеҚҲеҗҺ桑科гҖӢд»–иҝҷж ·еҶҷзүҰзүӣпјҡ“йӮЈдәӣй»‘иүІзҡ„й—Әз”өпјҸеңЁзңјзңёйҮҢзЁҚдҪңеҒңйЎҝпјҸдҫҝйҡҸж·ұз§Ӣзү§еҪ’зҡ„еҸЈе“ЁпјҸе‘је•ёиҖҢеҺ»”ж·ұз§Ӣзҡ„иҚүеҺҹжҳҜеҶ·иүІи°ғзҡ„пјҢиҜ—дәәзҡ„жғ…ж„ҹпјҢеҲҷйҡҸзқҖ桑科иҚүеҺҹиҖҢйЈһжү¬йЈҳиҚЎгҖӮ“жҲ‘зҡ„зҒөйӯӮйҒ—еӨұеңЁе“ӘйҮҢпјҸдёҖеҲҮйғҪе®ҡж јеңЁжЎ‘科黄жҳҸзҡ„йӣЁе№•дёӯпјҸиҖҢжҲ‘е·ІжғідёҚиө·пјҸдҪӣеүҚдё–дҝ®иЎҢзҡ„еҫҖдәӢ”иҜҳй—®дёӯжңүз”ҹе‘ҪзңҒи§үзҡ„еҠӣйҮҸгҖӮгҖҠиә«еңЁзҫҡеҹҺгҖӢпјҢеҶҷиҝңеҺ»зҡ„зҫҡпјҢеҶҷж¶ҲеӨұзҡ„жө·еӯҗпјҢеҶҷзҺ°д»ЈеҢ–еҜ№еӨ§ең°зҡ„жҠўжҺ пјҢеҶҷз»қзҒӯдәәжң¬зҡ„еҷ©жўҰгҖӮж„ҸеңЁе…ҲпјҢи®©жҖқжғіе…Ҳе…Ҙдёәдё»пјҢжҳҜиҝҷйҰ–иҜ—зҡ„зү№зӮ№гҖӮгҖҠеҪ“е‘ЁжІҹзҡ„йҳіе…үгҖӢеҶҷдёҖз§Қз”ҹе‘Ҫзҡ„й—ІйҖӮгҖӮиҝҷй—ІйҖӮпјҢдёҚжҳҜиҜ—дәәеёёеёёеҜ„жҖҖзҡ„жў…е…°з«№иҸҠжҲ–йЈҺиҠұйӣӘжңҲ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еҸӘ“иҷ«е„ҝ”пјҡ“жҲ‘дё”еҒҡиҝҷиҷ«е„ҝзҡ„жӮ й—ІпјҸеҝҳеҚҙдәҶе°ҳдё–зҡ„жө®иәҒ”пјҢиҷ«е„ҝжҳҜејұе°Ҹзҡ„з”ҹе‘ҪдҪ“пјҢиҝҷдёӘж„ҸиұЎиҝҗз”Ёзҡ„еҫҲеҘҪпјҢд№ҹдҪ“зҺ°дәҶиҜ—дәәеҚ‘еҫ®е’ҢиҮӘжҲ‘ж…°жҖҖд№Ӣе®үйҒ“е®ҲиҠӮжң¬жҖҒгҖӮгҖҠиҝңжңӣиӢҘе°”зӣ–иҚүеҺҹгҖӢгҖҠжҷЁжӣҰдёӯзҡ„е·ҙиҘҝзү§еңәгҖӢд№ҹеҗ‘жҲ‘们еұ•зӨәдәҶиҜ—дәәжғ…жҖҖпјҡж јжЎ‘дёҺеҚ“зҺӣгҖҒжңҲдә®дёҺжў…еҚ“гҖӮдё»е®ўдҪ“зҡ„移жғ…гҖҒдә’жҳ пјҢиҫғеҘҪиҝҗз”ЁиҚүеҺҹзү№жңүзҡ„иҜ—жҖ§е…ғзҙ пјҢеҮёжҳҫдәҶз”ҳеҚ—иҜ—жӯҢең°еҹҹзү№иүІгҖӮ
е”җдәҡзҗјзҡ„гҖҠеҸҲеҲ°й»„жҳҸгҖӢж·Ўж·ЎжҠ’еҶҷеҲ«жңүдёҖз•Әж»Ӣе‘ігҖӮ“жЎҢеӯҗеҜ№йқў”зҡ„д»–пјҢеҚҙжҳҜ“йӮЈйҒҘиҝңзҡ„ең°ж–№”пјҢиҜӯиЁҖзҡ„еҸҚеҗ‘е–»д№үпјҢеҗҜеј•жҠ’еҶҷгҖӮиҝ‘дёҺиҝңзҡ„еҸҚеҗ‘пјҢи®©й»„жҳҸе……ж»ЎдәҶдјӨж„ҹгҖӮй»„жҳҸзҡ„дәәз”ҹд№Ӣе–»пјҢеҫҲжҳҺжҳҫйҒ“еҮәгҖӮгҖҠжҲ‘иә«дҪ“йҮҢдҪҸзқҖдёҖзҫӨеӯ©еӯҗгҖӢиҝҷйҰ–иҜ—жҲ‘еҫҲе–ңж¬ўпјҢиҜ—дәәжҠҠжҖқз»ӘдёҮеҚғзҡ„зҠ¶жҖҒеҶҷеҫ—еҰӮжӯӨд№ӢеҰҷпјҢд»ӨжҲ‘жӢҚжЎҲеҸ«з»қгҖӮ“жҲ‘иә«дҪ“йҮҢдҪҸзқҖдёҖзҫӨеӯ©еӯҗпјҸе’ҢжҲ‘еҗҢе№ҙеҗҢжңҲеҗҢж—ҘеҗҢеІҒ”гҖӮеӯ©еӯҗжҳҜзҫҺеҘҪж–°з”ҹгҖҒж°ёжҒ’зҡ„иұЎеҫҒпјҢд№ҹжҳҜз”ҹжңәж—әзӣӣзҡ„е–»иұЎгҖӮиҜ»иҝҷйҰ–иҜ—пјҢи®©жҲ‘жғіиө·е®үеҫ·жӢүеҫ·зҡ„еҸҘеӯҗ“еӯ©еӯҗзҡ„жүӢжҳ з…§дәҶжҲ‘й»‘жҡ—зҡ„жүӢ”д№ӢзҫҺеҘҪгҖӮиҝҷз§ҚзҘһжҖ§еҲӣйҖ пјҢйҰ–е…ҲжҳҜеҜ№дәҺзҘһжҖ§зҡ„и®ӨеҗҢгҖӮе®ғдёҚжҳҜиҷҡж— йЈҳзјҲзҡ„еӯҳеңЁпјҢиҖҢжҳҜзәҜжҙҒзҡ„гҖҒдё°жІӣзҡ„гҖҒзғӯзғҲзҡ„еӯҳеңЁгҖӮжңүеҰӮжҳҘйЈҺжөҙжҙ—дәҶиә«дҪ“жҜҸдёҖеӨ„иҗҢз”ҹзҡ„еҠӣйҮҸгҖӮгҖҠз§ӢеӨ©е°ұиҰҒжқҘдёҙгҖӢгҖҠеғҸд»–дёҖж ·гҖӢгҖҠжҖҖжҠұгҖӢзӯүпјҢд№ҹжҳҜйҖҡиҝҮж—¶еәҸзҡ„жҢӘз”ЁпјҢжқҘеҶҷз”ҹе‘Ҫзҡ„еҝғеўғгҖӮеҰӮ“з§ӢеӨ©”“й»„жҳҸ”зӯүпјҢжұӮиҜҒдәәз”ҹзҡ„жҹҗз§ҚеұҖдҝғеёҰжқҘзҡ„жҖқиҖғгҖӮиҪ»зҡ„“еҸ¶еӯҗ”пјҢжҳҜе®ЎзҫҺи§Ӯз…§жңҖзӣҙжҺҘзҡ„пјҢе®ғеҢ…еҗ«зӣҙи§үгҖҒжғіиұЎгҖҒиҒ”жғігҖҒеӣһеҝҶпјҢе®ғдјјй•ңеӯҗгҖӮеә„еӯҗжүҖи°“зҡ„“и§ҒзӢ¬”пјҢе°ұжҳҜе°Ҷдё»дҪ“зҡ„еҶ…и§ҶдҪңз”ЁеҠ е…Ҙе…¶дёӯдәҶгҖӮ
еҪӯдё–еҚҺзҡ„иҜ—пјҢжңүеҰӮзҺ°д»Ји°ЈжӣІпјҢжңәеҰҷгҖҒзІҫе·§пјҢиӢҘи°ұжӣІпјҢеҲҷдјјжңүзқҖе°Ҹи°ғзҡ„ж°‘й—ҙжӣІгҖӮе…¶е®һпјҢиҝҷж ·зҡ„иҜ—пјҢжңҖжҳҜйҡҫеҶҷпјҢйЎ»иҰҒжңү“жңәи¶Ј”еӯҳеңЁгҖӮиҖҢдё”пјҢжңҖйҖӮеҗҲең°еҹҹзҡ„д№Ўдҝҡж°‘и°Је”ұеҗҹгҖӮгҖҠеӨ§йӣЁгҖӢдёӯзҡ„еҸҘеӯҗпјҡ“йӣЁд»ҺдёңйқўжқҘпјҸйӣЁд»ҺиҘҝйқўжқҘпјҸйӣЁд»ҺеҚ—йқўжқҘпјҸйӣЁд»ҺеҢ—йқўжқҘ”пјҢжңүеҰӮжұүд№җеәңеҸӨиҫһгҖҠжұҹеҚ—гҖӢгҖӮжӯӨзұ»иҜ—жӯҢпјҢжңҖиғҪжҺҘиҝ‘еҪ“д»ЈиҜ—жӯҢзҡ„еҸЈиҜӯеҢ–ж•ҲжһңгҖӮжұүд№җеәңеҸӨиҫһиҜ—пјҢеёёеёёйҮҮз”Ёзҡ„жҳҜжҜ”е…ҙдёҺеҸҢе…ізӯүжүӢжі•гҖӮеҰӮпјҡ“жұҹеҚ—еҸҜйҮҮиҺІпјҢиҺІеҸ¶дҪ•з”°з”°пјҢйұјжҲҸиҺІеҸ¶й—ҙгҖӮйұјжҲҸиҺІеҸ¶дёңпјҢйұјжҲҸиҺІеҸ¶иҘҝпјҢйұјжҲҸиҺІеҸ¶еҢ—пјҢйұјжҲҸиҺІеҸ¶еҚ—гҖӮ”жҳҫеҫ—жҙ»жіјгҖҒиҮӘ然гҖҒжңүи¶ЈгҖӮеҸҘејҸеӨҚжІ“иҖҢз•ҘжңүеҸҳеҢ–пјҢжҳҜгҖҠиҜ—з»ҸгҖӢзҡ„дј з»ҹжүӢжі•пјҢиҜ—дәәиғҪе°Ҷиҝҷз§Қд№җеәңжүӢжі•з”ЁеңЁеҪ“д»ЈиҜ—жӯҢеҲӣдҪңдёӯпјҢжҳҜйқһеёёеҘҪзҡ„继жүҝпјҢдёҚеҫ—дёҚд»ӨжҲ‘еҲ®зӣ®зӣёзңӢпјҢдё”жңүзқҖдёҖе®ҡзҡ„еҗҜиҝӘгҖӮдҪҶйЎ»иҝҗз”Ёеҫ—иҮӘ然гҖҒдёҚз•ҷйӣ•еҮҝд№Ӣиҝ№гҖӮиҝҷйҰ–иҜ—и®©дәәжғіеҲ°дёҺйӣЁеЈ°зӣёдәІгҖҒзӣёе’ҢгҖҒзӣёеә”зҡ„жғ…еўғгҖӮйӣЁзҡ„з”ҹжңәпјҢйӣЁзҡ„зЁ еҜҶпјҢйӣЁзҡ„жҪҮжҙ’пјҢйғҪжҳҜдёҖз§ҚеҰҷи¶ЈжЁӘз”ҹзҡ„дәәзҡ„з”ҹжҙ»жң¬жҖҒгҖӮгҖҠиЎЁе§җгҖӢгҖҠзәўзўҢзўЎгҖӢгҖҠеӨңиүІгҖӢзӯүпјҢзқҖеўЁдёҚеӨҡпјҢеҚҙиҜ—ж„Ҹж·ұиҝңпјҢз»ҷиҜ»иҖ…з•ҷдёӢдәҶзӣёеҪ“еӨ§зҡ„иҒ”жғіз©әй—ҙгҖӮеҪӯдё–еҚҺзҡ„иҜ—еӨҡиҮӘ然д№ӢжҖҒпјҢдёҺйҖ еҢ–зӣёйҖҡпјҢдёҺеҝғеўғзӣёдҫ”гҖӮиҜ—иҷҪзҹӯпјҢеҚҙеӨ§жңүе№ҝиҝңзІҫеҫ®д№ӢеҠҝгҖӮ
з”ҳеҚ—иҜ—жӯҢпјҢзәҜеҮҖеҸҜйҘ®гҖӮ
гҖҠдёӯеӣҪиҜ—дәәгҖӢ2012е№ҙ第5еҚ·“з”ҳеҚ—иҜ—жӯҢ”е°Ҹиҫ‘дҪңиҖ…з®Җд»Ӣпјҡ
зҺӢеҠӣпјҢз”·пјҢжұүж—ҸпјҢз”ҳиӮғйҖҡжёӯдәәгҖӮжңүиҜ—жӯҢгҖҒж•Јж–ҮгҖҒиҜ„и®әи§ҒиҜёзңҒең°зә§жҠҘеҲҠжқӮеҝ—еҸҠж°‘еҲҠгҖӮгҖҠз”ҳеҚ—ж—ҘжҠҘгҖӢеүҜеҲҠзј–иҫ‘гҖӮ
зҺӢе°Ҹеҝ пјҢз”·пјҢи—Ҹж—ҸпјҢз”ҳиӮғз”ҳеҚ—дәәпјҢ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дјҡе‘ҳгҖӮдҪңе“Ғж•Ји§ҒдәҺгҖҠеӨ§е®¶гҖӢгҖҒ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гҖӢгҖҒгҖҠйқ’е№ҙ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еұұиҠұгҖӢзӯүеӨҡ家еҲҠзү©пјҢе…ҘйҖүгҖҠдёӯеӣҪе№ҙеәҰиҜ—жӯҢ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зІҫйҖүйӣҶ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еӣҪеҫ®еһӢе°ҸиҜҙжҺ’иЎҢжҰңгҖӢзӯү10дҪҷз§ҚйҖүжң¬гҖӮи‘—жңүиҜ—йӣҶдёӨйғЁпјҢж•Јж–ҮйӣҶдёҖйғЁгҖӮ
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и—Ҹж—ҸпјҢ1972е№ҙз”ҹпјҢз”ҳиӮғз”ҳеҚ—дәәгҖӮе·ІеңЁ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ҠиҜ—жӯҢжҠҘжңҲеҲҠгҖӢгҖҠиҜ—йҖүеҲҠгҖӢгҖҠжҳҹжҳҹиҜ—еҲҠгҖӢгҖҠиҘҝи—Ҹж–ҮеӯҰгҖӢзӯүеӣҪеҶ…жҠҘеҲҠжқӮеҝ—дёҠеҸ‘иЎЁж–ҮеӯҰдҪңе“Ғиҝ‘еӣӣеҚҒдёҮеӯ—гҖӮжӣҫиҺ·“иҜ—зҘһжқҜ”е…ЁеӣҪиҜ—жӯҢеҘ–гҖҒз”ҳиӮғзңҒе°‘ж•°ж°‘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й“ңеҘ”马еҘ–гҖҒз”ҳиӮғзңҒ第еӣӣеұҠж•Ұз…Ңж–ҮиүәеҘ–гҖҒз”ҳиӮғзңҒ第дә”еұҠе°‘ж•°ж°‘ж—Ҹж–ҮеӯҰеҘ–гҖҒгҖҠйЈһеӨ©гҖӢеҚҒе№ҙж–ҮеӯҰеҘ–гҖҒгҖҠиҘҝи—Ҹж–ҮеӯҰгҖӢе№ҙеәҰдҪңе“ҒеҘ–гҖӮдҪңе“Ғе…ҘйҖүеӨҡйғЁиҜ—жӯҢе№ҙйҖүе’ҢжҖ»з»“жҖ§иҜ—йӣҶгҖӮз”ҳиӮғзңҒдҪңеҚҸдјҡе‘ҳгҖӮ
иҠұзӣӣпјҢи—Ҹж—ҸпјҢз”ҳиӮғз”ҳеҚ—дәәгҖӮдҪңе“Ғж•Ји§Ғ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Ҡйқ’е№ҙж–ҮеӯҰгҖӢгҖҠжҳҹжҳҹиҜ—еҲҠгҖӢгҖҠйЈһеӨ©гҖӢгҖҠиҜ—жӯҢжңҲеҲҠгҖӢгҖҠеІҒжңҲгҖӢгҖҠж•Јж–ҮиҜ—гҖӢгҖҠиҜ—жҪ®гҖӢгҖҠиҘҝи—Ҹж–ҮеӯҰгҖӢзӯүеҲҠпјҢжӣҫиҺ·е…ЁеӣҪеҚҒдҪіж•Јж–ҮиҜ—дәәеҘ–гҖҒ第дә”еұҠз”ҳиӮғзңҒе°‘ж•°ж°‘ж—Ҹж–ҮеӯҰеҘ–гҖҒ第дә”еұҠдёӯеӣҪж•Јж–ҮиҜ—еӨ©й©¬еҘ–зӯүеӨҡдёӘеҘ–йЎ№пјҢеҸӮеҠ иҝҮ第дәҢеұҠз”ҳиӮғдҪңеҚҸй«ҳз ”зҸӯгҖҒ第дёғеұҠе’Ң第еҚҒеұҠе…ЁеӣҪж•Јж–ҮиҜ—笔дјҡ,и‘—жңүиҜ—йӣҶгҖҠдёҖдёӘдәәзҡ„и·ҜйҖ”гҖӢпјҢж•Јж–ҮйӣҶгҖҠеІҒжңҲз•ҷз—•гҖӢгҖӮзҺ°дёәз”ҳиӮғзңҒдҪң家еҚҸдјҡдјҡе‘ҳпјҢгҖҠжҙ®е·һж–ҮеӯҰгҖӢзј–иҫ‘гҖӮ
зү§йЈҺпјҢеҺҹеҗҚиөөеҮҢе®ҸпјҢи—Ҹж—ҸгҖӮе·ІеңЁ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ҳҹжҳҹ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йқ’е№ҙ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еӣҪиҜ—дәә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еӣҪиҜ—жӯҢ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дҪң家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дё–з•ҢгҖӢгҖҒгҖҠйЈһеӨ©гҖӢзӯүеҸ‘иЎЁж–°иҜ—еҸҠж•Јж–ҮиҜ—ж•°зҷҫзҜҮпјҲйҰ–пјүпјҢдҪңе“Ғе…ҘйҖүеӨҡз§ҚиҜ—жӯҢеҸҠж•Јж–ҮиҜ—дё“йӣҶгҖӮзі»з”ҳиӮғзңҒдҪң家еҚҸдјҡдјҡе‘ҳпјҢдёӯеӨ–ж•Јж–ҮиҜ—еӯҰдјҡзҗҶдәӢгҖӮ
е”җдәҡзҗјпјҢеҘіпјҢи—Ҹж—ҸпјҢз”ҹдәҺз”ҳеҚ—иҝӯйғЁгҖӮдҪңе“Ғж•Ји§Ғ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ҠйЈһеӨ©гҖӢгҖҠдёӯеӣҪиҜ—жӯҢгҖӢзӯүгҖӮ
еҪӯдё–еҚҺпјҢзҪ‘еҗҚжІ§жөӘд№Ӣж°ҙпјҢз”ҳиӮғз”ҳеҚ—дәәпјҢеҮәз”ҹдәҺдёғеҚҒе№ҙд»ЈеҲқпјҢз”ҳиӮғз”ҳеҚ—е·һйқ’е№ҙиҜ—жӯҢеӯҰдјҡеүҜдјҡй•ҝ,жӣҫеңЁгҖҠйЈһеӨ©гҖӢгҖҒгҖҠз”ҳиӮғж—ҘжҠҘгҖӢгҖҒгҖҠиөЈиҘҝ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иҘҝйғЁиҜ—жҠҘгҖӢгҖҒгҖҠеҮ жұҹгҖӢгҖҒгҖҠйҖҗж°ҙ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иҖҒзҲ·еұұгҖӢзӯүжҠҘеҲҠеҸ‘иЎЁжңүиҜ—жӯҢгҖҒиҜ„и®ә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