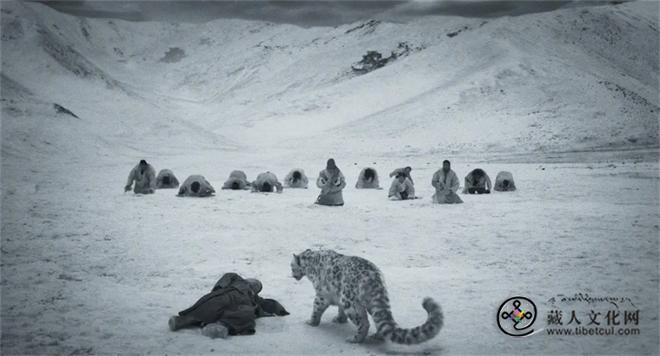еүҚзҺ°д»Јж—¶жңҹпјҢж–ҮеҢ–дј жүҝйҷӨд»Јйҷ…еҸЈдј еӨ–жңҖжңүеҠӣзҡ„е·Ҙе…·е°ұжҳҜеҲ©з”Ёж–Үеӯ—дёҺд№ҰеҶҷз¬ҰеҸ·ж’°еҶҷж–Үжң¬гҖӮиҝҷж ·иҷҪ然зӣёеҜ№жқңз»қдәҶеҸЈдј зҡ„жҳ“еҸҳејӮзү№жҖ§пјҢдҪҶеңЁзү№ж®ҠеўғйҒҮдёӢд»ҚиҗҪе…¶е’ҺгҖӮе°Өе…¶жҳҜж°‘ж—Ҹеҝ—(Ethnography)ж–Үжң¬пјҢз”ұдәҺең°зҗҶдҪҚ移гҖҒж”ҝжІ»ж„ҸиҜҶгҖҒеҶҷдҪңиҖ…иҮӘиә«зҡ„ж°‘ж—Ҹдёӯеҝғи§ӮеҝөзӯүеҺҹеӣ пјҢдәҰе……ж»ЎжғіеғҸзҡ„дё–з•Ң秩еәҸпјҢиҮҙдҪҝд»ҠдәәеҲ©з”Ёиҝҷжү№иө„ж–ҷйңҖиҰҒйҮҚж–°жһ„жӢҹеҪ“ж—¶зҡ„еңәжҷҜгҖӮе…¶е®һпјҢиҝҷйҮҢзҡ„“еҝ—”еҸҜд»ҘзҗҶи§Јдёә“и®°иҪҪ”пјҢдҪҶдәҰжңүдёҖеұӮ“жҸҸж‘№”д№Ӣж„ҸгҖӮж•…1839е№ҙжі•дәәиҫҫзӣ–е°”еҸ‘жҳҺж‘„еҪұжңҜиӮҮе§ӢпјҢе°Өе…¶еҲ°19дё–зәӘеҗҺжңҹпјҢиҘҝж–№ж®–ж°‘ең°дёҖзүҮ“еӨӘе№і”пјҢдё“дёҡдәәе‘ҳгҖҒж—…иЎҢжҺўйҷ©е®¶гҖҒдј ж•ҷеЈ«зӯүеңЁдё–з•Ңеҗ„ең°жӢҚж‘„дәҶеӨ§йҮҸеңҹи‘—жқ‘иҗҪе’ҢдәәдҪ“з…§зүҮгҖӮеҚідҫҝеҪ“еҲқж‘„еҪұиҖ…并没жңүеёҰзқҖдәәзұ»еӯҰзҡ„еҲқиЎ·пјҢдҪҶеӣ жһҒејәзҡ„“жҸҸж‘№”жҖ§пјҢиҝҷжү№з…§зүҮдёҡе·Іиў«дәәзұ»еӯҰйўҶеҹҹеҲ©з”ЁгҖӮд»ҺиҝҷеұӮи§’еәҰпјҢиҝҷдәҰжҳҜжҸҸиҝ°жҖ§ж°‘ж—Ҹеҝ—ж‘„еҪұ(Ethnographic Photography)зҡ„е…ҲжІігҖӮ

ж‘„еҪұжңҜеҸ‘жҳҺиҖ…иҫҫзӣ–е°”
иҷҪ然еңЁдәәзұ»еӯҰз•Ңй•ҝжңҹжңүе…ідәҺж’°иҝ°“жҳҜеҗҰзңҹе®һ”зҡ„дәүи®әпјҢдҪҶиҮӘ20дё–зәӘеҗҺеҚҠеҸ¶иө·пјҢж°‘ж—Ҹеҝ—еҶҷдҪңжқғеЁҒжЁЎејҸе·ІејҖе§Ӣеҗ‘йҳҗйҮҠеӯҰ(Hermeneutic)ж„Ҹд№үеұӮйқўжӮ„жӮ„иҪ¬жҚўгҖӮжІЎжңүдәәеҶҚиҜҙ他们и§ӮеҜҹзҡ„дёңиҘҝжҳҜ“е®ўи§Ӯзҡ„”гҖҒ“зңҹе®һзҡ„”пјҢеӣ дёәдҪ еҶҷдҪңзҡ„еҗҢж—¶жҜ«ж— з–‘д№үжҗәжңүиҮӘе·ұзҡ„дё»и§Ӯж„Ҹеҗ‘пјҢдәӢе®һе°ұеғҸжқғеЁҒзҡ„еӯҰиҖ…еҜ№еҸӨзұҚеҠ д»ҘзӮ№иҜ„пјҢз”өи§ҶеҸ°иҜ·дәәеҜ№жҹҗйғЁз”өеҪұгҖҒжҲҸеү§“иҜҙдёүйҒ“еӣӣ”гҖӮе°Ҫз®Ўиҝҷж ·пјҢжҲ‘们жүҝи®Өз ”з©¶иҖ…иҷҪжҗәжңүдё»и§Ӯж„ҸиҜҶпјҢдҪҶд»ҚеңЁе®ўи§ӮжҸҸиҝ°пјҢжүҖд»ҘпјҢжҲ‘们и®Өдёә他们“йҖјиҝ‘зңҹе®һ”гҖӮжҺЁе»¶ејҖпјҢиҝҷдёҖжү№йқ зңјзқӣ“е®һеҪ•”зҡ„ж°‘ж—Ҹеҝ—ж‘„еҪұдҪңе“ҒжҳҜзңҹе®һзҡ„еҗ—пјҹд»Һдәәзұ»еҝғжҷәжқҘиҜҙпјҢдәә们жҖ»жҳҜиҝҮдәҺзӣёдҝЎиҮӘе·ұзҡ„зңјзқӣпјҢзӣёжҜ”ж–Үеӯ—иҖҢиЁҖпјҢеӣҫеғҸжӣҙи®©дәәзӣёдҝЎпјҢеӣ дёәе®ғжҳҜ“зңҹ”зҡ„гҖӮжҳҜиҝҷж ·еҗ—пјҹ
еҰӮжһңиҰҒзҗҶи§ЈеҪұеғҸз”»йқўпјҢиҮіе°‘йңҖиҰҒд»ҺдёүдёӘж–№йқўеҠ д»ҘжҠҠжҸЎпјҡз…§зүҮжң¬иә«пјӣи§ӮзңӢиҖ…еҜ№з…§зүҮдё»йўҳзҡ„и§ЈйҮҠпјӣеҸҰеӨ–иҝҳиҰҒиҖғиҷ‘еҜ№ж‘„еҪұеёҲж„Ҹеҗ‘зҡ„еҸҚи§Ӯз”ҡиҮіжҳҜжҸЈж‘©гҖӮеӣәжӯӨпјҢе°Ҫз®Ўз…§зүҮд№ҹдҪңдёә第дёҖжүӢиө„ж–ҷжҲ–дәәзұ»еӯҰж–ҮзҢ®дҪҝз”ЁпјҢдҪҶе®ғз»қдёҚжҳҜзҺ°е®һжң¬иә«зҡ„еӨҚеҲ¶пјҢиҖҢеҸӘжҳҜдёҖз§ҚйңҖиҰҒжү№еҲӨзҗҶи§Је’ҢйҳҗйҮҠзҡ„иүәжңҜдҪңе“ҒгҖӮ

е…¶е®һиҮӘж‘„еҪұжңҜеҸ‘жҳҺиӮҮе§ӢпјҢеңЁд»ҘдёӘдҪ“жҲ–дәәзҫӨдёәжӢҚж‘„зӣ®ж Үзҡ„ж‘„еҪұиЎҢдёәдёӯпјҢж‘„еҪұеёҲдёҺиў«ж‘„иҖ…дёҖзӣҙеӨ„дәҺдёҖз§ҚеҜ№з«ӢзҠ¶жҖҒпјҢиҝҷеңЁй’ҲеҜ№йқһиҘҝж–№еңҹи‘—ж—ҸзҫӨзҡ„жҸҸиҝ°жҖ§ж°‘ж—Ҹеҝ—ж‘„еҪұйҮҢе°ӨжҳҫзӘҒеҮәгҖӮж‘„еҪұеёҲд»Ҙж®–ж°‘ең°ж”ҝеәңе’Ёе®ўгҖҒж°‘ж—ҸеӯҰ(дәәзұ»еӯҰ)家гҖҒжҺўйҷ©иҖ…иә«д»ҪеҮәзҺ°пјӣиҖҢй•ңеӨҙдёӯзҡ„жң¬еңҹеұ…ж°‘еҲҷжҳҜиў«з®ЎзҗҶиҖ…е’Ңз ”з©¶гҖҒи§ӮеҜҹзҡ„еҜ№иұЎгҖӮж‘„еҪұеёҲ们и®ӨдёәиҮӘе·ұдёҖж–№еӨ©з„¶ең°д»ЈиЎЁзқҖж–ҮжҳҺгҖҒ科еӯҰзӯүиҘҝж–№иЎЁеҫҒпјӣиҖҢеҜ№з«Ӣйқўзҡ„еңҹи‘—еҲҷзӣёеҜ№жҳҜдёҖдәӣйқһиҘҝж–№гҖҒйҮҺиӣ®гҖҒж„ҡжҳ§зҡ„ејӮж–ҮеҢ–з¬ҰеҸ·гҖӮзҝ»йҳ…ж—©жңҹиҘҝж–№ж‘„еҪұеёҲеҜ№зҺҜеӨӘе№іжҙӢгҖҒйқһжҙІзӯүең°еңҹи‘—еұ…ж°‘зҡ„еҪұеғҸи®°еҪ•пјҢдёҚйҡҫеҸ‘зҺ°иҝҷдёҖзұ»иҮӘжҲ‘зҡ„жғіеғҸйҖҡиҝҮй•ңеӨҙеҫ—еҲ°дәҶж·Ӣжј“е°ҪиҮҙең°иЎЁзҺ°гҖӮз”»йқўдёҠдёҚи®әжҳҜжөӢйҮҸеңҹи‘—дәәзҡ„дҪ“иҙЁзү№еҫҒпјҢиҝҳжҳҜи®°еҪ•еҪ“ең°зҡ„д»ӘејҸиҝҮзЁӢпјҢдәәзү©еӨ§еӨҡзңјзҘһе‘Ҷж»һпјҢиӮўдҪ“еғөзЎ¬пјҢз”ҡиҮіиЎЁиҫҫеҮәеҜ№зӣёжңәзҡ„жғҠжҒҗгҖӮз”»йқўдёҠиў«ж‘„иҖ…зңјзқӣжҳҺжҳҫзӣҜзқҖй•ңеӨҙпјҢиҝҷд№ҹи®©дәәзңӢеҮәе…¶дёӯж‘„еҪұеёҲжҢҮеҗ‘жҖ§зҡ„жҡ—зӨәе’Ңж‘ҶеёғгҖӮиҝҷж ·зҡ„з…§зүҮжҳҜ“зңҹе®һ”зҡ„еҗ—пјҹеӨ–жқҘиҖ…е’Ң他们зҡ„иЎҢдёә并没жңүеҫ—еҲ°иў«жӢҚж‘„дәәзҫӨзҡ„ж¬ўиҝҺпјҢиҝҷж—¶пјҢж‘„еҪұеёҲжҳҜдёҖдёӘе…ёеһӢзҡ„“е…ҘдҫөиҖ…”гҖӮд»–иҝҮеӨҡеҖҫеҗ‘дәҺе®үжҺ’е’Ңж‘ҶеёғпјҢиҖҢжІЎжңүйҮҮеҸ–дёҺжӢҚж‘„дәәзҫӨдә’еҠЁдәӨжөҒгҖӮдёҖж—Ұжң¬еңҹеұ…ж°‘иҺ·жӮүдәҶж‘„еҪұеёҲжүӢдёӯзӣёжңәзҡ„“йӯ”жі•”пјҢ他们дјҡйҖғйҒҝз”ҡиҮіжҠ—жӢ’гҖӮд»ҘиҮідәҺжңүиҝҷж ·зҡ„иҜҙжі•——еңҹи‘—жӢ’з»қиў«жӢҚж‘„жҳҜеӣ дёә他们зӣёдҝЎж‘„еҪұдјҡеҜјиҮҙзҒөйӯӮдёўеӨұпјҢиҖҢе…¶е®һпјҢиҝҷжҒ°жҒ°жҳҜејұеҠҝзҫӨдҪ“йқўеҜ№жӢҚж‘„иЎҢдёәиҝҷдёҖ“дҫөе…Ҙ”дәӢе®һиҖҢдә§з”ҹзҡ„дёҖз§Қи°ғйҖӮжҖ§жҠөжҠ—еҝғзҗҶгҖӮ

иҝҷдёҖдёҚе№ізӯүзҡ„дәӢе®һи®©йқўеҜ№й•ңеӨҙзҡ„жң¬еңҹеұ…ж°‘дёҖзӣҙеӨ„еңЁдёҖз§Қ“еӨұиҜӯ”зҠ¶жҖҒгҖӮдёӯеӣҪејҖеҹ д»ҘжқҘпјҢиҘҝж–№еӯҰиҖ…гҖҒжҺўйҷ©е®¶й•ңеӨҙйҮҢзҡ„дёӯеӣҪеҪұеғҸдәҰжӢ·иҙқдәҶиҝҷдёҖзұ»з”»йқўгҖӮж— и®әжҳҜж–№иӢҸйӣ…(Auguste Francois)й•ңеӨҙдёӢзҡ„жҳҶжҳҺдј—з”ҹпјҢиҝҳжҳҜзәҰз‘ҹеӨ«•жҙӣе…ӢжӢҚдёӢзҡ„зәіиҘҝеҸҠи—ҸдәәеҪұеғҸпјҢйғҪдёҚд№ҸзңјзҘһе‘Ҷж»һпјҢеҠЁдҪңеғөзЎ¬иҖ…пјҢж‘Ҷеёғе’Ңе®үжҺ’жҳҫиҖҢжҳ“и§ҒгҖӮз”»йқўдёҠзҡ„дәәзү©йҖҡеёёжҳҜе®ҡж је’Ңйқҷжӯўзҡ„пјҢиў«и®°еҪ•зҡ„зһ¬й—ҙ并没жңүиЎЁзҺ°еҮәеҪ“ең°дәәзңҹе®һзҡ„з”ҹжҙ»гҖӮжңүж„ҸжҖқзҡ„жҳҜпјҢиҝҷж ·зҡ„з”»йқўз”ҡиҮіиҝӣдёҖжӯҘиҪ¬иҫҫз»ҷеӨ–дәәдёӯеӣҪеёӮж°‘зӨҫдјҡжӯ»жқҝгҖҒеғөж»һзҡ„еҚ°иұЎ(иҝҷеңЁиҘҝдәәй’ҲеҜ№дёӯеӣҪзҡ„ж–Үеӯ—жҸҸеҶҷйҮҢж—¶жңүиЎЁиҝ°)——然иҖҢеңЁдәӢе®һдёҠпјҢзңҹе®һзҡ„еёӮж°‘зӨҫдјҡеҚҙжңүе…¶иҪ»жқҫгҖҒжҙ»и·ғзҡ„дёҖйқўгҖӮе…·дҪ“иҜҙпјҢдҪңдёәй©»жҳҶжҳҺзҡ„йўҶдәӢе®ҳе‘ҳпјҢж–№иӢҸйӣ…жңүжӣҙеӨҡзҡ„жңәдјҡе®үжҺ’гҖҒж‘ҶеёғжӢҚж‘„дәәзү©гҖӮжҲ‘们еҸҜд»Ҙжё…жҷ°зңӢеҮәпјҢиҖҒжҳҶжҳҺз…§зүҮйҮҢзҡ„еүҚжё…жӯҰе®ҳгҖҒиЎ—еӨҙеҗ„дёҡдәәзӯүеңЁж–№ж°Ҹзҡ„й•ңеӨҙдёӢйғҪеҒңдҪҸдәҶгҖӮиҖҢзәҰз‘ҹеӨ«•жҙӣе…Ӣзҡ„е·қж»ҮжёёеҺҶпјҢжҜ«ж— дҫӢеӨ–д№ҹйңҖиҰҒд»°д»—еҪ“ең°еңҹеҸёгҖҒе®ҳе‘ҳзҡ„з…§жӢӮдёҺе®үжҺ’гҖӮеңЁдёҖдёӘйҳ¶еұӮеҲҶеҢ–жҳҺжҳҫзҡ„зӨҫдјҡпјҢд»ҘдёҺдёҠеұӮеҗҢи°Ӣзҡ„ж–№ејҸд»Ӣе…Ҙж— з–‘дјҡжңүеҫҲеӨҡж–№дҫҝпјҢдҪҶжҜ«ж— з–‘д№үеҮҸејұдәҶж‘„еҪұеёҲдёҺиў«ж‘„иҖ…зҡ„дёӘдҪ“дә’еҠЁпјҢзүәзүІдәҶз”»йқўзҡ„зңҹе®һе’ҢеҪұеғҸзҙ иҙЁгҖӮиҝҷж ·жҳҫиҖҢжҳ“и§Ғзҡ„жЎҺжўҸжҒ°жҒ°жҳҜе…·еӨҮдё“дёҡзҙ е…»зҡ„жҙӣе…ӢеҚҡеЈ«дёҚж„ҝж„ҸзңӢеҲ°зҡ„гҖӮ
и‘—еҗҚеӯҰиҖ…зәҰз‘ҹеӨ«•жҙӣе…Ӣ
иҝҷзұ»еҪұеғҸи®°еҪ•дёӯпјҢзңҹжӯЈзҡ„еңҹи‘—еӨұиҜӯпјҢз”ҡиҮійҡҗиә«пјҢеӣ дёәи®°еҪ•иҝҮзЁӢжҳҜдёҖз§ҚеҚ•з»ҙжҢҮеҗ‘иҖҢйқһеҸҢеҗ‘дә’еҠЁзҡ„жӢҚж‘„иЎҢдёәпјҢдҪҶиҝҷеҚҙжҳҜж°‘ж—Ҹеҝ—ж‘„еҪұдёӯдёҖдёӘжһҒе…¶еёёи§Ғзҡ„йҖҡз—…гҖӮдәӢе®һдёҠпјҢеҪ“жҲ‘жҺҘи§ҰдәҶеә„еӯҰжң¬зҡ„ж‘„еҪұдҪңе“ҒеҗҺй•ҝд№…ең°жғҠејӮдәҶ——еә„ж°Ҹй•ңеӨҙдёӢзҡ„з”»йқўжҳҜ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е…ёеһӢзҡ„дҫӢеӨ–гҖӮиҝҷдҪҚйҖҡиҝҮеҒ·иүә(еә„ж°Ҹ1930е№ҙиҮі1934е№ҙеңЁеҚ—дә¬еҪ“иҒҢе‘ҳж—¶жҒ°дёҺз…§зӣёжқҗж–ҷе…¬еҸёдёәйӮ»пјҢе°ұеҖҹжӯӨжңәдјҡеӯҰд№ ж‘„еҪұ)иҖҢжҺҢжҸЎж‘„еҪұжҠҖжңҜзҡ„е№ҙиҪ»дәәдёҖзӣҙжҖҖзқҖеҜ№ејӮж–ҮеҢ–зғӯеҝұзҡ„еҘҪеҘҮгҖӮдәӢе®һдёҠпјҢеҪ“ж—¶е№ҙиҪ»зҡ„еә„еӯҰжң¬йҰ–е…Ҳд№ҹжғіеҲ°дёҺж—¶дәәзӣёеҗҢзҡ„еҪўејҸпјҢд»–дёҖзӣҙж„ҝж„ҸеҖҹеҠ©е®ҳж–№иЎҢдёәжқҘе®һзҺ°е…¶иҝӣи—ҸжӢҚж‘„зҡ„ж„ҝжңӣпјҢ然иҖҢеҚҙеӣ дёәеҗ„з§ҚеҺҹеӣ ж•°еәҰжңӘжһңгҖӮ1934е№ҙпјҢеә„еӯҰжң¬иҮӘеӨҮж—…иө„пјҢдёҺеҪ“ж—¶еӣҪж°‘ж”ҝеәңеӣ иҫҫиө–е–ҮеҳӣеҺ»дё–иҖҢз»„з»Үзҡ„иөҙи—ҸиҮҙзҘӯдё“дҪҝе…¬зҪІеҗҢиЎҢиөҙи—ҸгҖӮдҪҶеҲ°еӣӣе·қжҲҗйғҪеҗҺиў«еҖҹеҸЈиә«д»ҪдёҚжҳҺдёҚе…Ғиҝӣи—ҸпјҢеә„ж°ҸеҸӘеҘҪеҸҰжӢ©йқ’жө·жһңжҙӣи—ҸеҢәи°ғжҹҘж‘„еҪұгҖӮ1935е№ҙпјҢеә„ж°ҸеҸӮеҠ еӣҪж°‘ж”ҝеәңжҠӨйҖҒзҸӯзҰ…еӣһи—Ҹдё“дҪҝе…¬зҪІпјҢ并任摄еҪұеёҲпјҢдҪҶеӣ зҸӯзҰ…еңЁйқ’жө·еңҶеҜӮе’ҢжҠ—жҲҳзҲҶеҸ‘пјҢеә„ж°ҸдәҰеҸӘиғҪеңЁе·қеә·дёҖеёҰйҖ—з•ҷ10дёӘжңҲиҖҢжңӘиғҪиҝӣи—ҸгҖӮ1942е№ҙз»•йҒ“еҚ°еәҰиөҙи—ҸпјҢеҸҲеӣ еҚ°еәҰж”ҝеәңдёҚиӮҜзӯҫеҸ‘жҠӨз…§иҖҢжңӘиғҪе®һзҺ°е®ҝж„ҝгҖӮжӯЈеӣ дёәиҝҷдәӣеҺҹеӣ пјҢеә„ж°ҸжңҖз»ҲйҮҮеҸ–дәҶдёӘдҪ“д»Ӣе…Ҙзҡ„ж–№ејҸгҖӮиҝҷеёҰжқҘдәҶеҫҲеӨ§зҡ„иү°иӢҰе’ҢжӣІжҠҳпјҢдҪҶеҚҙжңүеҠ©дәҺеә„ж°Ҹж— жқЎд»¶иһҚе…ҘеҪ“ең°ж°‘дј—з”ҹжҙ»пјҢ并иҰҒжұӮд»–з§ҜжһҒең°дёҺиў«жӢҚж‘„зҫӨдҪ“дәӨжөҒдә’еҠЁгҖӮ
ж‘„еҪұеӨ§еёҲеә„еӯҰжң¬
еҪ“жҲ‘зҝ»йҳ…еүҚдёҖдё–зәӘ30е№ҙд»Јзҡ„гҖҠиүҜеҸӢ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еҚҺгҖӢзӯүз”»жҠҘд»ҘеҸҠеә„еӯҰжң¬и‘—дҪңгҖҠзҫҢжҲҺиҖғеҜҹи®°гҖӢпјҢжҲ‘дёҚеҫ—дёҚдёәеә„ж°ҸеҪ“ж—¶жӢҚж‘„зҡ„з”»йқўиҖҢй•ҝд№…ж„ҹеҠЁпјҢиҝҷжү№й’ҲеҜ№йқ’жө·гҖҒеӣӣе·қзӯүең°и—ҸгҖҒзҫҢзӯүе°‘ж•°ж°‘ж—Ҹзҡ„ж°‘ж—Ҹеҝ—ж‘„еҪұиҫҫеҲ°дәҶдёҖдёӘеҫҲй«ҳзҡ„зЁӢеәҰгҖӮеҪұеғҸдёҖжү«д»ҘеҫҖж°‘ж—Ҹеҝ—ж‘„еҪұзҡ„е‘ҶжқҝдёҺжј з„¶пјҢдәәзү©з”ҹеҠЁпјҢ笑容满йқўпјҢз”»йқўе……ж»ЎеҠЁж„ҹгҖӮжҚ®еә„еӯҰжң¬е„ҝеӯҗеә„ж–ҮйӘҸи®Іиҝ°пјҢеә„дёҺеҪ“ең°дәәзӣёеӨ„йқһеёёиһҚжҙҪпјҢеҫҲеӨҡи·Ҝж®өйғҪеҫ—еҲ°дәҶеҪ“ең°дәәиҮӘж„ҝжҠӨйҖҒгҖӮжҚ®иҜҙпјҢеә„еӯҰжң¬еҪ“ж—¶еңЁеӣӣе·қеҮүеұұжҳӯи§үеҺҝеҹҺиЎ—дёҠз»ҷеҪ“ең°дәәж”ҫз•ҷеЈ°жңәеҗ¬(并没жңүдәәи§үеҮәиҮӘе·ұзҡ„зҒөйӯӮжңүд»Җд№ҲејӮж ·)пјӣеңЁйҳҝеққиҝҳд№°дәҶдёҖйЎ¶зҷҪеёҗзҜ·дёҺи—Ҹж°‘ж··дҪҸеңЁдёҖиө·гҖӮиҖҢиҝҷжҒ°жҒ°жҳҜжҙӣе…ӢгҖҒж–№иӢҸйӣ…д»¬ж— жі•еҒҡеҲ°зҡ„гҖӮжҙӣе…ӢдёҖзӣҙдҝқжҢҒзқҖиҮӘе·ұдјҳйӣ…зҡ„з»…еЈ«йЈҺеәҰпјҢеҚідҪҝеңЁеҒҸиҝңзҡ„ең°ж–№д№ҹйҖҡеёёиҰҒ“е№ІеҮҖ”ең°зӢ¬еұ…гҖӮд»–еңЁж–Үз« йҮҢй•ҝзҜҮзҙҜзүҚи®°иҝ°зқҖж—…иЎҢдёӯйҒҮеҲ°зҡ„дёҚе№ІеҮҖгҖҒйҡҫеҸ—зӯүзӯүд»–и®Өдёәж— жі•еҝҚеҸ—зҡ„дәӢжғ…гҖӮиҮідәҺж–№иӢҸйӣ…иҝҷж ·зҡ„еӨ–дәӨе®ҳпјҢиҮӘ然е°ұжӣҙжңүжқғеҲ©е’ҢзҗҶз”ұд»…д»…з”ЁзӣёжңәдҝқжҢҒдёҺиў«ж‘„еҜ№иұЎзҡ„иҒ”зі»пјҢд»–еҸҜд»ҘдёҘж јзҡ„дёҺиў«ж‘„иҖ…дҝқжҢҒи·қзҰ»пјҢеҮ д№ҺдёҚйңҖиҰҒжӣҙеӨҡжҺҘи§ҰгҖӮ


еә„еӯҰжң¬з”ЁиҮӘе·ұзҡ„й•ңеӨҙдёҺиў«ж‘„иҖ…дәӨжөҒпјҢ并йҷҲиҝ°зқҖд»–иҮӘе·ұ“зңӢеҲ°”зҡ„еҪұеғҸгҖӮеңЁд»–жӢҚж‘„зҡ„дәәзү©еҪұеғҸдёӯпјҢиў«ж‘„иҖ…йҮҚж–°ејҖеҸЈи®ІиҜқгҖӮйҖҸиҝҮд»–еҪ“е№ҙж‘„дёӢзҡ„еҪұеғҸпјҢжҲ‘们еҸҜд»ҘжғіеғҸд»–еңЁдёҠдё–зәӘ30е№ҙд»ЈеҰӮдҪ•з”Ёз¬ЁйҮҚзҡ„120зӣёжңәеЁҙзҶҹең°жҠўжӢҚпјҡд»–жӢҚдёӢжҙ’йҶүеҗҺи®Іжө‘иҜқзҡ„з”·еӯҗпјӣз©ҝзқҖз ҙзғӮиЎЈжңҚеҸ‘еҮәзҲҪжң—笑声зҡ„и—Ҹж—ҸеҘіеӯ©……д»–жӢҚдёӢжөҒеҠЁзқҖзҡ„д»ӘејҸпјҢејәжӮҚзҡ„еҪқж—ҸжҠўе©ҡ……з”»йқўдёҠпјҢдәәзү©иҮӘ然ең°жҙ»еҠЁзқҖпјӣиҖҢдёҖдәӣж ҮеҮҶзҡ„дәәеғҸдёҠпјҢиў«ж‘„иҖ…зҡ„зңјзҘһдёҺеә„еӯҰжң¬еңЁдёҚж–ӯдәӨжөҒгҖӮиҝҷж ·зҡ„ж°‘ж—Ҹеҝ—ж‘„еҪұеҰӮжӯӨд№ӢйҖјиҝ‘зңҹе®һпјҢ并еңЁжңҖеӨ§йҷҗеәҰдёҠжҒўеӨҚдәҶеҺҹе…Ҳзҡ„з”ҹжҙ»еңәжҷҜгҖӮжҲ‘们еҸҜд»ҘйҖҡиҝҮиҝҷдәӣеӣҫзүҮдё»дҪ“гҖҒж‘„еҪұеёҲе’Ңи§ӮиҖ…иҮӘиә«дёүдёӘж–№йқўзҡ„е®Ңж•ҙжҠҠжҸЎпјҢиҝӣиЎҢдёҖзі»еҲ—еҲҶжһҗе’ҢиҜ йҮҠпјӣ并且жҲ‘们иҝҳдјҡеҸ‘зҺ°иҝҷжү№еҪұеғҸжҜ”е…¶д»–еӣҫзүҮжӣҙиғҪж–№дҫҝең°иҺ·еҸ–еҪ“ж—¶зҡ„“зңҹе®һ”гҖӮ
еҜ№дёҖдәӣиҫ№иҝңзҡ„е°‘ж•°ж°‘ж—Ҹең°еҢәжқҘиҜҙпјҢд»ҠеӨ©зҡ„дёҖдәӣж‘„еҪұеёҲе·Із»Ҹи·іеҮәдәҶ“йҮҮйЈҺ”зҡ„еәёдҝ—жЁЎејҸпјҢ然иҖҢеҚҙеҸҲеҝҷзўҢең°еҲ¶йҖ зқҖдёҖдәӣеҲҮзүҮ——дёҖдәӣи§Ҷи§үгҖҒи§Ӯж„ҹдёҠзҡ„еҲҮзүҮгҖӮжҲ‘и§ҒиҝҮжө·еҶ…еӨ–дёҖдәӣж‘„еҪұеёҲиҝҷж ·зҡ„дёҖдәӣдҪңе“Ғпјҡз”»йқўз”ЁжЁЎзү№е’ҢеҪ“ең°еұ…ж°‘зҡ„еҸҚе·®иЎЁиҫҫеҮәдёҖз§ҚејәзғҲзҡ„и§Ҷи§үеҲәжҝҖгҖӮж‘„еҪұеёҲжҠҠиҝҷж ·зҡ„еҪұеғҸжҸҗдҫӣз»ҷдё»жөҒзӨҫдјҡпјҢи®©дәә们用画йқўж¬ЈиөҸиҫ№зјҳгҖҒејұеҠҝзҫӨдҪ“жҸҗдҫӣдёҖз§Қеұ•зӨәдёҠзҡ„иҷҡеҒҮзңҹе®һгҖӮиҝҷжҳҜз”ЁдёҺи§ӮеҜҹиҖ…иҮӘиә«жһҒеӨ§зҡ„е·®ејӮйҖ жҲҗи§Ҷи§үдёҠзҡ„еҶІзӘҒ(жңүж—¶жҳҜдәәйҖ зҡ„——ж°‘ж—ҸжңҚиЈ…гҖҒжЁЎзү№еӨёеј зҡ„йҖ еһӢгҖҒеҸ‘ејҸзӯүзӯү)жқҘи§ЈеҶіеӣҫеғҸдёҠзҡ„еҲәзӮ№зҺ°иұЎгҖӮжі•еӣҪз¬ҰеҸ·еӯҰ家зҪ—е…°?е·ҙе°”зү№иҝҷж ·и§ЈйҮҠеҲәзӮ№пјҡ“жӯЈжҳҜиҝҷдёӘдёңиҘҝеғҸз®ӯз°ҮдёҖж ·д»ҺжҷҜзү©дёӯеҸ‘е°„еҮәжқҘгҖӮе®ғжҗ…д№ұдҪ е·ІзҹҘзҡ„йӮЈдёӘеұӮйқўпјҢе®ғжҳҜз…§зүҮдёӯзҡ„дёҖдёӘеҲәпјҢдёҖдёӘж–‘зӮ№пјҢдёҖдёӘдёӯж–ӯпјҢдёҖдёӘжҙһпјҢжҳҜжҺ·еҮәеҺ»зҡ„дёҖдёӘйӘ°еӯҗгҖӮе®ғдҪҝи§ӮзңӢиҖ…ж„ҸеӨ–ең°еҸ—еҲ°еҲәжҝҖгҖӮ”иҝҷж ·зҡ„еҲәзӮ№з®ҖеҚ•иҖҢеҸҲдҫҝдәҺеҲ¶дҪңпјҢе®ғз”ЁдёҖз§ҚиҷҡеҒҮзҡ„з”»йқўжҸҗдҫӣзқҖе»үд»·ең°еҲәжҝҖе’Ңж¬ЈиөҸ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иҝҮеҺ»и®©иў«ж‘„иҖ…еӨ„дәҺеӨұиҜӯзҠ¶жҖҒжңүиў«еҠЁзҡ„еӣҝеӣ пјҢйӮЈд№Ҳд»ҠеӨ©зҡ„з”»йқўеҚҙе®Ңе®Ңе…Ёе…ЁжҳҜдёҖз§ҚдәәдёәеҲ¶дҪңгҖӮе®ғдё»еҠЁиҝ«дҪҝз”»йқўдёҠйғЁеҲҶдәәзү©йҷ·е…Ҙ“еӨұиҜӯ”зҠ¶жҖҒпјҢдҪҶж•ҙдҪ“зҡ„зӨҫдјҡдј еӘ’еҸҲжІЎжңүз»ҷеӨұиҜӯиҖ…жҸҗдҫӣеҸҚй©іе’ҢиЎЁиҫҫиҮӘиә«иҜқиҜӯзҡ„ең°ж–№гҖӮжүҖд»ҘпјҢиҝҷд»Қ然жҳҜдёҖз§Қе…ёеһӢзҡ„“жңҜ”пјҢж‘„еҪұеёҲгҖҒжЁЎзү№гҖҒзӣёжңәиҒ”еҗҲиЎЁжј”дәҶдёҖеңәеҜ№жң¬еңҹеұ…ж°‘зҡ„“е…Ҙдҫөд»ӘејҸ”гҖӮ
жҲ‘д»¬ж— ж„ҸиҰҒжұӮж‘„еҪұеёҲйғҪе…·еӨҮдәәзұ»еӯҰзҡ„зҙ е…»пјҢдҪҶиҮіе°‘еңЁиҝӣе…ҘжӢҚж‘„ең°еҢә(е°Өе…¶жҳҜдёҺиҮӘе·ұзҶҹзҹҘзҡ„ж–ҮеҢ–иҝҘејӮзҡ„е…¶д»–ж—ҸзҫӨең°еҢә)еүҚеҸҜд»Ҙйҳ…иҜ»ж–ҮзҢ®пјҢеҠӘеҠӣдәҶи§ЈеҪ“ең°йЈҺдҝ—ж–ҮеҢ–пјҢжҲ–иҮіе°‘еҜ№жҺҘеҸ—жӢҚж‘„зӨҫеҢәдҝқжҢҒж•Ҹй”җзҡ„и°ғз ”дёҺи®ӨиҜҶгҖӮе…¶е®һпјҢд»Һеә„еӯҰжң¬зҡ„ж‘„еҪұиҝҮзЁӢд№ҹ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еә„зҡ„еҲқ衷并没жңүеёҰзқҖдәәзұ»еӯҰ家иҝӣе…Ҙз”°йҮҺзҡ„еҮҶеӨҮпјҢ然иҖҢеә„зҡ„ж‘„еҪұиЎҢдёәеҲҷеёҰжңүдәҶз”°йҮҺе·ҘдҪң(Field work)зҡ„жҲҗеҲҶпјҢиҮіе°‘д»–зҡ„еҪұеғҸе°ұжҳҜдёҖз§Қе…ёеһӢзҡ„ж°‘ж—Ҹеҝ—ж‘„еҪұгҖӮ
дәәзұ»еӯҰзӣёдҝЎеә”ж‘Ҳејғд»»дҪ•еҪўжҖҒзҡ„ж—ҸзҫӨдёӯеҝғдё»д№үпјҢйҮҮзәіж–ҮеҢ–зӣёеҜ№зҗҶеҝөгҖӮе…·дҪ“жҳҜжҺЁеҙҮеҜ№дёҖдёӘж—ҸзҫӨз”ҹжҙ»ж–№ејҸд»·еҖјзҡ„зӣёеҜ№зҡ„жҖҒеәҰпјҢдҫӢеҰӮзӣёдҝЎд»»дҪ•ж—ҸзҫӨзҡ„жҲҗе‘ҳеңЁдҝЎд»°дёҠзҡ„зңҹиҜҡжҖ§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з”ЁиҮӘе·ұжҲ–дё»жөҒзҡ„д»·еҖји§ӮеҺ»иҜ„д»·еҲ«дәәгҖӮиҝҷдёҚд»…жҳҜдәәзұ»еӯҰиҖ…еә”еҸ–зҡ„з ”з©¶еҺҹеҲҷпјҢиҖҢдё”д№ҹжҳҜең°зҗғдёҠжҜҸдёҖдёӘдәәеә”еӯҰд№ зҡ„з”ҹжҙ»жҖҒеәҰгҖӮд»Һдәәзұ»еӯҰзҡ„и§’еәҰжқҘзңӢпјҢз…§зүҮдё»дҪ“жҳҜеҜ№дәәзұ»жІҹйҖҡиҝҮзЁӢзҡ„зҗҶи§ЈдёҺе…іжіЁгҖӮиҝҷж ·пјҢеҪұеғҸе°ұеҸҜд»ҘеңЁиҜҫе Ӯжү®жј”ж•ҷиӮІи§’иүІпјҢд№ҹеҸҜд»ҘеңЁеҚҡзү©йҰҶй•ҝжңҹеӯҳз•ҷеҪұе“ҚеҗҺдәәзҡ„еҲӨж–ӯе’Ңж–ҮеҢ–жҺҘеҠӣпјҢиҝҷжҳҜе®ғзҡ„дј жүҝжҖ§пјҢиҖҢжҲ‘们еҲҷеҸҜд»ҘйҖҡиҝҮе®ғиЎЁзҺ°зҡ„зҺ°е®һеңәжҷҜеҲҮйқўжқҘжҜ”иҫғдёҚеҗҢдәәзҫӨе’Ңж–ҮеҢ–гҖӮиў«ж‘„иҖ…жҳҜж— иЁҖзҡ„пјҢдҪҶеҪұеғҸеҚҙжңүејәзғҲзҡ„иЎЁиҫҫпјҢе®ғеҸҜд»ҘдёәејұеҠҝзҫӨдҪ“иҜҙиҜқпјҢд№ҹеҸҜд»Ҙеұ•зӨәжҹҗдәӣж—ҸзҫӨ“дё‘йҷӢ”зҡ„дёҖйқўпјҢеҪ»еә•дҪ“зҺ°ж‘„еҪұиҖ…жғіеғҸзҡ„дёӯеҝғе’Ңиҫ№зјҳгҖӮеҪ“然пјҢиҝҷдёҖеҲҮеҸ–еҶідәҺж‘„еҪұдәәй•ңеӨҙзҡ„йҖүжӢ©дёҺжҢҮеҗ‘——жҳҜжңүж„ҸиҜҶеҸ‘зҺ°е·®ејӮеҲҮзүҮз”ҡиҮізү№ж„ҸеҲ¶йҖ еҲәзӮ№пјҢиҝҳжҳҜи®©еҪұеғҸеңЁжңҖеӨ§йҷҗеәҰдёҠиЎЁиҫҫ并且еҠӣеӣҫиҝҳеҺҹжң¬еңҹеұ…ж°‘зҡ„зңҹе®һз”ҹжҙ»гҖҒеҺҹе§Ӣжғ…ж„ҹд»ҘеҸҠ他们зҡ„е§ҝжҖҒгҖӮиҖҢеңЁиҝҷж–№йқўпјҢеҸҜд»ҘиҜҙеә„еӯҰжң¬жҳҜжҲ‘们зҡ„е…Ҳй©ұе’ҢзңҹжӯЈзҡ„иҖҒеёҲгҖӮ

дҪңиҖ…иҗ§дә®дёӯ
иҗ§дә®дёӯпјҲ1972-2005пјүпјҢдә‘еҚ—иҝӘеәҶдәәпјҢиӢұе№ҙж—©йҖқзҡ„дәәзұ»еӯҰ家гҖӮ1972е№ҙ12жңҲ5ж—ҘпјҢд»–еҮәз”ҹеңЁйҮ‘жІҷжұҹиҫ№зҡ„дә‘еҚ—зңҒиҝӘеәҶи—Ҹж—ҸиҮӘжІ»е·һдёӯз”ёеҺҝйҮ‘жұҹй•ҮиҪҰиҪҙжқ‘пјҢиҝҷдёӘеӨҡж°‘ж—ҸиҒҡеұ…зҡ„иҝһжҺҘжұүи—ҸдёӨең°зҡ„зҫҺдёҪжқ‘иҗҪпјҢеҗҺжқҘжҲҗдёәд»–зЎ•еЈ«жҜ•дёҡи®әж–Үе’Ңд№ҰзЁҝгҖҠиҪҰиҪҙгҖӢзҡ„з”°йҮҺи°ғжҹҘеҹәең°гҖӮеҗҢж—¶пјҢдёәзқҖжҚҚеҚ«иҝҷдёӘжқ‘иҗҪд»ҘеҸҠйҮ‘жІҷжұҹжөҒеҹҹиҝҷзүҮд№ЎеңҹзӨҫдјҡе’Ңдәәж°‘зҡ„жқғзӣҠпјҢд»–ејҖе§ӢдәҶеӣӣеӨ„еҘ”иө°пјҢеҮ иөҙйҮ‘жІҷжұҹпјҢз”Ёд»–зҡ„зғӯжғ…е’Ңеқҡйҹ§жқҘеҪұе“ҚзӨҫдјҡе…¬дј—пјҢжңҖз»ҲдҪҝеҫ—иҷҺи·іеіЎжөҒеҹҹзҡ„дҝқжҠӨе·ҘдҪңеңЁ2004е№ҙйҖҡиҝҮеӣҪеҶ…ж°‘й—ҙзҺҜдҝқз»„з»Үзҡ„е‘јеҗҒиЎҢеҠЁе’ҢеӘ’дҪ“жҠҘйҒ“пјҢи·ғе…Ҙе…¬дј—и§ҶйҮҺгҖӮ